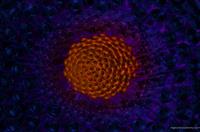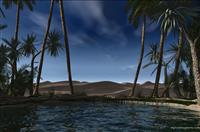
对欧债危机,郑永年并不悲观。“欧债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系统性和结构性矛盾的结果,因此也需要强政府的系统性解决方案。”郑永年对本报记者强调,“尽管目前欧洲各国难以出现强政府,但从长期来看,形势比人强,最终会逼出强政府。”
中国也难以置身事外。“如果欧盟解体,对中国也会造成重大损失。”郑永年强调,过去中国与欧洲由于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关系,所以对欧洲关注不多,但今天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欧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开始变化,因此中国应该增加对欧洲的关切。
欧债危机是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
《21世纪》:您认为,欧洲为什么会发生债务危机?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无论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是欧洲的债务危机,首先是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这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的崛起有关。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很快就发展到世界经济领域,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理想化,过度理想地认为全球化会形成一种完美的国际劳动分工,各国可以借其“比较优势”来促进无限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看不见的手”和“比较优势”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西方各国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经济结构失衡的道路。
具体来说,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产业转移所造成的不同产业之间的失衡。冷战结束后,很多欧洲国家加快了产业的转移,把大量的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甚至大胆地放弃了大部分制造业,而转向了高附加值的服务业。这就导致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失衡,在服务业中过分侧重于金融领域。
按理说,产业转移的目标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既可以在同一产业链上升级,即通过增加技术的含量来增加附加值,也可以通过把附加值低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而发展新产业来追求附加值。但不少欧洲国家在没有找到新兴产业的时候,就把一些已有的产业转移了出去。产业的转移必然影响到就业,而就业又转而影响消费和政府财政等方面。这次危机表明,凡是制造业仍然领先的国家(如德国),受危机的影响就小;凡是金融业发达的国家(如英国),不仅制造了危机,而且影响到本国的制造业。
其次是,产业转移之后,导致了社会性投资和生产性投资之间的失衡。因为很多产业转移了出去,实体经济空间大大减少,生产性投资缺少了目标。西方的很多生产性投资是通过FDI的形式投资到海外企业。企业的大量出走,也导致了政府税基的缩小。而在欧洲的福利社会,政府需要越来越大的社会投入,但同时国内的税基减小。那么,政府的钱从哪里来?政府只有搞债务财政。大多西方政府的债务财政节节升高,在背后有很多因素,但社会投入的负担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再者,由于产业转移之后,过于依赖金融业,导致了创新与投机之间的失衡。传统上,大多技术创新都发生在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但是,在欧洲不少制造业被转移出去,或者制造业空间缩小,技术创新显得不足。因此,这些国家的企业把大部分财力用来搞金融创新。尽管金融创新也很重要,但这往往和投机或者冒险联系在一起。在很多情况下,金融工程和投机工程没有什么两样。而种种金融投机又反过来弱化实体经济。这次金融危机就是因为美国的金融资本把美国的实体经济(房地产)过分货币化的结果。
欧盟不能解体是解决危机的底线
《21世纪》:就当下而言,您认为应如何解决欧债危机?
郑永年:既然欧债危机已经政治化了,那么最后还是需要通过政治方式。欧债问题本身是经济危机,如果解决不好就会演变成政治危机。要解决欧债问题,还是要通过政治的方式。政治方式如何解决?从历史上看,欧洲历史上也经历过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最后还是出现强政府来解决这个危机。所以像英国人现在非常怀念丘吉尔、撒切尔,美国人也非常怀念罗斯福等政治强人,因为政治强人用政治权力来解决危机的能力非常强,手段非常有力。
从目前的欧洲来看,我们还看不到怎样产生这样的强政治、强政府。无论是社会还是资本,大家都不能做出让步,社会不想放弃福利,资本也不让步,政府要么讨好人民,要么讨好资本,但这两者都难以产生有效的政府。
如果不能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干预经济,欧洲经济就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呈现危机、衰退和滞胀的状态,但同时也要警醒,强有力的政府也可能给世界带来的威胁。但从长期来看,形势比人强,我觉得最终会出现这样一个“强政府”。
《21世纪》:既然欧债危机的解决需要“强政府”的出现,而目前希腊、西班牙已经完成了换届,法国正在进行大选,您认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未来的表现有何预期?您认为,他们对于债务危机的解决能起到什么多大作用?您对他们未来的表现有何预期?
郑永年: 我觉得现在的处理效果还是不错的,应付危机不错。包括意大利的政府出现了一个由经济学家领军的专业人士组成的政府。不久前他们通过了一些新的措施,欧洲克服危机是比较长的过程,克服过程中也有很多磕磕碰碰,最终我还是觉得它会走向一个比较积极的方向。
我把他们现在做的事情称为“救火机制”,就是着火了他们要去做。但是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比如传统产业资本主义、制造业资本主义跟金融资本主义,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跟现在大众民主,大众民主跟资本主义之间,各种矛盾都很多。
尽管存在这么多结构性矛盾,但欧盟无论如何不能解体。如果欧盟一解体,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牺牲品,没有一个国家会赢的,大家必须把欧盟保住,这是一个非常明确也非常重要的底线。甚至对中国、美国来说都一样,也要保住欧盟。欧盟一解体,不用说其它政治问题,单是整个世界经济就会完全呈现另外一种情形。 所以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底线,到最后会保持这个体制。
《21世纪》:在欧美都出现大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他们都想拉拢中国,中国应该如何处理与美国、欧洲的外交关系?
郑永年:美国金融危机刚开始时,世界普遍认为,美国和欧洲之间跨大西洋联盟的合作,就可以克服这次金融危机。那时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并不在欧美政界和学界的话语中。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这次危机的深刻程度远比人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深刻得多,不但美国出现了危机,很快欧洲自己也面临了严重的债务危机。
另一方面是欧美在应付危机上的不同思路。要欧美联合起来,也存在一些困难。欧洲和美国很难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因为两者的思路不一样。欧洲最先看到美国的金融霸权的腐败性和危害性,欧元体系产生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制衡美元。尽管欧洲众多国家目前的经济很难整合,欧元尚无能力成为与美元对抗的基础货币,但其基础形式已经在那里了。
因此,无论欧洲也好,美国也好,都无法单独解决这场危机,所以他们都在争取中国,毕竟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我个人觉得,这种单一选择太简单。从实际政策层面来看,中国可能会选择美国,因为从战略上考量,中美两国的经济依赖度非常高。中国当然应该帮助美国,这也符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利益,但如果一味帮助美国恢复它的经济地位,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从长远来看,无论光选择美国,或者光选择欧洲,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性,中国应该同时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做一个平衡,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欧洲重视不够。最近国家领导人访问欧洲,表明中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21世纪》:为什么过去会存在对欧洲重视不够的问题?
郑永年:我认为一直以来,中国对欧洲强调得不够。这有多种原因:中国和欧洲基本上没有地缘政治的关系,没有国家安全上的问题,中国与欧洲的主要关系是经贸关系。但是,实际上正是因为没有国家安全问题,没有地缘政治上的关系,欧洲一些经济体反而更有可能对中国开放,要比美国开放。
从中国的长远利益来看,要将欧洲考虑进来,欧元作为对美元制衡的基础货币非常重要。就像冷战期间,中国、美国和苏联三者,在经济上形成一个平衡。当然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情况和冷战时期有很大的差别。但道理还是一样。如果中国过于依赖美国,国际空间会远远小于中国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做一个平衡。后者的国际空间反而更大,也比较符合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国在外交上应该增加对欧洲的关切。
《21世纪》:具体到中国与欧洲的外交策略上,目前还有哪些可以努力的领域和空间?
郑永年:中国对欧盟的理解不要过于理想化。欧盟在内部还没整合好,目前只有欧元和议会,比如老欧盟成员国和新欧盟成员国之间差异很大,需要进一步的整合;又如对目前欧债危机的理解也没有形成统一共识,还必须依靠一个一个国家的努力。因此,中国在与欧洲相处的过程中,单是与欧盟打交道比较难,彼此关系很难有实质性改变。承认中国在WTO的市场经济地位和取消对华武器禁运,这两点欧盟都不支持,尽管这两点对中国已经没有实质性意义,但由此可以反映出欧盟的意识形态依然很浓厚。
因此,我主张在对欧外交战略上,中国在与整体的欧盟打交道的同时,也要重视双边的关系,通过双边的关系的突破推动中国与欧盟的关系。
《21世纪》:4月26日,温家宝总理出席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举行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议,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此您如何评价?
郑永年:包括中东欧在内的新欧盟成员国家在内,中国对欧洲各个国家的了解都很少。即便是过去打交道比较多的老欧盟成员国,中国对其了解也仅仅限于经贸方面,而在文化政治、地理和历史等诸多方面了解不够。因此,应当增强对欧洲的了解,再从战略上挑选一些重点国家进行不同领域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