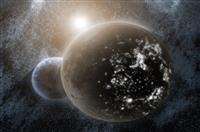如果读者不是反社会型人格或者精神病态者,那么《发条橙》的第一部分就很容易让读者引发不适。因为《发条橙》的第一部分讲述的都是主角阿历克斯及其同伴的犯罪行为。
而且为了与《发条橙》的后半部分形成对照,作者安东尼·伯吉斯竭力把阿历克斯塑造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徒,他的恶行几乎触及所有道德底线:殴打老人、抢劫店铺、盗窃汽车、擅闯民居、轮奸妻子、街头火并、诱奸女童……除了故意杀人,阿历克斯几乎违背所有的道德法律。而且种种暴行只发生在短短的一天一夜,阿历克斯还只有15岁。
在《发条橙》电影上映后,伯吉斯提到,他之所以把阿历克斯塑造成一个无可救药的恶徒,是为了把《发条橙》变成一本宣教书,以告诫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是何等重要。
《发条橙》的创作时间是1961年,当时的英国年轻人因为对战后世界的不满而充满暴力倾向,以至于当时英国媒体讨论的都是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新闻。
针对这种社会现象,有人提出可以通过某种矫正疗法让他们对犯罪行为感到不适——比如一旦产生犯罪念头就感到恶心,以此来迫使他们一心向善。
这种观点一度从民间理论上升为政府提案,而伯吉斯编写《发条橙》的最初目的就是反对这种观点。
伯吉斯试图在《发条橙》中阐述的是,一个人们可以凭借自由意志选择作恶的社会,要优于一个人人被迫为善、毫无选择权的社会。
在伯吉斯看来,善良是靠抉择实现的,如果你失去选择的权利,如果你的自由意志被社会教条替换,你也就无法被称之为“人”,而只是一台机器。就像一个被装了发条的橙子,内部的自然生机完全被机械的发条取代。
为了到达这一目的,伯吉斯在《发条橙》的第二部分杜撰出一个路多维克疗法——一个整合经典性条件作用和操作性条件作用的矫正方案,并让锒铛入狱的阿历克斯作为试验品接受了这一疗法。
路多维克疗法的矫正过程和矫正成果的呈现是《发条橙》的最大亮点。伯吉斯的细节刻画将政府是如何以正义之名包装恶行,如何以善之名践踏生而为人的尊严展现的淋漓尽致。
路多维克疗法的矫正过程极为简单粗暴,而且可行。其核心就是先给被矫正者注射路多维克试剂,以缓慢引起恶心的生理反应;之后再将被矫正者固定在看台上,逼迫他观看各种暴力行为视频。一天两次,一次半天,一连两周。
路多维克疗法的目的就是在暴力行为和恶心反应之间建立条件反射,以使被矫正者一旦产生暴力念头就会被恶心所淹没,而不得不选择行善。
然而路德维克疗法中矫正者的行径却与入狱前的阿历克斯全无二致:对他人施加伤害并以此为乐。就像阿历克斯因为痛苦而哀求停止时,得到的反馈却是“我们才开始呢”以及满屋的哄堂大笑,似乎只要暴力行为师出有名,并且加以伪装,就变得合法合理——就像政府专事镇压人民并以此为荣。
而路德维克疗法最终效果的呈现则完全践踏应有的人权。为了检验阿历克斯是否真的不会做出暴力行为,人们极尽羞辱之事;而为了避免被恶心淹没,阿历克斯却只能选择卑躬屈膝,甚至跪在地上舔羞辱者的靴子——这一幕总让我想起《1984》里被迫承认“2+2=5”的温斯顿。
从这一刻起,阿历克斯不仅失去作为人的尊严,还只能做社会认可的事,就像一台专做好事的发条机器。
如果说《发条橙》的第二部分令人惊艳,那么发条机器出狱后的第三部分就有点乏善可陈。如果伯吉斯的目的是宣扬自由意志、反对矫正疗法,那么第三部分的核心应该是发条机器出狱后所面临的困境——以此来证明矫正疗法的弊端。
自我保存永远是生物的第一要义,每个人都需要适当的暴力,来与侵犯者进行斗争。然而矫正疗法却将这一权利彻底剥夺,因此当发条机器出狱后,原先的强弱关系就会完全颠覆,发条机器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新的受害者——还会在别人打完左脸后再把右脸伸过去。
我原以为伯吉斯会呈现这样一个困境,从而证明,矫正疗法什么都无法改变,还会剥夺生而为人的尊严,除非所有人都成为发条机器。
但伯吉斯没有,他把《发条橙》的第三部分打造成一场政治斗争。反对矫正疗法的人把发条机器作为工具,来推翻现任政府,并且在计划成功后,恢复了阿历克斯的本来面目。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第三部分和前两部分就有些格格不入,就像一部小品从家长里短突然上升到家国情怀。
而且在最后的最后,当阿历克斯真的决定放弃原有的生活,而寻求一个安稳的生活时。他把过去的犯罪行为全部归咎于青春,叫喊着青春是一头野兽,青春是发条机器,青春总会过去……
似乎伯吉斯写到最后早已忘记阿历克斯在入狱前犯下的都是什么罪行,而只想为其谋求一个好的结局,然后随便找个理由为他的恶行进行辩护。
这不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