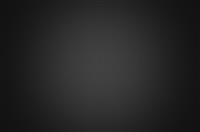世界经济就像一台陈旧的机器,不时发出恼人的噪音,人人都知道它出了问题,但连最优秀的机械师也无法确定故障所在。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就一直在复苏之路上蹒跚。从官方宣布衰退结束至今已过去60个月,美国经济依旧踯躅不前,呈现着经济增速和新增就业双低的态势。
此外,我们还发现,即便利率已创下历史新低,怀揣着巨额现金储备的企业们却依旧不愿投资到那些可能促进发展的创新活动。这不禁让我们深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何在?是缺乏市场机会,还是管理者缺少识别机会的慧眼?企业这种行为与整体经济不振有何联系?到底是什么在拖累经济增长?
用大部分经济发展理论观察宏观经济层面,就像从3万英尺的高空鸟瞰全局,我们能轻松发现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机制。然而要理解推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就要深入到公司内部,并探究公司高管的思想,因为他们才是投资并管理创新的人。本文基于克里斯坦森2012年末在 《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撰写而成,目的就是通过考察公司的具体状况,建立起一种自下而上的创新理论。
经过研究,我们厘清了管理者作茧自缚,不敢投入到他们认为高风险的创新活动的原因。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类型的创新对经济和公司产生的影响天差地别,然而人们却用完全相同且不完善的标准对它们进行评估。换言之,运用现行金融市场和公司使用的评估标准的结果,就是让缩减工作岗位的创新比创造就业机会的创新更具吸引力。这种标准来自一种过时的假设,借用作家乔治· 基尔德(George Gilder)的话:资本是一种“稀缺资源”,人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资本。然而资本已不再是稀缺资源,美国企业拥有1.6万亿美元的现金储备这一事实就是例证。要想让这些现金的回报率最大化,企业就必须转变将其视为稀有资源的看法。我们认为,与现金相比,吸引并有效配置人才,进而抓住发展机遇的能力才是当今真正的稀缺资源。要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评估投资的工具以及对稀有资源的价值判断都亟需更新。
在提出解决方案之前,我们先要分析创新的类型。
三种创新
在研究公司间竞争状况时,克里斯坦森提出过影响深远的颠覆性创新和维持性创新概念,这种分类是基于市场新进入者挑战传统公司统治地位的不同阶段。本文则聚焦于创新的结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需要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对创新进行分类。
性能提升型创新体现为新产品替代旧产品。一般情况下,此类创新产生的新工作岗位十分有限,因为新产品是替代性的,一旦消费者购买了新产品,就不会再购买旧产品,比如购买了一辆丰田普锐斯后,你不会再去买一辆凯美瑞。在《创新者的解答》中,克里斯坦森将这种创新称为维持性创新,所有成功的传统公司都会试图不断复制此类创新,因此会为其配置大量资源。
效率提升型创新是帮助公司以更低的成本制造成熟产品或服务,以便用更低价格出售给原有客户。我们将该类创新中的某些案例称为低端颠覆,它们常常会引发商业模式的创新。例如沃尔玛就是零售行业的低端颠覆者。此外,此类创新还可体现为流程改进,例如丰田的零库存生产系统。效率提升型创新有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是提高生产效率,这对保持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但会带来痛苦的副作用:削减工作岗位;二是释放资本,使其运转更高效。丰田的生产系统让公司原本两年的库存周期骤减为两个月,帮助公司释放了大量资金。
市场创造型创新则是通过对复杂或昂贵产品进行革命性的改进,吸引新的消费者群体,创造出全新的市场。计算机的发展是此类创新的代表。最初大型机造价高达几十万美元,且仅供一小批专业人士使用;个人电脑则将价格降至2000美元,使消费者群体扩充至几百万人;现在智能手机只要200美元,从而将消费者群体扩充至全球数十亿人。此类创新频繁出现,几乎形成了定律:只要某种产品或服务的技术或价格门槛极高,那么就有可能从中发现并开辟出新市场机会。
市场创造型创新有两个关键前提。一是要有能提高产量,同时降低成本的技术进步。二是要有新商业模式,即能够通过大幅降价,将非客户转化为客户的能力。如果运用得法,效率提升型创新也能将非客户转化为客户,从而成为一种市场创造型创新。最经典的案例是福特的T型汽车。由于本身设计简洁,加之福特独创的生产线系统,T型汽车的制造形成规模效应,造价大幅降低,让大多数美国家庭负担得起,福特从此开辟出私家车市场。同理,德州仪器和惠普采用固态元件技术,将低成本的计算器普及到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工程人员。
进行市场创造型创新的公司往往能产生新工作岗位。随着客户不断增多,公司需要更多的员工来进行生产、分销、销售和后勤保障工作。此外,公司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以及依托创新形成的新平台上的合作伙伴,也会产生大量工作岗位。贝塞麦转炉于1856年获得发明专利,史无前例大幅降低了钢铁冶炼成本。安德鲁·卡耐基利用这种革命性技术建立了汤姆森钢厂,价格廉价的钢铁催生了铁路产业。在19世纪最后25年,美国钢铁业的雇员人数增长了3倍,在1900年达到18万人;20年后,铁路产业的雇员人数达到180万人。
降低成本的技术同刺激消费的市场远见相结合,将满足新顾客需求。这常常引发革命性创新。10年前,苹果公司试图寻找一种价格低廉,轻巧便携的音乐储存介质,让人们能随时随地享受音乐。得知东芝正在开发1.8寸硬盘,苹果公司意识到机会来临,此后它不仅开发出iPod,更创建了以iTunes为中心的平台商业模式。如果特殊玻璃和材料制造商康宁和电信公司Global Crossing当年没有铺设足够多的低成本暗光纤网络,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也许根本不会存在。
市场创建型创新的发展需要资本,甚至是巨额资本,但同时会产生大量工作机会,当然创造就业机会不是创新目的。每时每刻各行各业中都有效率提升型创新发生。如果运用得当,我们就可以大幅降低产品成本,并使产品更易于获取,这样就不必削减工作岗位,甚至能创造新就业机会。
3种创新的不同组合,都会对国家、行业和公司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如果能将用于效率提升型创新的资本投入到市场创造型创新中,我们的经济将受益匪浅。然而这种假设实现的难度颇高,我们将在后文中阐述。
被恪守的旧信条
回到开篇的问题:公司为什么青睐削减职位的效率提升型创新,却对能带来工作机会的市场创造型创新敬而远之?答案是一个未经验证的经济假设:资本使用效率是判断公司表现的惟一标准。这种假设根深蒂固,几乎已成为信条,它严重影响了投资者和管理者对市场机遇的判断。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资本主义的窘境”。
让我们追溯这一经济假设的来源。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如果制造产品或服务的原料供应充足且价格低廉,例如沙土,人们就不会珍惜这种资源,甚至会挥霍浪费。但稀有昂贵的资源则必须小心谨慎地管理。一直以来,资本是稀缺昂贵的资源。因此投资者和管理者都被灌输这样的信条:要让每一美元资本带来的收益和回报最大化。
今天我们依旧需要谨慎管理稀缺资源,但资本已不在其列。贝恩最近的分析很好地阐述这了一观点,该分析认为,目前已经进入到“资本极度过剩”时代。贝恩预计,当今全球金融资产总和是同期产品和服务产出值的10倍,随着新兴经济体金融部门的发展,到2020年,全球资本还会增长50%。我们其实已经淹没在资本的海洋中。
由于人们笃信资本效率的重要性,金融界衡量利润能力的工具,早已不是美元、日元和人民币,而是净资产回报率(RONA),投资资本回报率(ROIC)和内部收益率(IRR)等财务指标。这些指标仅是分子与分母的简单之比,却给管理者带来了更多提升业绩表现的手段。为了提升RONA或ROIC,管理者一般通过提高利润来增大分子;如果这样做有难度,他们就会致力于缩减分母——公司资产,也就是尽量外包。同样,他们既可以通过提高利润,也可简单地缩短回报周期来提高IRR;要知道,在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只需投资那些短期见效的项目,IRR就会自然提高。
相比之下,市场创建型创新就没有这样的投资吸引力。因为这类创新的投资回报期需要5到10年,而效率提升型创新只要1到2年就能见效。更糟糕的是,前者需要大量资本才能形成规模;而后者则会减少公司资本规模。此外,效率提升型创新的风险看起来要小得多,因为其市场已经存在。当你用财务指标衡量这些创新时,效率提升型创新无疑会胜出。
长期投资者在哪里
有人想当然地认为,短期投资者青睐上述财务指标;而机构投资者会更看重长期价值创造,后者的投资可以抵消投资短期化倾向。实际情况却与这种猜想大相径庭。养老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基金种类,总资产超过30万亿美元,仅美国养老基金规模就近20万亿美元。理论上,养老基金应该最具耐心,然而大部分养老基金都没有展现出应有的耐心,它们甚至还引领了追求短期回报的潮流。我们的合作者剖析了养老基金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模式。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整体回报率低,潜在的未履行出资承诺和人均预期寿命增长等。这些因素致使养老基金的成长速度不够快,无法履行日益沉重的义务。因此它们不得不追求短期回报,并要求被投公司及其管理者达到苛刻的要求回报率。如果无法调整过高的收益预期和要求回报率,未来养老基金的发展就愈加艰难,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风险投资基金(VC)一般被认为不太在意公司的短期回报,因为它们对市场创建型创新更感兴趣。很多VC确实如此,但也有很多VC热衷于投资那些从事性能改进型和效率提升型创新的初创公司,这些公司创业就是为了在一两年内出售给大行业孵化器。我们的合作者在与VC沟通时发现,很多VC青睐的创业计划都有同成熟公司一样清晰明确的市场定位。
降低资本成本会鼓励管理者和外部投资者冒险吗?从技术角度来看,目前资本成本确实很低,美联储的再贴现率已接近零。然而问题是,企业界和投资者从未从中受益,主要是由于苛刻的资本回报率要求推高了实际的资本成本。创业者经常在商业计划里宣称,投资者能得到5倍的投资回报,VC对回报率的要求更高。就连公司内部商业计划也通常要求20%-25%的回报率,因为回报率必须与企业历史权益资本成本持平。投资者和管理者都被灌输:投资价值计算要以企业成本为基础,辅以不同风险系数的加权。因此当真正寻求资金投入时,资本成本要远高于零。
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是,投资者获得的实际投资收益在不断减少。与此前情况大不相同,如今任何一个有前景的商业机会都会被大量公司和投资者觊觎。激烈竞争导致交易成本上升,使投资回报大打折扣。近10年来,VC投资的总回报率每年都在递减。威廉·萨尔曼(William Sahlman)教授将这种现象称为“资本市场近视症”。
每年美国公众公司的商业计划都会涉及对新市场的投资。只要对这些公司的研发预算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只有很少一部分预算被投入到市场创造型创新中。还有一部分预算用于性能改进型创新,绝大部分预算则用于效率提升型预算,比例之高甚至超过公司管理者的预计。我们的合作者还提到了近年来逐渐流行的“研发成本回报指数”(RORC),该指数是当年利润与上一年研发费用的比率。该指数的出现使得公司更加偏爱前两类创新。
令人失望的是,目前的资本分配更青睐那些瞄准现有客户的投资,而对新市场中高成长、高利润的机会视而不见。这导致了悖论:企业在看似容易获利,实则竞争惨烈的成熟市场中激烈拼杀,却不顾在规模、利润和机会方面的广阔蓝海。本文一位合作者是一家老牌《财富》100强制造企业的产品经理。他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抛弃了投资组合的概念,几乎每一项投资的目标都是要提高公司的关键财务指标。”其结果就只能是那些旨在提升效率的短期计划泛滥。“如果我提出不同意见,上级的反应是’这个点子听起来很有趣,本财年结束后我们再讨论吧’”。
这些问题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其结果是,原先为资本主义系统提供润滑作用的机构失灵。尤其是银行,它们对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商业贷款缺乏热情,而这些贷款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命脉。银行惜贷也会对银行系统自身造成永久性伤害,因为新的借贷机构会应运而生,填补银行留下的市场空白。美联储的作用也被削弱,因为美联储刺激经济的两个主要手段是加强货币供给和维持低利率,然而目前利率已不再是企业成本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窘境。按照现行的投资评估指标(例如净资产回报率),那些聚焦于长期投资的行为反而会损害大部分投资者的利益。我们越是想将资本回报最大化,我们获得的回报就越少。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对开拓新市场进行资本支持,然而目前的资本持有者却对资本主义失去了兴趣。如果任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窘境会将迫使我们进入“后资本主义时代”。亚当·斯密曾说,“看不见的手”会高效地分配资本和劳动力,将它们带向价格和回报上升领域,反之资源就会撤离。在“后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本成本的降低,“隐形的手”失去了指导作用,无法把资本引导到最需要它的地方。
四方法重建
造成问题的原因简单直接,但解决问题复杂困难得多。下面我们将提供4个值得探索的方案。
1 引导资本流向
与资本供给方不同,资本本身是可塑的,特定的政策可以引导资本流向。我们将今天的资本分为3类,其中大部分资本是迁移性资本,它们不停流动,没有固定方向。投资后,迁移性资本会尽可能快地退出,在此8、之前,它们还会拿走尽可能多的其他资本。第二种是避险资本,大部分此类资本以现金和等价物的形式,栖身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由于其避险的天性,企业宁愿固步自封,也不愿冒险去投资。最后一种是创业型资本,这种资本一旦被投入到公司中,就不会轻易退出或迁移。要摆脱资本主义的窘境,我们需要想办法将前两种资本转化为创业性资本。
一种方法是通过税务政策。本文合作者建议对金融交易征收托宾税,遏制高频交易,从而将资本推向创新投资。设计和实施新托宾税绝非易事,然而越来越的学者和从业者都建议,延长股东的持有期会对资本起到引导作用。
从企业角度讲,公司可以奖励忠诚的股东。我们的合作者提出了几种方案,其一是让股东权利随持有时间增加而增加,就像员工股票期权一样,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增加股东的投票权。提案者向我们解释:那些投机者持有股票的时间只有几周或数月,他们凭什么拥有和长期股东同样的投票权?另一种方法是设置奖励股票或奖励分红机制,人们将其称之为L股票。其中最流行的一种L股票方案是,如果股东在某个特定时间段持股,那么他们将会获得特定时间期限和特定价格的认购权证。
这些提高股东忠诚度和促进长期投资的方案还处于实验起步阶段,各方博弈将会影响到其效果,但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股东大会的公告和招股说明书中。
2 革新商学院教育
我们必须痛心地承认,出现资本主义窘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商学院,包括我们任教的哈佛商学院。在进行商业和管理学教育时,我们总是循规蹈矩地把学科分开,而很多学科知识必须要在交叉互动的情况下才能正确理解和掌握。而现行的某些成功标准常常浮于表面,极端情况下甚至误导学生。
在大多数商学院中,战略和财务课程都是分开传授的,好像战略的设计和执行不需要财务的支持。然而在现实中,即便最优秀的战略也要受财务部门的制约,除非我们能找到一种新的方法,让这两个部门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制定投资决策,否则财务指标永远比战略更重要。如果我们无法改进这种“竖井式”的学科设置和教学方法,即便最顶尖的商学院也会逐渐落后于公司和未来管理者的实践需求,而这些学院毕业生的目标正是担任公司未来管理者。
此外,商学院不会教授学生资源分配带来的复杂作用,这导致商学院毕业生完全不了解投资决策对公司其他部门的影响。对此一位合作者说:“关于如何选择投资项目,我们只在哈佛商学院的财务入门课程中学到一些皮毛。”直到从商学院毕业,很多关键的课题也未被涉及,例如:如何辨认长期投资机会?在评估对新市场投资时,用何种指标估算未来现金流?如何进行创新将非客户转化为客户?传统的IRR和NPV指数应该在那些情况下使用,而在哪些情况下它们会具有误导性?在企业中,各个职能部门都相互合作且互动频繁,商学院的不同院系必须对这种现实做出反应。
3 协调战略&资源
关于资源配置对市场创造型创新的歧视,合作者讨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的共同出发点是,在机会评估中调整资本的风险成本。如果能了解资本的真实成本,人们进行长期投资的动力就会增强。
大部分合作者还指出了提高研发开支透明度的必要性。例如设立一种“创新积分卡”,管理者可以将研发开支分配给不同的创新类别。这种方法为管理者提供一个内部工具,用来分析公司的创新流程和蕴含的发展前景。
4 解放管理者
很多管理者希望进行长期投资,然而常常会感到有心无力。如今投资者持股期的中值是10个月,因此高管会面临短期回报最大化的压力。很多高管担忧,如果他们无法达到财务指标,就将自身难保。管理者的工作因此退化为利用各种手段提高财务数据,为股东带来短期收益。
在大多数公司中,无论公司上市与否,尽管有很多短期投机者,但还存在着大量战略投资者。两类投资者的利益已发生分歧。要满足一方的诉求,另一方的利益就会被损害。再完美的战略也无法为所有股东带来最大化的收益,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最大化企业的长期价值。管理者和商学院的职责就是开发出新的工具来支持这种做法。首先他们要做的是将财务指标视为决策的辅助工具,而不是战略的替代品。
问题不在于工具,而在于我们自身。就像一位合作者提到的,工具和指标的作用从未改变,ROA是资产回报率;DCF是现金流折现法。问题在于我们理解和应用这些指标的方式。几十年前,德鲁克和莱维特呼吁管理者不要被产品和标准分类所束缚,要记住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客户。如今我们要重拾这一管理精神。
当人们无法理解周围环境及其产生原因,就会陷入窘境和矛盾的陷阱。这就是为什么创新者的窘境曾让无数明智管理者无计可施,坐以待毙。一旦了解窘境产生原因,管理者就能在面对颠覆时有效应对。现在我们正面临资本主义的窘境,我们希望本文能敲响警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工作中,找到有效解决方案。这不仅仅关系到某个人或某家公司的利益,更是为了我们所有人的长期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