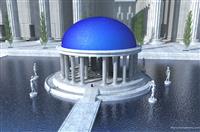【专题名称】文艺理论
【专 题 号】J1
【复印期号】2001年06期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2001年01期第126~132页
【作者简介】樊星(1957-),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思潮的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20世纪中国作家接受俄苏文学影响的历程的勾勒,揭示了俄苏文学的道德感、抒情风格在塑造中国文学现代品格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论证了中国作家在兼收并蓄世界文学丰富成就的过程中显示出的超越性,并指出了中国文学与俄苏文学的差距。
【关 键 词】俄苏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兼收并蓄
中图分类号:J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1)01-0126-07
鲁迅曾经说过:"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1](p460)鲁迅的这段话,与英国作家吴尔芙和美国学者布朗有关俄苏文学的评论正好相合:"如果我们寻求对灵魂和内心的理解,那么我们在哪里还能找到如此深刻的理解呢?……我们从所有俄国大作家身上都可以看到圣洁品德的特征。正是他们这种圣洁的品德使我们为自己的没有灵魂的天真品质而感到羞愧,并且使我们的如此赫赫闻名的小说家们变成虚饰和欺骗。俄国人的理智是如此真挚而又富于同情心,其所得出的结论因此恐怕也必然充满不可解脱的哀愁。"[2](p438)"在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俄国文学可能是最伟大的。二十世纪自1917年革命以来,俄国文学……仍然是光辉灿烂的文化之一。"因为"俄国作家不仅满足了美学经验,也满足了思想的需要。大多数作家都充当了教育者和鼓舞者的角色。"[3](p48-59)俄苏文化之所以格外能够打动20世纪中国文化人,与俄苏文化中的强烈道德感、鲜明理想主义精神密切相关,也与俄苏文化中博大、恢弘的气质,感伤、抒情的风格有关。因此,研究俄苏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就成了揭示20世纪中国文学品格的要素之一。
一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指出:"在俄罗斯,道德的因素永远比智力因素占优势。"[4](p13)在俄苏作家的创作中,深重的道德感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弱者、对受苦受难的大众寄予真挚的同情与悲悯,对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进行猛烈的批判。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赫尔岑都出身于贵族、地主之家,可他们都对黑暗的农奴制、对贵族、地主阶级的腐败作出了无情的揭露与抨击,对小人物的不幸进行了感人至深的描写,并企图在他们的作品中对"怎么办呢?哪里更好些呢?谁是有罪的呢?"之类问题作出解答[5](p6-7)。在这方面,他们也深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对黑暗的批判、对正义的呼唤与伏尔泰、雨果、左拉、易卜生的正直一样,都是人道主义、理想主义情感的证明。不过,相比之下,西方人道主义的呐喊似乎更富于慷慨激昂的锋芒,而俄国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感更多表现为深沉、感伤的忧思和叹息。这里是人道主义情感的两个境界。它们昭示了不同的民族精神、不同的文化品格。在西方作家慷慨激昂的呐喊声中,体现出西方民主主义精神的深入人心;而在俄罗斯作家深沉、感伤的忧思和叹息中,则隐隐使人感受到东正教的悲凉精神。
第二,建立在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感和民主主义情感之上的民粹主义精神。因为同情受苦的民众而与他们共命运,直至由于良心的感动而产生"罪孽和忏悔意识",由于热爱人民而"企图模仿人民的生活方式"[4](p103)。托尔斯泰为自己的贵族生活而痛苦的情感、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苦难理想化的情感都是民粹主义情感的典型体现。这种情感是俄罗斯作家最突出的精神标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孽感、忏悔意识与卢梭在《忏悔录》中表现出来的罪孽感、忏悔意识虽然都发自肺腑,但前者那种近乎自虐的凝重感、痛苦感,那种将民众的痛苦与自己的情感紧紧相连的情感,又是与卢梭面对上帝的情感颇不一样的。俄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民粹主义情感是俄国后来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思想源泉。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传统。在20世纪追求国家富强、民族解放的事业中,他们自然会从邻国俄罗斯那儿找到自己的精神导师。
"五四"那一代作家大都受到过俄苏文学的洗礼。王富仁的研究表明,鲁迅是在经历过广为搜求、多方尝试、精心思考、严格选择的漫长路程后才格外注重从俄罗斯"为人生"的文学中汲取精神养分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执着而痛苦的追求激情、博大的人道主义感情,使鲁迅的小说显示出俄国文学的强烈影响。果戈理那"含泪的笑"、契诃夫的悲悯情怀、安特莱夫的孤寂与冷峻、阿尔志跋绥夫的消沉与悲观,都溶化在鲁迅的作品中[6]。周作人虽然最推崇英国心理学家蔼理士的学说,但也认为:"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因此,俄国的"主张人生的艺术"自然适合中国的文学家,"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7](p72)。郁达夫也说过:"世界各国的小说,影响在中国最大的,是俄国的小说"[8](p14)。他认同于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的人"形象,也神往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析病态心理的深邃。巴金从俄国十二月党人和民粹派那里找到了真诚无畏的力量,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获得了深沉又热烈、悲悯也感伤的博大情怀;茅盾多次谈及托尔斯泰给自己的巨大教益;艾芜的《南行记》中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高尔基的《草原上》等"流浪汉小说"的影响;艾青崇敬叶赛宁的抒情才华,也为马雅可夫斯基的豪迈所激动;夏衍、曹禺的戏剧创作也都深深打上了契诃夫的烙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作家的创作显然没能达到俄罗斯作家已经达到的阔大、深邃境界(是因为才力不够?还是因为急功近利之心太切?或者是像周作人指出的那样,有民族性方面的差异?(注:周作人认为:"俄国人的生活与文学差不多是合而为一,有一种崇高的悲剧气象……中国的生活的苦痛,在文艺上只引起两种影响,一是赏玩,一是怨恨。……概括的怨恨实在与文学的根本有冲突的地方。"对此,他从宗教、政治、地理等方面进行了大略的分析。参见《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载《艺术与生活》第73-74页。),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净化中国现代作家的灵魂,提升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境界与艺术境界所产生的影响,却可谓至深至远。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俄苏文学史上的新时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展开也催生了新的文学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理想主义已经不再是在忍从苦难中期待灵魂的获救,而是依靠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和集体主义的奋斗去建设幸福的人间天堂。早在大革命的年代里,苏联革命文学就开始影响中国的文坛。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等作品都在向往革命的青年心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思潮、40年代的"解放区文艺运动",都是苏联革命文艺在中国文坛上产生的回声。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呼唤革命的暴风骤雨,有意识地引导读者了解革命、参与革命,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成了从20年代的"革命文学"、40年代的"解放区文艺"到50~6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艺"、60~70年代的""文革"文艺"(虽然""文革"文艺"中不乏"帮派文艺"之作,但也有小说《海霞》、《闪闪的红星》、电影《创业》那样的革命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作品)一脉相承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在"文革"结束以后有衰落之势,但我们仍然不难从魏巍的《东方》、刘富道的《眼镜》、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谌容的《人到中年》、孔捷生的《普通女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郑义的《老井》、张承志的《金牧场》这样充满英雄主义气概和理想主义情操的感人作品中感受到苏联革命文学和新中国"工农兵文艺"传统的延续。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思潮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销声匿迹。它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多元化格局中不可缺少的一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是在苏联革命文学中,也不只是单调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之歌。除了《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深受热血青年喜爱、无可争议的"革命文学"经典外,苏联革命文学至少还包括以下几类作品:一,以《静静的顿河》为代表的,充满了情味和沧桑感的史诗性作品(小说真实展现了革命的画面,但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显然不属于具有共产主义情操的革命英雄人物之列);二,以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爱伦堡的《解冻》为代表的,敢于暴露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充满批判精神的"干预生活"作品;三,以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拉斯普京的《活下去,并且记住》、舍克申的《秋天》、贝科夫的《活到黎明》为代表的,苦苦探索伦理困惑,具有浓郁的感伤情调和哲理深度的作品。而在上述三类作品中,俄国批判现实主义针砭现实、追问人生的伟大传统,悲天悯人、深沉博大的真诚情怀,都依然在延续。这意味着,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并没有被苏联共产党人抛弃,而是深深融入了苏联革命现实主义的潮流中。无论是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还是在苏联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中,道德感、批判意识和忏悔精神一直灼然可感。正是由于苏联革命现实主义成功继承、容纳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才使苏联文学一直为世界文坛所瞩目,并产生了萧洛霍夫、艾特玛托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拉斯普京等具有国际影响的优秀作家。
苏联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给过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以决定性的影响。尽管中国的革命文学也产生了《小二黑结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吕梁英雄传》那样广为传诵的作品,但就如王蒙在晚年回首往事的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中指出的那样:"不论是赵树理还是周立波、康濯,他们总是不像苏联作家、俄国作家那样抒发丰富多彩乃至神奇美妙的内心。中国作家可能写得很幽默、智慧、通俗、激烈、尤其是真实、生动、纯朴,但他们从来不像苏联作家乃至旧俄作家写得那样美,那样丰满。这也许正是苏联文学里充满了幸福、生活、光荣、爱情,而中国的文学作品里净是被骗后的觉醒、翻身后的感恩、识破奸诈与显露忠诚……的缘故吧。"[9]苏联革命文学与中国革命文学在艺术境界上的差异正如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差距一样。也正因为如此,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才都对俄苏文学表现出格外倾心的深情。
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王蒙受到《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影响写出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周立波、刘绍棠从《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山乡巨变》、《青枝绿叶》就显示出《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影响;李国文在少年时代因《铁流》、《毁灭》的启蒙而走上文学道路[10];贺敬之、郭小川的"楼梯体"诗歌明显脱胎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体"诗歌;……苏联文学的理想主义热情、集体主义精神、现实主义品格哺育了新中国一代作家和一代青年。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两国执政党交恶,中国开展"反修"运动,苏联文学也被视为"修正主义"文学而受到错误的批判,直至在"文革"中成为"禁书"。但是,在那片文化沙漠里,还是有不少青年偷偷传阅着那些被禁的苏联政治、文学书籍--从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赫鲁晓夫的《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到爱伦堡的《人,
岁月,生活》、《解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叶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他》、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李巴托夫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在"文革"中的"地下读书"活动中,苏联文学作品较之西方现代派作品显然更加受到中国青年的喜爱,是颇耐人寻味的。这一现象至少表明:深受苏联文化精神熏陶的中国青年并不恐惧"修正主义"。他们似乎天然亲近深沉、感伤的苏联文学,而不是怪异、冷漠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更不是因为政治的不断挤压而明显缺少人情味和哲理感的中国当代文学。在"文革"的"地下文学"作品中,被认为奠定了"地下文学"基石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就得名于俄国画家埃瓦佐夫斯基的同名油画,小说主人公司马丽被欺凌而走向堕落的悲剧故事令人想起托尔斯泰的《复活》。("文革"后"伤痕文学"的名作《黑玫瑰》、《在社会的档案里》、《女贼》都是出于同一模式。)而在郭路生的诗歌《相信未来》、靳凡的小说《公开的情书》中,也充满了俄苏文学那苍凉又豪迈、深沉也激越的氛围。"地下文学"是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先声。
到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禁书"重见天日。俄苏文学的译介和传播再次涨起高潮,并汇入了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回归的洪流中。冯骥才的《啊!》令人想起契诃夫的《一个官员的死》;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与屠格涅夫的《木木》颇有相似之处,他的《绿化树》则是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的奇特结合;王蒙的《布礼》、《如歌的行板》、《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中,俄苏文学的情调总是那么浓郁;从维熙的"大墙文学"是索尔仁尼琴的"大墙文学"的某种折射;蒋子龙的"改革者文学"中,有李巴托夫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的影子;张炜的《古船》中的隋家父子身上,体现出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列文的精神……此外,张承志曾经说过:"苏联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给了我关键的影响和启示。"[11]王蒙也谈及他喜欢艾特玛托夫[12](p436)。他们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草原故事"(王蒙的《在伊犁》系列和张承志的《黑骏马》、《阿勒克足球》等)都富于理想主义的激情和感伤的色调,与艾特玛托夫的影响密不可分。王蒙的《杂色》以"意识流"手法写成,但是,"一个人与一匹马"的故事及其感伤、抒情的风格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艾特玛托夫的《别人,古利萨雷》。还有徐怀中的《西线轶事》,也显然受到了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启迪。具有不同经历、不同气质的中国作家,在文坛多元化格局中,在欧美文化新潮的不断冲击下,仍然不断从俄苏文学中汲取了多方面的养分,由此可见俄苏文学魅力的一斑。虽然王蒙在苏联解体以后,曾经反思过苏联文学的缺陷("沉重呆板有余而生机勃勃灵动飞扬不足";"一些杰出的苏联作家--例如法捷耶夫、费定和阿·托尔斯泰,无法摆脱他们的孩子气的虔敬恭谨,而终于没有能够尽情尽才地写出他们的传世之作。……另一些不错的作家--例如西蒙诺夫、苏尔科夫、柯切托夫、巴甫洛夫--有意去迎合意识形态的模式,而终于囿于已有的却是未经验证的武断之中。……还有一些杰出的作家--例如阿赫玛托娃或者左琴科、帕斯捷尔纳克以及可能有的没有被允许发芽的种子,--潦倒压抑,有花不能开"[13];等等),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坛上,英、美、法国的现代派文学乃至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已经明显大于俄苏文学,但是,俄苏文学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已经深深积淀在了许多中国作家的心灵之中。90年代是世俗化大潮高涨的时代。而在这大潮的冲击中高举起了理想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旗帜的作家们(例如张承志、张炜、梁晓声、史铁生、陆天明等人),都有相当鲜明的俄苏文学背景。在《九月寓言》、《年轮》、《务虚笔记》、《泥日》这些作品中,都弥漫着热烈而深邃、感伤又温馨、博大亦绚丽的气息。这一股思潮,是90年代多元化思潮中的一股热流。它与"新写实"的冷漠、"私人写作"的琐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另一方面,"重新发现俄苏文学"的思潮也将俄苏文学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发掘了出来。蓝英年在《读书》杂志、《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寻墓者说》就介绍了那些在苏联时代遭受厄运的作家们的命运:从革命作家高尔基的精神苦闷与神秘之死(《高尔基回国》)、法捷耶夫因为对斯大林失望而自杀(《作家村的枪声》)、马雅可夫斯基因为绝望而自尽(《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到不理解十月革命的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因为生活困难、家破人亡而自杀(《性格的悲剧》)、莫名其妙受到不公正批判的作家左琴科(《倒霉的谢皮拉翁兄弟》)……苏联文学史上的这些悲剧为俄罗斯文化精神中的道德感加了新的注释:知识分子为什么常常与现实格格不入?他们的受难意味着什么?1996~1999年间,作家出版社、上海学林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辽宁教育出版社纷纷推出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化与文学著作。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这些在思想与艺术的探索中坚忍不拔、孤独前行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写作表达了在苦难中追求灵魂获救、在忧伤中抒发高贵情感的思考。他们的书在90年代的中国流传开来,耐人寻味:在世俗化、商业化大潮高涨的时代,在"后现代主义"狂欢节的喧哗声浪中,在"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叹息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从俄苏文化遗产中汲取精神力量。有的评论家指出:"我们的知识界内心的确充满了困惑与渴望。""在我们这个没有激情的年代,这个被欺骗、软弱、埋怨和嘀咕所笼罩的年代里,中国作家和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派那隔靴搔痒式的模仿,造就了一大批术语玩弄家、技术权威、无病呻吟者、语言游戏者,最后弄得自己都腻了。"相比之下,""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俄罗斯精神的传承者,他们能做到不鼠目寸光,不为一时的现实功利所动,甚至不惜被流放,而执着于对俄罗斯的正义、灵魂获救等问题进行探索。这与我们十九世纪前辈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是息息相关的。"[14]"新生代"作家余华则从布尔加科夫在厄运中写成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中了解了"真正的写作";"现实的压制使他完全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他将自己的命运推入到想象之中。"[15]这一现象昭示人们:在当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重新建构中,俄苏的文化因素没有过时,而且不可缺少。知识分子的良知、特立独行的个性、追求理想的激情就这样通过那些在厄运中受难、殉道的思想记录渗透进了中国90年代不屑于与世俗化大潮认同的作家与学者的心中。与那些殉道者深沉的情感、忧伤的思想相比,狂欢化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就显得肤浅、苍白了。
二
20世纪的中国作家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不过,许多中国作家并不将自己的目光仅仅局限于俄苏文学。他们常常将世界各国文学的成果兼收并蓄。这使得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广泛接受世界文学影响的同时又于兼收并蓄中呈现出某种不拘一格的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又一次验证了历史学家钱穆指出过的中国文化特质:"中国人主通。"[16](p249)"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的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能融合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17])(p205)
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中就列举了他心仪的外国文学家的名字:德国的尼采、英国的莎士比亚、卡莱尔、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波兰的密茨凯维奇、匈牙利的裴多菲,在鲁迅看来,上述作家虽然种族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敢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鲁迅作品中的忧患意识、愤世情绪、冷峻笔锋,都显示了尼采、拜伦、果戈理的影响。巴金从卢梭、雨果、左拉、罗曼·罗兰那里学到了"把心交给读者"的真诚,从俄国十二月党人、民粹派(包括赫尔岑)、无政府主义者(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和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屠格涅夫、契诃夫那里学到了"旧俄的悒郁风",他的创作因此而兼有热烈与感伤的双重风格。王蒙早年倾心于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爱伦堡、屠格涅夫、契诃夫的"温柔和优美"、"感伤和叹息"、"对于庸俗与野蛮的谴责",后来既喜欢艾特玛托夫的优美,也迷恋美国作家约翰·契佛干净、清爽的文体[12](p434-436),并成功地将对革命的反思与"意识流"手法结合在了一起,写出了《布礼》、《蝴蝶》、《相见时难》那样的作品。张承志也将艾特玛托夫那"真正的抒情艺术"与海明威"那股透着硬的劲头"熔于一炉[18],既写出了《绿夜》、《黑骏马》、《老桥》那样的抒情作品,又写出了《北方的河》、《大坂》、《金牧场》那样的硬朗力作。上述例子表明,中国作家的胸怀是宽广的,他们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立场是兼收并蓄,而不是跟在某一国作家的后面亦步亦趋。而当他们在兼收并蓄外国文学的影响时,他们也就显示了某种努力超越外国文学影响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中国现代文学绚丽多彩、充满活力的原因所在。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作家是怎样成功将各国文学的不同色彩巧妙地融合为一的?
大略看去,这种融合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不同的创作阶段尝试借鉴不同的外国作家。例如巴金在早期的创作中主要受到法国作家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以真诚的激情呐喊;到了后来,随着体察社会的深入,他的创作风格与渐渐靠近契诃夫,由"热"变"冷"[19]。这时,兼收并蓄显示为"阶段性"。
二是在创作中同时采纳不同作家的风格。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的题目就来自果戈理的同名小说;《药》的风格"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20](p239);《头发的故事》、《孤独者》中也显示了阿尔志跋绥夫"冷中见热"的风格影响。这时,兼收并蓄显示为"杂糅性"。
三是将俄苏文学的主题、格调与英、美文学的创作手法融合在一起。例如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就是将"反思革命"的深沉主题、感伤风格与"意识流"的叙事手法融为一体。他的"意识流"创作因此而独具特色。张承志小说的抒情风格、浪漫激情来自艾特玛托夫,硬朗的风骨则脱胎于海明威。他也在这样的融合中写出了自己的个性。在这种情况下,兼收并蓄则显示为在包容异质文化基础上的"组合性"。
不拘一格的兼收并蓄使中国作家的创作也不拘一格。而当中国作家成功地将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颇不相同的各国、各流派文学熔于一炉时,他们也就别致地证明了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定律:"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21](p1)。在流派与流派之间、在不同的艺术手法之间、在千差万别的作家个性之间,竟然有那么多可以被才华巧妙穿越的通道。这正是文学的奇迹,也是文学的继承与创新之路之所以层出不穷的奥妙所在。
三
不过,尽管俄苏文学给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响,但中国文学中迄今为止没有产生出可以与《战争与和平》、《卡拉玛佐夫兄弟》、《静静的顿河》、《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并驾齐驱的文学巨著,又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中国作家为什么没能够写出史诗性作品?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人认为:"把"世界文学"作为参照系统……从总体上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对灵魂的"拷问"是几乎没有的。深层意识的剖析远远未得到个性化的生动表现。大奸大恶总是被漫画化而流于表面。真诚的自我反省本来有希望达到某种深度,可惜也往往停留在政治、伦理层次上的检视。"[22]许子东也表述过相似的思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忏悔"也还是不同于俄罗斯形态。或者说更像屠格涅夫的抒情式的悲天悯人,而很少真正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撕肝裂胆"。……由于历史文化等种种原因,除鲁迅、郁达夫等少数作家的有克制的试验以外,
大多数的20年代中国文人是不会忍心像陀氏那样"残酷"地对待自己和自己的艺术的。"[23]如果中国作家的主要问题不在才华的有限,而是在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缺乏对人性的深刻剖析,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的局限性就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20世纪中国作家过于执着、过于突出的政治意识(从"救亡意识"到"革命意识";从"革命文学论争"中党同伐异的宗派主义到"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政策造成的文艺界浩劫)妨碍了他们登上更高、更博大的人生与艺术境界,使他们写出了不少主题肤浅、艺术粗糙、急功近利的作品;中国作家对学习、模仿外国文学的热情虽然显示了历史的意志,毕竟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和人生洞察力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伴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政治压力的不断增强也常常迫使作家们(尤其是生逢"反右"、"文革"政治高压的作家们)放弃了独立思考的立场、自由探索的精神,在随波逐流中或苟且偷生,或误入歧途。
到了世纪之交的年代,作家们早已告别了被政治强力扭曲人格的悲剧命运,并且已经写出了一批能与外国文学优秀之作媲美的作品。然而,当代文坛仍然缺乏史诗性巨著,甚至连《古船》、《白鹿原》那样的当代长篇小说代表作也给人以虎头蛇尾、"半部杰作"的印象。原因何在?是因为才力不逮?还是因为思想不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什么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应有的成熟品格?中国文学应该如何在充分吸纳世界文学成就的基础上超越对外国文学新潮亦步亦趋的模仿?这些问题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似乎没有得到经典性、创造性的解答。这些问题表明:中国现代文学在建构自己的独立品格方面,还有一段路要跋涉。
显然,在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俄苏文学注定会继续扮演着"我们的导师和朋友"的角色,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收稿日期:2000-10-16
【参考文献】
[1] 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 当代文学[A].英国作家论文学[C].北京:三联书店,1985.
[3] 十月革命以来的俄国文学[A].欧美学者论俄苏文学[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4] 俄罗斯思想[M].北京:三联书店,1995.
[5]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6] 参见王富仁.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7] 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A].艺术与生活[C].长沙:岳麓书社,1989.
[8] 小说论[A].郁达夫文集:第五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
[9] 王蒙文集:第2卷[C].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10] 李国文.并非陨星的苏联文学[J].文学自由谈,1993,(4).
[11] 引自章廷桦.艾特玛托夫和他笔下的悲剧与神话[J].中国青年,1985,(2).
[12] 王蒙文集:第7卷[C].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13] 苏联文学的光明梦[J].读书,1993,(7).
[14] 张柠.白银时代的遗产[J].读书,1998,(8).
[15] 余华.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J].读书,1986,(11).
[16]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长沙:岳麓书社,1986.
[17]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18] 彼岸的故事[J].小说界,1993,(2).
[19] 参见汪应果.巴金:心在燃烧[A].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20]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1]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2]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1985,(5).
[23] 许子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张贤亮之间[J].文艺理论研究,19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