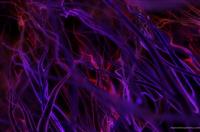
《诗经》不仅是我国诗的肇端,也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艺术特征,折射出中华民族反映和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的特点。
一、“赋、比、兴”——直觉思维的创作方法
“赋、比、兴”最早见于《周礼》,再见于《毛诗序》,且与“风、雅、颂”合称“六义”或《诗》的“三经三纬”。其基本含义历代大都承东汉郑玄之说:赋之言铺,直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比者,比方于物;兴,见今之类,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兴者,托事于物。郑玄的上述见解,二千年来未曾有太多的异议,问题是“赋、比、兴”本身早已成为中国文学创作乃至文学理论的发端,对它的探讨和研究绵延近二千年仍无穷尽,而本文认为,从文学艺术反映出民族思维方式的角度上来看,《诗经》中的“赋、比、兴”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首先,“赋”具有概括性、形象性、想象性的特征。《诗经》中的概括,已经完全不同于原始思维中那种对直观表象的概括。这种概括,融进了对复杂生活现象的丰富感受,人们的思维水平从自发的或自觉的表象运动,过渡到主体对客体的把握理解和创造阶段。表现在剪裁上精取约收,以少总多的表现手法。例如《卫风?氓》,诗的内容是一位劳动妇女,追述前夫当初向她求婚,结婚之后,过了三年辛劳勤苦的生活,家庭境况有了好转,而自己年过色衰,遭到无情遗弃的悲剧。这在当时的诗歌里,算是一个比较繁富的题材了。但诗人只用寥寥数笔,给读者展现了:氓幼年时代和悦说笑的样子,求爱时憨厚嗤笑的情态;女主人公的痴情和满腮擦不尽的涟涟泪水;淇水气势漭洋,浸湿了车帷,浸湿了裙裳;兄弟咥笑欢快的情景;女主人公静言思之的处境与神态、悲伤而孤独的内心……。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跃然纸上。
由此看出,《诗经》中的艺术概括性,并不是抽象化的叙述,而是伴随着许多具体的感性描绘、充满生动而有诗味的细节,从而构成生动的形象,使诗的概括性和具体形象性达到统一。它是主体对客体的整体把握和形式美的观照。《卫风?硕人》极尽描写了女子的美丽容貌,其中最为人传诵的是“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细玩诗意,它的妙处不仅在于使用巧妙的比喻,描写了美人的静态,而且后二句不用比喻的白描,使人物显得更有神采,更有风韵了。那不可捉摸的巧笑,那不可言传的流盼,使整个人物形象活动起来了。这里,它赋予我们一种审美的直觉。它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是她的纤手,也不是她的皓齿蛾眉这些单个部分,而是美人的体态与神态构成的整体和谐形象,并由此表现出来的气韵生动的精神风貌。
诗是靠想象发出光辉的,赋也离不开想象。它往往借助想象而腾越于悠远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显示出一种飞动性和跳跃性,表现出直觉思维的本质特征。在《小雅?大东》一诗中,描写主人公对不合理事情的憎恶,连天上的星宿也是空有其名而无实用:“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不仅如此,箕星的口张得大大的,好象要吞噬什么;斗星的柄高高地向着西方,它仿佛是帮助西人向东人进行掠夺的工具。这是多么奇特的想象!多么不平凡的表现手法!诗人借助想象“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陆机《文赋》)借助想象把广阔的社会生活凝聚在诗的形象里。如果说,想象是蕴含在我国神话思维中直觉的要素,那么在《诗经》里,想象已长出了翅膀,它将推动着民族直觉思维的成熟。
其次,“比、兴”具有类比与象征的特征。“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也。”(朱熹《诗集传》卷一)朱熹对比和兴所下的定义是准确的,概括出了它们的基本特征。比和兴虽然在具体手法上略有不同,但都是以他物来表现所咏之物。《诗序?正义》云:“比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当先显而后隐,故比居先也。”因此从形式上看,“兴”附托外物,多用于每篇诗之开头,为数极少的用于诗的中间。“比”附托外物,较“兴”更为普遍和多样化。
“比、兴”附托外物的目的是要表达“义理”。通过“比、兴”,设立不同的客观对象以深刻描绘主体的思想感情,并经过联想造成统一的气氛。因此,“比、兴”所附托的外物,和主体的感受和体验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的质的联系。一般说来,用于比、兴的事物对于正文所要表达的内容,往往起着象征的作用,起着“取譬引类”,“起发己心”和“环譬以托讽”的作用。选用比兴的事物是具体的,但是旁及连类所取得的艺术效果却是巨大的。如果从思维科学的角度上说,比、兴的过程,是直觉思维的过程,这种创作手法,可以叫作艺术上的直觉类比。
然而,这种艺术上的直觉类比对象,并不是同类事物。主体所托之物与所要表达的义理之间的某种内在的联系,并不能在普遍的有效的常规常理下推论出来的。相反,它完全是主体的直觉感受,是由创作的个体所产生的。当然,这种直觉的感受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建立在经验事实之上,建立在人们已有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是在经验基础上由于高度活动而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比较迅速的直接的综合判断。可见,这种艺术类比,带有超逻辑思维的特征。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没有严格的形式和规则,艺术类比才体现了一种灵活多变的创造性特点,使诗人在应用这种方法时,能够驰骋于丰富的联想与想象之中,在许多表面上看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对象中作出生动的类比。
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将客观对象的知识转移到主观感受的主观世界方面来,这是艺术类比。换个角度说,诗人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因此,比、兴也是一种象征。黑格尔认为:“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黑格尔《美学》第2卷,第10页)正是诗人从感性所观照的外在事物身上,找到了所要表现的对象之间某些类似之处,于是就用这些具体事物作比、起兴,进行象征。
这种象征首先是具体的,是具体事物构成形象,供人感性观照。“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睢》)用作起兴的事物是睢鸠。“关关”是其鸣,以听觉感知。“在河之洲”是其住所,以视觉把握。诗人既言其声,又绘其形,睢鸠是栩栩如生的形象。这些用作比、兴之物具有可诉诸感观的性质,是具体的形象。
其次,在这些象征中,思维对象始终没脱离人的感性直观。这正是艺术类比的重要特征。“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邺风?凯风》)凯风即南风,是温暖之风。以南风比喻母爱,都是取其温暖的性质。“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郑风?野有蔓草》)滴着露珠的蔓草和年青的姑娘,都具有清秀的特点,诗人从清秀上取像把二者联系在一起。
再次,这些象征又都是委婉含蓄的。比、兴虽然是创作主体对作品中的客观对象与主观对象的本质联系的一种把握方式,但在表现上却是不尽言、不直言、不明言。不尽言,就是不把内在的意蕴全部显露、一览无余,而是要有所保留和隐晦;不直言,就是不作直接地表现,而是以迂回曲折的方式表现;不明言,就是不以明白晓畅的方式表现,而是通过暗示发人深思。正因为如此,《诗经》具有委婉含蓄的特点。
可见,赋、比、兴的创作方法,体现了直觉思维的本质特征。这些方法具有极大的灵活多变的创造性特点,使诗人在丰富的想象与联想中来表现自己对客观现实的感受和体验。
二、模糊——直觉思维的语言表现
模糊性是直觉思维的重要特征。直觉既没有感觉、知觉那样实在具体和清晰,也不如纯形式逻辑推理、分析那样明晰和精确。直觉不能用形式逻辑方法来解析和定量说明。因而直觉的产生、过程和结果都具有模糊的特点。由于直觉是感性与理性、形象与逻辑以及多种心理活动水乳交融的瞬间爆发,不是通过一步一步形式逻辑推理得来的,因而人们很难说清楚直觉思维是怎样产生的,是怎样进行的,对直觉的内容也很难作出精确的分析,甚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思维形式上的这种模糊性,是与思维的内容紧密相连的。客观上确实有模糊的对象存在。如山水风景中的气韵,人的某种意味深长的表情等,很难用理性的逻辑思维去把握,也难以得到明确的判断。这些就是模糊对象,它在于“亦此亦彼”的两极对立的中间过渡地带。面对这样的对象,为了捕捉、把握它,为了再现和表现出来,不得不动用“意会”、“观照”之类的直觉思维特质的思维形式。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上的模糊性必然反映语言上的模糊性。因此,《诗经》中用赋、比、兴直觉思维方式创作,必然使用大量的模糊语言。
《诗经》语言的模糊性,首先表现在一些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如使用不同的副词来表达时间、范围、状态和程度上具有模糊的特性。如“式微式微”,表示天色昏暗,“日之方中”,表示时间在某一时辰;“西方美人”,“出自北门”,“南山崔崔”,“东门之栗”,表示在一定的方位上存在某人或某物;“愿言思子”、“谓之何哉”、“已焉哉”,表示思念、慨叹、无可奈何的样子;“琐兮尾兮”、“谓山盖卑”“谓天盖高”,表示事物的大小、高矮等等。尤其是《诗经》大量使用了形容词,更增加了模糊色彩。在人的形容上,以“良士蹶蹶”、“赳赳武夫”、“駪駪征夫”、“老天灌灌”、“硕人敖敖”、“温温恭人”形象地描绘了人的性格和举止。在对于思想情感的形容上,不仅以忧心、棘心、劳心、中心、小心、忍心、褊心、肃心等词将心情作了区分,而且将心作了个性的形容:如“中心摇摇”、“悠悠我心”、“刺心夭夭”、“心焉惕惕”、“惴惴小心”、“小心翼翼”、“劳心怛怛、忉忉、博博”、“忧心愈愈、恂恂、惨惨、殷殷、钦钦、烈烈、京京、奕奕、炳炳。”同时使用了人在意会中易于理解的动作和感受,来描写模糊的难以形容的心情,如“中心弓兮”,“中心如醉”、“忧心如薰”、“忧心如惔”、“忧心孔疚”、“祇搅我心”、“乱我心曲”等词。
其次,在客观事物与主观认识的关系上,使用了大量的模糊语言来加以描写。如“肃肃宵征”、“明星煌煌”、“四牡业业”、“檀车彭彭”、“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涕泣如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执辔如组,两骖如舞”等。
此外,《诗经》语言的模糊性还表现在运用了模糊修辞的方式。“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小雅?大东》)这段话的意思是南方箕星闪着光,不能用来簸米糠,北方天上有北斗,也不可能舀酒浆。其中“箕”和“斗”都关顾到两个意思,诗人故意利用语言本身具有的模糊现象进行修辞,使诗文写得灵巧活泼。当然,《诗经》中还有其他种模糊修辞形式。如语义上的虚化、省略、跳跃、闪避等等。
最后,大量运用虚字,也是《诗经》语言模糊性的一个特点。虚字的使用,除了促成音节的铿锵和谐,产生音响的意趣,而且摹拟了客观与主观之间认识关系的模糊性,摹拟了语言和情态的模糊性,加深了语意,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据统计,《诗经》中作为助词、连词、代词、动词的“之”字,就用了1039次,在诗中起到句法作用或修辞作用。语气词“兮”字的使用,是民歌的特点,《国风》中用了258次。这种表现方式及《诗经》中的许多虚字,为我国两千多年的文言文所习用。
总之,直觉思维的模糊性,对《诗经》语言的模糊性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二者是紧密相连的,而《诗经》语言的模糊性,又从一个侧面加深了我国文学创作乃至民族的直觉思维方式。
三、知、情、意——高度统一的直觉境界
直觉是多种心理活动的快速综合、交融,它包括感觉、知觉、表象、联想、情感、意志、体验、判断、理解等多种心理活动,
它是情感与理性、形象与逻辑、情感与意志的相互渗透、参与、融合而成的一种完整的认知形式,是知、情、意的有机结合。在《诗经》的创作中,诗人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在客观的色相、秩序、节奏与和谐之中,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在活泼的心灵飞跃而又凝神寂照的经验中,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因而创造出知、情、意高度统一的直觉境界。
这种境界,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情因景而物态化,景因情而意象化。《卫风?氓》中的第三、四章描写女主人公在万物披绿的春色中,自悔陷入情网的沉迷状态和被遗弃后悲愤的心情。诗中写道:
桑之末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真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正值青春年华的女主人公,充满着对美的直感和对幸福的追求与渴望。她从沃若的桑叶上,想到自己年青貌美、容颜焕发之时;从食桑葚而易醉的斑鸠,想到自己沉醉于爱情之中而不能自拔,从而渲染了如醉如痴的爱情的意境。诗人凭借他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从而发现宇宙间深沉的境地,在对自然景物的感受中,体验人生的美。同样,诗人将自己的情感外射到凋败的桑叶上,借助桑叶这个意象渲染出姿容已减,遭人遗弃的悲苦凄凉的典型氛围,流露出无限的愤懑和哀愁。
《诗经》中意境的创造,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它是选取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生活画面和自然画面,与诗人(或说是诗中的主人公)的真实的思想感情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洋溢着充沛的思想感情,使诗经过“写实”、“传神”而达到“妙悟”的境界。《王风?君子于役》是这样写的: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久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这首诗是写一位山村少妇对久役不归的丈夫的深切怀念。在夕阳西下,薄暮降临的时候,一位少妇孤独地倚门伫望,她看到一群群放牧的牛羊从高地下来,正往村里走,鸡也进了窝,劳作了一天的人们也该回家与家人团聚了,可她远行服役的丈夫却没有归期,此时此景,怎能不触动她对丈夫的思念?怎能不盼望丈夫早日归来?她的盼望是长久的,思念的痛苦也是长久的。在这个情景交融、物我统一的意境中,体现了人类崇高的主题——和平与爱情。这个意境的创造,是作家最深的心灵与自然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它不是一味客观地描绘,而是以自己特殊的直感、妙悟来把握那真理的闪光,直接地启示宇宙内部和谐与节奏,从而创造出一种孤苦无奈的缕缕离愁,在万物都有所归之时,益发增添了诗人心中的寂寞、空虚与失落,乃至离别之苦的惨淡心境。
总之,诗人的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在诗人的突然领悟之中得到妙合,产生知、情、意高度统一的境界。它是直觉的最高结晶。就中国文学艺术与世界文学艺术的关系来说,这种直觉境界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的。因此,《诗经》中的意境的创造,对整个后世文学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