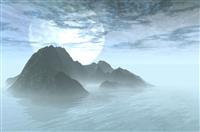关于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游国恩等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早已作过总结,认为白居易诗歌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一、强调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二、强调文学必须植根于现实生活;三、阐述了诗歌的特性及其社会功能;四、强调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因而他的诗论是“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是“先进的诗论”①。这基本成为对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权威性结论。但是,这是以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框架去图解古人的理论,拔高了古人,混淆了古今的理论界限。其结果,理论体系倒是建立了,而对白居易诗论的本质却是曲解了。白居易诗论的确具有严密自足的理论体系,但并非上述《中国文学史》所描述的那样,那是面目全非的另外一种理念框架。对于白居易的诗论及其新乐府诗,在八十年代中期理论界曾展开过颇具规模的讨论,但是多集中于白居易诗论的理论是非,而对其诗论的本来面貌及其完整的体系性却较少涉及。为此,本文试图加以论述,目的是揭示白居易诗论理念框架的内在体系。
一、文学本质
白居易诗论的理论基石是文学本质论,其诗论的理论大厦完全建立在这块基石上。建国以来,不少学者在论述白居易诗论时陷入迷津,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他的文学本质观。
关于文学的本质,白居易在《策林》第六十八中有个通俗而简洁的提法:“皇家之文章”。虽然他提出这个命题时是随意点出:“若然,……则何虑乎皇家之文章,不与三代同风者与?”且又未具体展开论述,但它仍道出了白居易的文学本质观。这里的皇家之文章,似乎是指“皇朝之文章”或“我朝之文章”,但是,联系到他在文章开头有“国家化天下以文明,奖多士以文学”的理论前提及“先王文理化成之教”的理论精髓,而形成的诗论的政治主义学说,这“皇家之文章”应是“皇帝之文章”。文中,白居易还说:“臣谨按:《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记》曰‘文王以文理’,则文之用大矣哉!”在他看来,文章、文学是帝王治理天下的工具,是国家政治的重要手段,因此,自然就得出文章是“皇家之文章”的命题。
这个命题的出现并不奇怪。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国家的一切都为皇家所有。《左传》昭公七年云:“封略之内,何非君士;食土之毛,谁非君臣”。类似的话还可以在《诗经•小雅•北山》中找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见这已成为社会上的普遍共识。土地、人都是皇家的,文明、文化、文学也自然是皇家的。这是白居易“皇家之文章”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
“皇家之文章”的提法有其理论渊源。《礼记•乐记》云:“是故先王之制礼乐,……则王道备矣”,“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在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先秦时代,文学的性质与作用与乐相同,也属于王道政治的工具。此外,葛洪《抱朴子》所谓文学是“大教之本”,王通《中说》认为诗歌要“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以及韩愈、柳宗元等人“文以载道”的理论,都隐含着同样的命题。所以,把文学纳入国家政治轨道,称为“皇家之文章”就并非偶然。但是,在白居易之前,还没有人对文学的政治本质作过如此明白的表述。
“皇家之文章”规定了文学的政治本体论和文学的封建政治特性。照白居易的理解,文学的根本性质在于推动政治活动,在于帝王鸿业和皇家意志,它是帝王治理天下,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这是白居易诗歌理论的基本精神,是他文学创作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文学批评活动的基本理论视角和文学价值尺度。因而他的《新乐府》等讽谕诗是为了皇家而作,是典型的“皇家之文章”。所谓“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②,所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③,就是要让诗歌上达“天听”,受到帝王重视而有效地服务于王道政治。“皇家之文章”把文学规范为封建政治学、封建社会学,它成为白居易诗论的理论内核。
二、文学功能
在文学政治本体论的前提下,白居易论述了文学的功能及其实现文学功能的途径。
既然文学的本质不是主体的精神活动,而是客体的政治行为,那么文学的功能自然离不开政治。对于文学的功能,白居易在《策林》六十八中说:“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贤,以文学取士”。这几句话中,从以文德应天的宇宙天人论讲到文学取士的科举政策,但最重要也最能体现他皇家文学观的是“以文教牧人”,这代表了他的文学功能观。他认为,帝王治理国家,需要运用“文教”这个“牧人”的工具。“以文教牧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重视文学的信息反馈作用,另一方面要重视文学的宣传教育作用。对于第一方面,他在《策林》六十九中以设问的方式云:“圣人之致理(治)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政,顺为教也。”通过诗歌可以了解民风民怨,然后“酌人言,察人情”,也就是他在《策林》六十八中说的诗歌的“稽政”作用。第二方面,帝王利用文学来“立理本,导化源”,实现文学的惩恶劝善功能。因此文学的作用在于“以文教牧人”,在于具体地服务于封建政治教化活动。也只有在实用层面上使文学能够“牧人”,才能真正使文学成为“皇家之文章”。
在如何使文学具体地实现“牧人”的政治功能上,白居易也在方法论层次作了阐述。他认为,帝王“以文教牧人”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立理(治)本”,二是“导化源”。“立理本”使诗直接地为封建政治服务,“导化源”,则是使诗歌为封建伦理教化服务,“当然它最终也服务了封建政治。为政治服务,要求诗歌要“稽政”,通过“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策林》六十八)的途径来“补察时政”;为教化服务,则要求文学要“惩劝善恶”,“泄导人情”。诗歌“稽政”可以使“王道”日臻完备美好,诗歌“惩劝善恶”,可以使“王教”风行、民风淳厚。用白居易的话说:“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④,他对此十分自信。
在“以文教牧人”的封建政治主义文学原则指导下,白居易以高度的封建政治觉悟开始了他《新乐府》等讽谕诗的文学实践。他在《与元九书》中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里的“时”、“事”,都是政治的“时”“事”。他还回忆道:“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泳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⑤。他说得十分明白,他的《新乐府》等诗的文学创作是他以谏官参予朝政活动的一部分,奏疏谏章是他直接呈进给皇上的政治文书,而诗歌则是他间接地传递给皇上的政治诗篇。他还在《寄唐生》中说:“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哭声,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一句话,诗歌也是写给皇家的政治文章,它与谏章一样,意在规劝皇上,为皇帝“牧人”服务,为封建统治服务。
这种“牧人”工具论的文学观,在中唐政治危机深重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对于巩固李唐王朝的政治统治,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它的实质在于用文学为封建政治服务,使文学完全政治化,是很难说得上“先进的”。在唐代文学空前繁荣的情况下,白居易的理论还停留在秦汉时代,要取缔一切非政教的文学,只允许政教文学一花独放,无疑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这种落后性在他的文学政策和文学批评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白居易的诗论之所以被目为“先进的”“现实主义的诗论”,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论者忘记了白居易诗论的封建政治主义的本质,而只看到它所具有的民主因素。这与六十年代的极左文艺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文艺理论前景有关。二是只看到封建政治主义文学积极的一面,而忽略了其消极的一面。白居易在其诗论的指导下,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批判现实意义的讽谕诗,揭露了社会丑恶,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表现了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清醒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社会良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呼声,是能难可贵的。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人们忘记了其诗论的封建政治徽章,也忘记了其诗论的消极面。如果把文学完全政治化,在帝王开明时还能有一些批判性文学,但在高压政治的黑暗时代,充斥朝廷的只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无聊文学。这似乎是人们不愿看到的事实。
三、文学创作方法
为了实践其封建政治主义的文学主张,白居易提出了一整套政治诗歌的文学创作方法,即新乐府的写作程式。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具体地制定了新乐府的创作程式。这主要有:(一)开头方法,要“首句标其目”;(二)结尾方法,要“卒章显其志”;(三)题材要求,要“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四)语言要求,要“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五)体制篇章要求,要“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样,在操作层次对文学提出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系统要求。这些方法,开头与结尾的方法是沿袭汉儒的《诗经》理论,即所谓“《诗三百》之义也。”其他几点,则是白居易的创造。
这是一套规定细致具体的诗歌创作论,按照这个创作模式产生的文学将是怎样公式化、类型化,不在本文论述之列。但这套方法体现出一个基本原则:只重政治内容的传达,因而这套方法又是实践其政治主义文学观的文学保证,表现出白居易诗论从理论到创作的系统性和严密性。
贯串这一套文学创作方法的是一种忽视文学性的美学观。白居易在《策林》六十八中说:“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王者删淫辞,削丽藻”。崇尚质朴无文是实施其政治主义文学观的美学保证。与这相类似的表达还很多,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系于意,不系于文”,又说:“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在《寄唐生》中说:“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等等。一句话,为了“意”而牺牲“文”,为了传达政治内容而贬斥“文”,甚至取消“文”。使文学永远身陷政治实用主义囹圄。若照白居易的理论去做,中国文学实质上被取消了。白居易诗论的理论偏激和狭隘的尾巴在此暴露出来。
四、文学政策
白居易从政治需要的理论视角出发,还提出了他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并制定了相应的文学政策。
“系于意,不系于文”,不仅适用于文学创作领域,也适用于文学批评领域,它代表了白居易的文学价值观。“系于意”是白居易的文学思想标准,“不系于文”是白居易的文学艺术标准。在这两个标准中,由于白居易以否定判断来表述其艺术标准,因此他实际上取消了文学的艺术标准,取消了文学的审美特性,只剩下一个标准——即文学的政治标准,只重视一种价值——即文学的政治教化价值。在白居易的文学价值尺度上,凡是符合他的政治标准的文学便是有价值的,反之便是无价值的。
白居易正式提出“系于意,不系于文”的文学标准是元和四年(公元809),但是这种思想早在元和元年就产生了。元和元年,白居易在《策林》六十八中阐述了他与“系于意,不系于文”相一致的文学政策思想。他说:
臣又闻: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 文也。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 野,采而奖之;碑诛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这里的文学政策正是“系于意,不系于文”思想的政策化、具体化。
在白居易看来,文学的唯一标准是政治标准,文学价值是在于它是否适合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和教化的需要。帝王应以这个标准为价值尺度去衡量文学,并运用行政手段去强行实施文学干预,以贯彻封建主义的文学政策。凡是符合封建政治主义原则的文学,虽质虽野,虽然没有什么艺术性,也要“采而奖之”,以行政措施加以扶植;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文学虽华虽丽,虽具有文学性,也要“禁而绝之”,以行政手段去消灭它。扶植政治教化文学禁止非政教文学,以皇家政权的强硬手段去实施文学干预,
这种文学政策是白居易在为科试而作的政策论文中提出的,当时只是纸上谈兵,并非实行。可以借用杜牧批评白居易的话来形容白居易当时的心境:“吾无位,不得用法治之’⑥,若白居易的文学政策得以实施,唐诗的大劫难便再所难免了。
但是,这种文学价值观和文学政策在白居易的文学批评王国里实施过。在《策林》十年之后,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全面梳理,对代表作家作品进行了文学批评。他认为,自《诗经》而下,文学一代不如一代,中国文学史是一个“诗道崩坏”的历史。屈原,仅仅“得风人之什二三焉”,《诗经》的“六义”原则在屈原的时代已经所剩无几,魏晋六朝文学是一片空白。到唐代,李白虽是“才矣,奇矣,人不逮矣”,“但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甫是白居易最称道的诗人,但千道之中符合白居易文学标准的诗,“也不过三四十首”。在白居易的文学尺度检测之下,千古以来的文学,只剩下《诗经》、梁鸿《五噫》、陈子昂《感遇》二十首,鲍防《感兴》十五首,以及上述差强人意的几位诗人的少得可怜的讽谕诗。包括整个盛唐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基本上被否定了。
这个“诗道崩坏”的中国文学史和几乎荒芜的中国诗坛是白居易封建政治主义文学观的必然结果。它充分表现了白居易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和理论旨趣,凸现出白居易政治文学理论的实质,也暴露出白居易诗论的理论偏颇程度和落后本色。即使那些极力推崇白居易诗论的人,在他的文学政策论和文学批评论面前都吱声不得。
五、余论
由上可知,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由文学的本质论、诗歌的功能论、诗歌创作论以及文学政策论、文学批评论几个方面的内容组成,这些理论既有哲学美学层面的文学本质论、美论,也有文艺学层面的创作方法论,也有政治学层面的工具论、政策论等,它们构成了一个结构严密、功能齐备的理念构架。
不少学者研究白居易诗论仅以他的《与元九书》为批评文本,是不够全面的。白居易的诗论主要体现在他的《策林》六十八、六十九,《新东府序》、《与六九书》等文中。《策林》写作最早,是他为应制举而撰写的政治策论,因而《策林》六十八、六十九充满了政治色彩,而这种政治本位的理论视角和理论特征成为他以后诗论的理论基础。《新乐府序》是他身为谏官时的政治谏章式的文学的序言,意在为他的政治性文学作理论阐释。《与元九书》是他被贬出京后所作,他的思想仍浸润在政治文学的热情中。由此可见,白居易诗论的现实出发点在政治,理论落脚点也在政治。白居易为了政治而利用诗歌,为了诗歌政治化而谈论文学,政治是白居易诗论的唯一价值取向,因此白居易诗论是以封建政治主义为核心的政治学、社会学诗论。它的理论覆盖面和理论适用度都只限于封建政治主义文学——“皇家之文章,它对于例如白居易的感伤诗,闲适诗那样的非政治主义的文学,对于例如现当代诗歌这样的非封建的文学都是不适用的。这便是白居易诗论遭到今人诟病的原因。
白居易诗论的主要内容大都有明显的理论渊源。他关于文学本质,文学功能的理论来自儒家诗教学说,而其主要部分的“六义”、“风雅比兴”、“稽政”、“惩劝美刺”都来自汉儒的《诗经》学说。他的文学政策论来自《礼记•王制》的“四杀”和例如李谔那样的儒家复古派的学说。从中国文学思想史的角度说,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并没有比前代提出多少新的理论内容。但是,白居易也有他的贡献:第一,他以文学本质论的角度,提出“皇家之文章”的命题,更鲜明地突出了封建道统文学的政治本质;第二,他在新乐府的创作方法上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内容,在文学创作的操作层面对儒家诗教理论有所补充和发展;第三,他把儒家诗教建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以系统的整体功能对儒家诗教原则作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可以说,在白居易之前,没有人将儒家诗教理论作过如此系统的阐述,在白居易之后,也没有人象白居易这样不遗余力地张扬儒家诗教,白居易在儒家诗教史上是一位殿军式的人物。所以唐人张为在《诗人主客观图》中把白居易奉为“广大教化主”,使他成为唐代儒家诗教的教主,居于该教五个层次的塔尖上。
对白居易诗论的理论是非和得失进行全面的历史评说,还得再进行深入研究。
收稿日期:1994-03-09
注释:
①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二、第119-121页。
②白居易《读张藉古乐府》。
③白居易《寄唐生》。
④白居易《策林》六十九。
⑤白居易《与元九书》。
⑥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