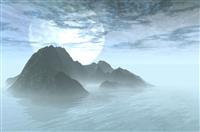
由唐宋迄于明清,杜诗的价值愈见重视,杜甫的声誉日趋卓著,最终确立了“诗圣”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
与此同时,一种对杜甫认识理解的人为纯净化也随之而生,并甚为突出。论及杜甫思想,往往扣住“奉儒守官”的传统,极力宣扬其“每饭不忘君”,而对于儒学之外的其他成分,与圣哲不尽合谐的声音一概视而不见,或曲为附会,以为此类皆为异端,恐污诗圣皎洁。似乎杜甫的思想自始至终单纯一致,别无他念,亦无变化。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世人对诗圣形象的图解:神情庄重,面容枯槁,举止循规蹈矩,终日忧心忡忡。拈须苦吟之状令人敬而畏之,难以攀近。这也直接妨碍着新的时代环境下对杜甫精神的学习借鉴、弘扬光大。因此,全面深入理解杜甫思想是杜甫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探讨杜甫与道家道教之关系,旨在从一个侧面说明杜甫思想的丰富性。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诗人之一,杜甫精神与诗歌成就都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其诗艺“宪章汉魏、而取材六朝、至其自得其妙”,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其感情深沉而多彩,执着又率真,喜笑由衷,痛饮狂歌;其思想博大精深,本于儒家仁义,而兼取释老精魄,大凡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理想道德因素,在大唐帝国由盛到衰特定历史转折条件下凝聚成独具个性的杜甫精神与人格。
关于杜甫与道家教之关系,学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种是传统的观点,影响甚大,有代表性者如萧涤非先生《杜甫研究》所指出,“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在杜甫思想领域中并不占什么地位,……在他的头脑中,佛道思想只如‘昙花一现’似的瞬息即逝。”冯至先生《杜甫传》亦称“(杜甫)王屋山、东蒙山的求仙访道是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
另一种观点则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其著《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宗教信仰》中专门反驳萧、冯之说,认为“杜甫对于道教有很深厚的因缘,他虽然不曾象李白那样,领受《道箓》成为真正的道士,但他信仰的虔诚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求仙访道的志愿,对于丹砂和灵芝的迷信,由壮而老,与年俱进,至死不衰。无论怎么说,万万不能认为‘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有如‘昙花一现’的。”
对比两派说法,分歧焦点不在于杜甫头脑中是否存在过某些道德观念意识,而在于这种意识的深厚持续程度。即到底是暂时受李白影响,“一时的热情冲动”(陈贻?{《杜甫评传》),还是持续终生,甚至超过李白笃信不悟。
由于《李白与杜甫》产生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立论多有偏颇,故而颇遭非议,有关杜甫与道教关系的意见也较少为人认同。但平心而论,剔除郭氏书中明显带有时代与个人色彩的偏激之词,其意见亦并非毫无可取之处。郭老认为杜甫信道至死不衰、超过身为道士的李白这一说法固然还可商榷,但由此所表现出的不拘于表面形式而着眼于内在实质的独特视角却是值得肯定的。在李杜研究方面多有这类今人费解而又习以为常的现象,比如二人同样酷嗜美酒,然而后世往往津津乐道于“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名句)以诗仙为酒仙,而诗圣则很难进入著名酒徒之列。而在对道教关系上也同样如此。人们从不怀疑李白头脑中的道教信仰,也很少注意他最后是否清醒,这大概是因其领受道箓,成了“名符其实”的道士吧!基于这一思维定式,杜甫只是短暂地求仙访道,在行动上没有李白那样激烈狂热,因“苦乏大药资”也并无真正的炼丹实践。尤其是没有受箓之举,故而其思想深处道家成分如何也就被忽略不计或完全否认了。
正由于此,我们认为郭沫若的基本观点即认为杜甫对于道教有很深厚的因缘,不是暂时受李白影响,有如昙花一现,而是由壮到老、与年俱进、至死不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它有着相当的事实依据,不能简单否定。郭老当年为了证明其说,列举了大量证据,说明杜甫在早年与李白相识之前即已有仙道之志,离开李白之后,某些仙道之念仍不时萦系于心,直至临终。
如果说尚有可议者,郭老未及将道教成分作具体分析,笼统地视作迷信,也未将其与老庄道家思想作区别,并指出其在杜甫不同生活阶段的消长,以及对丰富杜甫思想的积极影响。可以说是时代的局限。其后曹慕樊先生对此有所补正,指出“道家应分别先秦道家和汉以后道家,杜甫的道家思想中两种因素都有,汉以后道家有许多派别,比如玄言、服食、外丹、内丹、神仙等派,杜甫是相信服食的。所以常提葛洪、嵇康、对神仙派他不大信。”(《杜诗杂说》)曹先生同时还肯定了老庄思想对于杜甫性格“真”与“放”的良好影响,更趋具体客观。
但是,学术界对郭沫若的观点大多持否定态度。在这类文章中,近年钟来茵先生新撰《再论杜甫与道教》(《首都师大学报》1995.3)一文,自称“就郭先生全部论据作驳论”,阐述己见,在否定性意见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钟先生将郭沫若提出的全部论据归纳为五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反驳。一、杜甫求仙访道,是否受李白影响;二、关于《三大礼赋》;三、关于《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四、关于《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乙天尊图文》;五、关于丹砂、葛洪、蓬莱及其他。条分缕析,不乏创见。倘能破之有据,则无异釜底抽薪,郭说自然难立。但细读之后,却感时有牵强,未能信服。故亦特就所列五题略申管见。就教于钟先生等方家。其中第一问题为杜李相识前之论据,二至五则为杜与李别后之论据。下面试分别论之。
一、与李白相识之前杜甫是否已有仙道之愿?
郭沫若认为杜甫思想中道教因缘很深;早在与李白相遇之前即已有求仙访道的意愿,并非“暂时”受李白影响。这个论述十分明确,强调相遇之前即已存在,并未涉及李白影响问题,二者之间也就并无矛盾。李杜相识可以使已有的仙道之愿更为强烈,尤如催化剂作用,促其化为行动。因此应该说受李白影响是杜甫求仙访道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和唯一原因。更不是暂时的影响。所以郭老又指出:“如果一定要说受了影响,那倒可以更正确地说:李白和杜甫的求仙访道,都是受了时代的影响。”在朝廷高度重道的情况下,整个士大夫阶层都不能不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即使不是出于信仰的虔诚,你也非歌颂道教不可。”应是较合实际的。
钟先生的文章首先列出第一个论题是“杜甫求仙访道是否受李白影响”,具体反驳的却是郭沫若认为杜甫早已有仙道志愿的观点和论据。指出:“传统意见认为:杜甫的求仙访道是受李白的影响,完全是事实,郭沫若所举的相反的例证是无法成立的。”从而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但文中同时也指出,早年以奉儒守官为主导思想的杜甫“受时代的影响,杜甫也有求仙访道的雄心,具体来讲,杜甫的求仙访道,受李白的影响更大。”这其实与郭说无大差异,因而其反驳郭沫若有关杜甫与李白相识之前有仙道志愿的根据也就难以自圆。
让我们还是具体来看看这类论据吧:
其一:杜甫《壮游》诗云:“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
郭沫若解为杜甫20岁时“南游吴越,已准备浮海,去寻海上仙山——扶桑三岛。这愿望没有具体实现,直到晚年还视为‘遗恨’。”钟先生则称“这里杜甫只是以‘扶桑’作文学典故用,表明自己的壮游之雄心,并无半点道教迷信成分。”
细研二说,感觉皆不尽如人意,前说过于拘泥,未免太实,后说完全抹去道教色彩,又显得虚泛。“扶桑”自然是文学典故,但杜甫用之真的就毫无仙境之意么?我们不妨采用以杜解杜之法,另求参证。杜甫晚年在潭州曾作《幽人》诗,其中有句云:
“往与惠询辈,中年沧州期,天高无消息,弃我忽若遗。……洪涛隐笑语、鼓枻蓬莱池。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风帆倚翠盖,暮把东皇衣。
钟惺评此诗为“绝妙游仙诗”。其与《壮游》中数句怅恨之意相近,并在慨叹之余更掺入海上仙境美妙遐想。稍加比较即可看出两处诗中“扶桑”并非毫无关连。
杜甫又有《卜居》诗云:“归羡辽东鹤,吟同楚执珪。未成游碧海,著处觅丹梯。”以“碧海”与“丹梯”相对。仇注引《十洲记》:“扶桑之东有碧海。”诗意似亦与“不得穷扶桑”相关,均见其早年游仙之意。
再通览《壮游》诗中所叙早年行程:“渡浙想秦皇”、“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指天姥”诸境,让人极易联想到孟浩然、李白、孔巢父及“竹溪六逸”等人之游踪。谁又能肯定杜甫此行只是单纯的漫游呢?陈贻?{先生曾指出:“他(杜甫)的学道和漫游是出了名的了”。正由于此,多年不见的友人韦济特意向人打听杜甫近况,开口即问:“青囊仍隐逸、章甫尚西东?”(《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关心他是仍在隐逸学道,还是在到处漫游。而杜甫的回答则是?“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术空。谬惭知蓟子,真怯笑扬雄。”可见杜甫早年的生活中,隐逸、炼丹、学仙与漫游、干谒等本自时相纠合,难以全然区分,又都一事无成。既如此,又怎能断然判定杜甫壮游途中,登姑苏台而望海兴叹,不会生发寻仙扶桑之念呢?
其二,郭沫若还从杜甫早年有限诗作中拈出《题张氏隐居二首》之一、《巳上人茅斋》、《临邑苦雨、黄河泛滥》等三首诗,认为其中都含孕着道家的气息。钟文对此一一提出相反意见。我们不妨再略作辩析。
关于《巳上人茅斋》诗,钟先生认为“只与佛家有关”,因“杜甫笔下的‘巳公’是佛教而非道士”。其说有一定道理,但似乎只限对题目的理解。细揣末联云:“空忝许询辈,难酬支遁词,”不难感受到同时存在的另一种气息。仇注曰:“末以许询自此,以支遁比巳公。”许询为东晋著名玄言诗人,曾为道士,隐居永兴,遍游名山,采药服食。又精于名理、善论难,与支遁辩论,轰动一时。此处用以自比,可见当与僧道皆有关系。
钟先生又称《临邑苦雨,黄河泛滥》末尾用《列子》“钓巨鳌”之典只是“文学上的夸张”;《题张氏隐居》“只是一般的歌颂隐士。”诗末“乘兴杳然迷出处,对君疑是泛虚舟”,适用《庄子》之典来表达对隐居深山的向往。其实这类意见与郭说并无本质差异。根据文学创作之规律,作品主题多有复杂性、不确认性以及语辞兼有多义等性质,理解小有差异实属自然,从对隐居生活的颂扬中看到道家气息也无大错了。
其实,杜甫在认识李白之前有无仙道之想,在其最早一首《赠李白》诗中已说得明白不过。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
野人对腥羶,蔬食常不饱。
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
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
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
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全诗十二句,分上下两章,前八句自叙,后四句赠李,层次分明,逻辑严密。遇李白之前,久客东都,深感世风机巧,格格不入,避世访道之念油然而生。既思“青精饭”(钟文亦称之为“道士专利品”),又欲求大药,苦于资金匮乏,彷徨无奈。故仇注云:“叹避世引年之无术也。”此时的志愿与苦闷皆与李白无关,而正在无计可施之时,恰与“脱身事幽讨”的李白相遇。相见恨晚,一拍即合,遂促成其事。一个“亦”字,并非杜甫单方面亦步亦趋,而是双方不谋而合,相傍成行。叙述如此清晰,可见这种求仙访道之志早已蕴藏于心,怎能将其仅仅归结于与李白相识后受其影响,而且还只是“暂时”呢?
二、杜甫离别李白后是否再无仙道之想?
郭沫若列举了大量的论据来说明杜甫与李白分别之后,仙道之念时有显现,直至临终。钟先生对此另作解释,得出相反之论,称这类作品中不仅没有道教意识,而且表现了对道教的“讥讽意思”。“反对道教的字句,证明了杜甫坚定的儒家思想。”甚至剥开其道家语的外衣,“其忧国忧民之伟大情怀至今读了还感人呢。
”
在此,有必要再作具体剖析。
1.关于《三大礼赋》
要确切把握《三大礼赋》之内涵及性质,不能不对其写作缘由与背景先有所了解。《通鉴》记玄宗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合祭天地于南郊三大礼在天宝十载春。直接起因是天宝九载冬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谓“见玄元皇帝(老子)言宝仙洞有妙宝真符”。玄宗派刑部尚书张均等往求而得之。更深缘由则是皇帝自身好道。如《通鉴》所载。“时上崇道教,故所在争言符端,群臣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上悦。”
由此可见,所谓三大礼本身就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崇道仪式。而杜甫加入这朝贺之列更有其特殊的原因。正值四处干谒无果,走投无路之际,唯有投匦献赋、企求圣恩一法。投献时机亦精心选择,或许还曾请老熟人张垍兄弟幕后出谋划策(
参陈贻?{《 杜甫评传》174页)。其目的十分明确,孤注一掷,打动人主、博取青睐,
求得功名。这一切都为赋作内容定下基调,只能是顺其所愿,投其所好。不可能大唱反调。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朝献太清宫赋》一开始便称:“冬十有一月,天子即纳处?士之议……”通篇顺迎圣意。所以朱东润先生论及该赋成功的原因时指出:“主要还是由于他的尽力歌颂,不表示丝毫的愤懑。”(《杜甫叙论》23页)正由于此,郭沫若先生直言杜甫“作赋的灵感是从骗子道士太白山人王玄翼那里得来的。”可谓一语中的,抓住了理解其意的关键。
遗憾的是,同其他不少的“杜甫研究家似乎把这事完全丢在脑后”一样,钟文也完全回避了杜甫献赋的直接缘由,进而否认其中有颂扬道教的成分,称其主旨是“以坚定的儒家思想反对唐玄宗崇道迷信。”实在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写作目的虽不能完全决定内容,但很难想象此时正“诚惶诚恐”的杜甫,既为生计而献赋,不去顺其所好,反而迕逆圣意,讥讽圣道,自找祸端,而笃信道教、兴致正高的唐玄宗读之还会龙颜大悦,废食相召,“命宰相试文章”。
作为献给皇帝之文,自然要颂扬皇朝勋业,故《朝献太清宫赋》中间有两段代皇帝立言、简括魏晋至唐由纷争而统一的历史,“兹火土之相生,非符箓之备及”,谓唐以土德继火,相生而致太平。此处既沿袭阴阳五行之说,又有否定符谶之意。这与崇奉道教并不矛盾,宗教本身也是要为政治服务的。而且杜甫亦偏于先秦老庄及丹砂服食派,不太信符箓。文中随后极力渲染老君下临盛状,洞宫俨然,祥云下垂,虹霓环绕,凤凰威迟,鲸鱼屈矫,天子恭迎。可谓集圣德与仙道于一体。如仇注所评:“此言唐兴致治,毕集祯符,见神灵之宜降。”切合唐玄宗顶礼膜拜玄元圣祖、祈求长生、永享鸿祚之心态,也正为“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的艺术写照,再加文采灿然,打动人主也就不足为怪。
《朝献太清宫赋》还写“天师张道陵等”率道士代为答辞,钟文认为郭沫若在此又搞错了,将法官道士误作汉代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实际上郭著中只是引用这几个字眼而已,特意加的引号可以说明,并无张冠李戴之意。杜甫以道士张道陵作为道教徒代表。赋中“列圣有差,夫子闻斯于老氏”,既是前代文献记载之转述,也是唐代统治者心目中“玄元皇帝”与“文宣王”不同等级的实录。无论杜甫心中真正作何评价,孔圣之徒在此确已自降一等。不能排除谄媚之嫌。
类似于此极力颂扬玄元圣祖之辞,在“三大礼赋”中随处可见,如《有事于南郊赋》中铺写唐朝正统时追本溯源:“伏惟道祖……协夫贻孙以降,使之造命更挈,累圣昭洗……”仇注曰:“此追原圣祖为发祥之本。”可见其迎合帝意,说明唐之国祚乃圣祖所赐。
当然,《三大礼赋》本身又是矛盾的统一体,也并非如郭沫若先生所说的单纯崇道,而是杂糅儒道之念。其中不乏维护皇权正统,继承先祖遗业、宣扬孝道,以及讥讽符谶,方士淫祀等内容,但综观三赋,投合时风与皇帝所好,崇奉道教之倾向是显而易见,勿须讳言的。
2.《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
此诗作于天宝八载冬,早于《三大礼赋》,关于其主旨的争论早在明清时即已展开。传统的观点以钱谦益为代表,认为唐玄宗崇道过分,故“老杜作此诗以为讽谏,讥老子庙悖礼逾制也”。而毛先舒则加以反驳道:
“此篇钱氏以为皆属讽刺,不知诗人忠厚为心,况于子美耶。即如明皇失德致乱,子美于《洞房》、《夙昔》诸作,及《千秋节有感》二首,何等含蓄温和。况玄元致祭立庙,起于唐高祖,历世沿祀,不始明皇。在洛城庙中,又五圣并列,臣子入谒,宜何如肃将者。且子美后来献《三大礼赋》,其朝献太清宫,即老子庙也,赋中竭力铺张,若先刺后颂,则自相矛盾亦甚矣,子美必不出此也。”(《杜诗详注》引)
其意十分明显,谓此篇与《朝献太清宫赋》皆为正面颂扬,并无讥讽之意,那些持讽谏说者,本意回护诗圣,谓其儒家思想坚定纯粹,不意反使其陷于有失忠厚。当然毛说也仍有迂执之处,但确属独具只眼,故杨伦对之大加赞许:“此论可一空前说。”而郭著其实不外是其延续和补充。
钟文反驳郭论,依然持讽谏说,谓杜甫“无论如何也忍不住要冷嘲热讽,于是在诗的结尾和盘托出,并无半点隐瞒。”
两说主要分歧在于三处不同的理解。
一是诗之第二段有“仙李蟠根大,猗兰奕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意为当年老子未被采入《史记》世家,而今其学得以弘扬,天子亲自注《道德经》。郭老认为这里谴责了司马迁,固然话说过了头,但反过来也看不出诗中对唐玄宗作注有何讥讽之意,看不出玄元皇帝庙的来源滑稽可笑。联系上下文意,杜甫对老子及玄宗都是必恭必敬的,这几句实际上只是推言庙祀由来和老子之道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记录,并无别的言外之意。该诗末二句云“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杜臆》解道:“老子见周衰而远去,文帝传河上丈人经,崇之以治天下,盖申赞老子之道,晦于当时而显于后世。”从时代的变化解释了老子的前后际遇,正可与此互证。
第二是关于庙中吴道子所绘壁画,郭沫若认为杜甫大力赞扬,写其气象森罗,笔意超妙,这实际上兼含画中内容、吴道子绝妙笔法及艺术效果。而钟先生却从后半“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四句中看出讥讽之意,并引钱谦益、金圣叹之说证明这是写其荒唐无稽。
考此句原注曰:“庙有吴道子画《五圣图》”。另康骈《剧谈录》载:“玄元观壁上有吴道子画五圣真容及老子化胡经事,丹青绝妙,古今无比。”均见此画甚得称道。既名为《五圣图》,唐高祖、太宗等崇道著称的五圣当然要占据画面主要位置,杜甫在总览之后,再拈出五圣真容略作描述也很自然,所以此数句不过是画面内容的概叙罢了。金圣叹指责画作“联衮”,则与千官成雁行,君臣无分,又认为五圣应作坐像,“冕旒”本当穆穆皇皇,深坐九重之上,“旌旆”则不免行色匆匆,因而相互矛盾,“一片无理”,“直欲笑杀人”(《杜诗解》)钱谦益亦认为此二句“近于儿戏”,似乎言之凿凿,研读仔细。却毫未顾藉壁画艺术创作之背景条件、特点与客观规律,倘拘于常理,谓“冕旒”、“旌旆”不当同时出现,则相距百年的“五圣”又何尝“联衮”而行?但事实上,这类“矛盾”之作在历代画中又是屡见不鲜。且为吴道子此壁画中物,杜诗不过拈其大概写实罢了。若谓果有讽意,也当是以画宗教人物擅场的吴道子所为,而吴氏画中类似之作不少,何以未见谈及暗含讥讽,而单单从杜诗数语概叙中发见讽意呢?
还是陈贻?{先生说得好:“杜甫早年在江宁见到瓦棺寺顾恺之维摩诘变相到老印象犹新,这次他看了当代艺术大师吴道子的五圣图和老子化胡变相,备加赞赏,又特意加注点明,可见他对壁画艺术的爱好。”(《杜甫评传》)实是不带偏见之论。
第三处歧解在诗末数句,所解更是大相径庭。“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关键是对这个“如”字作何理解,依钟说:“杜甫用了个假设的问句:“如果老子不死,他将在何处隐居呢?他会高兴地来到玄元皇帝庙吗?说过‘功成身退、天之道也’的老子,见到唐玄宗如此胡闹,是会反感之极的。”
我倒以为郭说讲作“俨如”之如似更符原意,引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谓这里加一“如”字,即《论语》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之意。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补证。一是因为“谷神”本为养护五脏内元神之意,汉河上公注曰:“谷,养也,人能养神则不死也。”仇注谓老子人往而道存,神藏而迹隐,即使人未露面无形无影,其元神俨然若存也无处不在也。此处“何乡”亦不是“何处”,而是《庄子·逍遥游》“无何有之乡”的简称,即什么都没有的空虚之境。这正是“谷”的本义。也符合老子“虚怀深藏若谷”之思想。第二,在历代道教典籍和唐人心目中,老子本来就是不死的,故而生于殷时,为周柱下史,积八百年,周德衰而乘牛车入大秦,以后于治世屡屡显灵,唐玄宗时亦显圣不断。以之映证其天下太平。此尚可以杜证杜,在稍后所作《朝献太清宫赋》中,有十分逼真的描绘:“烁圣祖之储祉,敬云孙而及此。诏轩辕使合符,敕王乔以视履。”仇注:“此乃顒望神灵,有洋洋如在之意,合符视履,盼其至也。”这是多么的煞有其事。再写神灵降灵:
“则有虹蜺为钩带者,入自于东,揭莽苍,履崆峒,素发漠漠,至精浓浓,……裂手中之黑簿,睨堂下之金钟,……”
这又是多么的活灵活现,不正是谷神“俨如”的最好注脚么?
4.关于丹砂、葛洪等例证
郭著曾按年代排列杜诗有关炼丹、服食、葛洪等仙道例证15个,说明杜甫一生到老都在追求,“都在憧憬葛洪、王乔,讨寻丹砂、灵芝。想骑仙鹤、跨鲸鳌、访勾漏,游仙岛。他是非常虔诚的,甚至于想成为彻底的禁欲主义者。”
这个结论是否过于绝对化,可以另作讨论,但这些例证却实实在在是杜甫某些时期仙道之念的反映和记录,说明道家意识在其脑海时常闪现是无疑的。此外类似之例尚多,无须再举。
钟文对此依然提出异议,逐一否定其仙道观念。郭所谓“禁欲主义”说的依据乃是杜甫《寄刘峡州伯华使君》中“养生终自惜,伐叛必全惩”,钟文首先反驳此论。认为“刘伯华热衷于长生,荒废了政务,所以杜甫劝他‘养生终自惜,伐叛必全惩’。意思是:养生延年,主要靠自己珍惜身体,但不能因此而放松政务。讨伐安史叛军之类,必需全力以赴,这与‘禁欲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那么,我们也不妨稍作解析。
其实:“伐叛必全惩”一句,前人早已有两解,一指平伐叛乱,一喻伐生伐性。郭氏“禁欲”之说即依后说,并非自创误解。是否正确,须联系全篇上下文意。《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是杜甫大历二年作于夔州瀼西,据仇注对其层次的划分,依次叙夔峡两地相去之近、思念刘君、先世渊源、刘君诗才、不同遭遇等,多为宾主并叙。自“乳瀼号攀石,饥鼯诉落藤,药囊亲道士,灰劫问胡僧”一段以下为序客夔近况。诗人又写道:
“姹女萦新裹,丹砂冷旧秤。但求椿寿永,莫虑杞天崩。炼骨调情性,张兵挠棘矜。养生终自惜,伐叛必全惩。政术甘疏诞,词场愧服膺。展怀诗诵鲁,割爱酒如渑。”
这一段十二句意思连贯而下,不难明白,自叙其夔州生理,炼丹养生,疏于时事。其中“张兵伐叛”,正如王嗣奭《杜臆》所释:
“‘姹女’以下,俱言服食以求长生之事。‘张兵挠棘矜’,乃卫生之喻,谓伤生之物,比于剑戟,而张兵以拒之也。‘伐数’(草堂本作伐数)句正顶说,谓凡有伐我寿数者,必全惩之也。又言‘政术甘疏诞’,已无意于仕矣。词场则愧于服膺,犹窃有志焉。故所自展怀者,诗唯诵鲁,……而割爱于酒如渑,公时以病戒酒。”
释意明白,可见正为杜甫当时生活情景之自述也。
有人谓“张兵”、“伐叛”二语是因当时“蜀寇未靖”,故而以之为刘使君职责所在。过于拘泥,反倒穿凿。王嗣奭解作借喻之法,已甚精确。朱注亦谓“多欲戕生,犹将兵伐性”,同于王说。典出《吕氏春秋·本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枚乘《七发》亦曰:“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指本为美好之物,贪多反倒危害身心。故曰“伐性斧”,“伐叛”“伐数”皆为近义。杜甫此处正用其义,谓炼骨养情性,须抵御棘矜般伤生之物,养生延年终靠善自珍惜,对伐性之物更应全力警诫防范。由此可见郭沫若“禁欲”之说并非风马牛不相及。杜甫每称“妻子亦何人?丹砂负前诺”。“笑为妻子累”。亦非泛言。陆游有句曰:“倩盼作妖狐未惨,肥甘藏毒鸩犹轻”,“养生孰为本?元气不可亏。”亦可为旁证。
该诗末云:“咄咄宁书字,冥冥欲避矰”。施鸿保评:“是言将避人遁世。”(《读杜诗说》卷十九)似亦可证该诗题旨,与讨伐安史叛兵无涉也。
最后再说有关丹砂、葛洪以及蓬莱等事物。钟先生将其割裂成三种类型,分而论之,实则三者本自关连,“丹砂访葛洪”、“服食寄冥搜”,炼丹祈长生,慕道欲轻举,蓬莱问仙药,关系密切而各有侧重罢了。故此简论之。
钟文称:“唐人诗中涉及丹砂,灵芝一类仙药,实在多不胜数,这些决不是道士的专利品,普通人都喜爱,其功能相当于现在人参、珍珠粉之类,是一种滋补药。”“满朝文武都服长生药,他们都不是道士”。文中又特举颜真卿服方药得长生之例,谓杜甫除丹砂外,还采种各种传统中药,“这些理智的活动,与道教迷信根本是两码事。”
确实如此,服食丹砂灵芝者并不全为道士,但果真与道教信仰无关吗?丹砂真的只是一种滋补药吗?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丹砂本名原硃砂,是一种矿物,本为炼汞的主要材料。道教徒以为可以炼化为黄金,又可炼为金丹,服之不老,长生成仙。如葛洪《抱朴子》所言:“金丹烧之愈久,变化愈妙,令人不死不老。”杜甫广德年间返草堂时自言“生理欲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正是指此。道教养生方法本来就是科学与迷信共存,葛洪为首的金砂派中有许多著名医家,因而有其合理之处,原始的炼丹术也正是近代化学的先驱,因而不乏服丹适当而治病强身的。但就总体而言,其敝大于利,历代中毒暴亡者不胜枚举,唐代有识之士亦多有揭露。可见其功能与当代人参珍珠粉之类大相径庭,不能以一般滋补药等闲视之。所以杜甫所写的丹砂、姹女(汞)以及灵芝、获苓等是否全为纯医药的理智活动,多次写及葛洪是否只是与避乱有关,也就都不难回答了。
三、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杜甫的思想并不只是单纯的儒家正统观念,同时还受到包括释、道在内的各种思想的深刻影响,其中道教及道家的一些观念意识在其思想深处长期存在。在与李白相识之前,既已有之,与李白分别之后直至终生亦并未完全消除,只不过因不同历史阶段和环境而有隐显之别罢了。因此,不能说道家观念在杜甫思想中不占什么地位,更不能说只是“昙花一现”,“暂时”受李白影响。
2.本文探讨杜甫与道家之关系,揭示其道家思想成分,旨在以此撕下人们长期以来贴得太多的“每饭不忘君”的纯儒标笺,从一个方面说明其思想性格的丰富多样性,但并不就此以杜甫为“道家面貌”,亦不否认“致君尧舜”的儒家理想在其整个思想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3.杜甫思想中的道家成分可谓糟粕与精华共存,其影响亦是消极与积极兼备,但更多地偏于积极良好方面,这其中如性情的真率、狂放、崇尚自然,以及诗歌艺术风格的斑斓多彩,都吸取了道家的丰富营养。因为博大精深的杜甫人格精神本身就是兼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想道德凝聚而成。“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这正是诗人心中充满“出世”与“入世”矛盾,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真实自诉,也是其与常人情感相通、共鸣可亲之处。而经过痛苦的抉择,诗人汲道家之营养,却未遁隐入道,所选取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关注民生疮痍的心路历程也才更弥足珍贵,饱经忧患的“笔底波澜”方更真切地传达出时代的脉博与世间的欣乐悲愁。比起所谓自始至终笃于人伦的愁苦呆板面孔来,其突出的诗史价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不知要高出几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