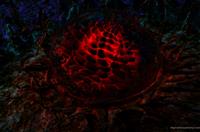
文章原载于《人间几回伤往事:黄朴民解读历史文化》
这里所说的历史“冷”“热”,指的是历史学这门学科、这门知识在现实生活中既受冷落,又被热捧的巨大矛盾现象,巨大地位落差。
要解释这种现象,恐怕还得从“历史”的本质属性入手。
古希腊杰出哲学家、爱非斯学派创始人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叫做“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这意思是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历史是无法重复的。这当然很对。可我们还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似乎也出自某位名人之口):“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很显然,它所蕴含的深义是,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又呈示出不断重复的特征,就像《孙子兵法》上讲的:“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孙子兵法•势篇》)
由于历史无法真正重复,那么它只能是凭吊的对象,只能是往昔的记忆,它离现实生活很远,距资源转换更遥,谈不上“活学活用”,更遑论“立竿见影”,而人们是现实的,社会是功利的,当学历史完全不像学经济、学法律那样,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无法实现以知识换取眼前财富的抱负,无法实现以金钱、地位为衡量标志的成功理想,使“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古人同样讲究实际)的梦变得遥不可及的时候,那么,历史作为一门学问,自然就不能不被忽略,被彻底的边缘化。这一点,从每年的高考招生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各大网站调查专业人气指数,忝居末座的总是历史学,似乎从来不曾花落他家。对广大考生及其家长来讲,“历史”犹如瘟疫,惟恐避之不及(当然我们也不否定有个别例外),谁要是“荣幸”地被历史专业所录取(即便是那些以“一流”自居的名牌大学的历史专业),那么他(她)和他们的家长之心情,恐怕很有可能是忧大于喜,哭多于笑,用秦观的词来讲,便是“春去也,飞红万点愁似海!”(《千秋岁•水边沙外》)而其周遭的亲朋好友此时此刻也往往是“唯见江心秋月白”“此时无声胜有声”(白居易《琵琶行》),投去的目光中除去艳羡,也参杂了一半的同情和怜悯。
历史的“冷”固然是事实,可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历史有“热”的一面。这种“热”并不肇始于今日,至少在唐宋的瓦舍勾栏里,历史的通俗化与大众化就全面上路了,“或笑张飞胡,或谑邓艾吃”(李商隐《骄儿诗》,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同样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诠释。恐怕专业正统的历史学家都会把这种历史传播方式视为歪门邪道,不值一哂。但是,它毕竟是历史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比之所谓的“正史”的影响要大得多,范围要宽得多,群众基础也要广泛得多。
这种以民间为基本对象的历史大众通俗化传播方式,在今天依然是十分时兴的,根本不存在任何“画眉深浅入时无”的问题。只要看看电视荧屏上的“汉武大帝”、“洪武皇帝”、“贞观君臣”的火爆出镜,再有空听听易中天教授讲三国的图书版税挣了X百万之类的消息。你就不能不承认,历史也有“热”的一面,尽管这种“热”并非历史学家心目中的“热”,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鲁迅《自嘲》),钻牛角尖折腾出来的“学术精品”,那些孤芳自赏的学术专著,不论是过去,或是现在,还是将来,大概都不太可能会走“热”,更不必说会“大热”。于是乎,连文学家也跑到“历史”圈子里(这里我所说的是大历史圈的范畴,圈中人不光是那些历史专业工作者)来助兴凑趣,如著名作家刘心武的“红楼”揭秘系列就平添了不少历史的佐料,变得十分有趣、好看(当然,这也惹怒了众多“红楼”权威,对刘氏口诛笔伐,齐声呵斥,但是刘氏之书依旧热销,“权威”们的煌煌巨著依旧“养在深闺人未识”,鲜有人问津,这也是事实。)
历史之所以“热”,原因同样有很多,譬如说,人们有强烈的“寻根”意识,渴望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的答案;又譬如说,人们有深层的“消遣”心理,希望通过历史了解知识,增添谈资,打发时间。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说法自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觉得,更主要或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把过往的既定史实与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从而激发了人们走近历史、认识历史、进而开发历史的心理期待与生命追求。
正因为历史有相似之处,人们才会在历史中看到现实的影子,从现实中嗅出历史的气味;正因为历史有相似之处,现实中的人在阅读历史、走近历史时才会感到莫名的熟悉,体会到身临其境的现场感,感同身受。鲁迅先生曾经说:“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而已集•小杂感》)。“历史”以它与现实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明白和重视:历史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更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无用之物。历史与现实实在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其实属于同一个气场。若想要在今天活得聪明,活得成功,在有限的人生道路上少走弯路,不论“阔的聪明人”也好,“不阔的傻子”也罢,了解“历史”终究是有益无害,抑或是利多弊少的。西哲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立论的。
历史的相似性,在我看来,可说是俯拾皆是的。随便举个例子,现代社会深为诟病的高校学术腐败,与钱钟书先生《围城》里有关三闾大学群生相的描绘简直如出一辙。《围城》自然是小说,而小说自然是虚构的,可艺术来源于生活,再厉害的虚构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场景,特定的历史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讲,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有关三闾大学群生相的描绘,是曲折和艺术的,但又是肯綮和真切的,是四十年代大学文化的形象写照,是历史真实的艺术再现。
承认了这个前提,我们再来重读《围城》,看到三闾大学的章节,我们不能不敬佩钱钟书先生的历史意识,不能不赞叹钱钟书先生的未卜先知,亦不能不折服于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
对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不当昆虫学家,而来专司一校之长的人事安排,钱先生的感慨是:“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在外国,研究人情的学问始终跟研究物理的学问分歧;而在中国,只要你知道水电、土木、机械、动植物(现在还可以加上航天技术、信息工程……笔者按)等等,你就可以行政治人——这是‘自然齐一律’最大的胜利。”看看现在有多少专家“学而优则仕”,凭着“光电生化”的专业知识而当官作宰或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的,可知“中国科学家进爵”这条规律虽历数十年但依旧是真理。
三闾大学的教授中,不乏韩学愈这样的“克莱登大学”出身的“博士”,杜撰和伪造学历学位而窃取教授之位,这可谓是斯文扫地的丑闻,但是就没有人去认真戳穿他,这更属莫大的讽刺(方鸿渐太老实,没有堂而皇之亮出“克莱登大学博士”头衔,所以煮熟的鸭子飞了,当不成教授只好屈尊当个“如夫人”地位的副教授。怪就怪他脸皮不够厚,心肠不够黑,可叹!)环顾今日的高校,不是也时常见到某某的海外履历属造假,某某的晋升资格系作伪一类消息的曝光、揭露吗?可见,在今天,“韩学愈”之流仍没有销声匿迹。
三闾大学搞任人唯亲,招揽的教师,多是高松年的亲戚、学生、朋友、同事或其顶头上司的亲朋好友,于是人品下流如李梅亭、人品猥琐如顾尔谦等等便缘夤而进,沐猴而冠,成了国立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了。这些人物到了学校后,又开始各自经营自家的山头,搭建自己的圈子,有所谓的“从龙派”、“粤派”、“留日派”、“少壮派”、“汪派”等诸多有形或无形的派系,把整个大学搞得乌烟瘴气,鱼龙混杂。时至今日,这种遗风似乎也不曾绝迹。抱圈子、占山头依旧是人事关系中的常态,这在职称评定、课题立项、经费分配、成果评奖等方面都有很明显的表现。总之,武大郎开店或武二郎按武大郎思维方式开店的现象并不是什么秘密,结果呢,在人事倾轧中人人是条龙,可一旦到了科研教学就有不少人一晃成了虫,寂然无声。但最令人佩服的当属这些人的勇气和狂妄,还动辄想象获诺贝尔奖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据此看来,几十年过去了,大学的某些社会生态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难道不是历史相似性的有力佐证么?
三闾大学也注重教育改革,所以教育部督导到校来贯彻英国高校的导师制,高松年、李梅亭诸人便一窝蜂起,纷纷响应。从小说介绍的情况来看,推行导师制的初衷该是要向西方一流大学看齐,与国际接轨。可是经督导、高松年、李梅亭等人胡乱一折腾,便变成了倡导教师一天三餐都跟学生同桌吃饭之类非马非驴的闹剧,难怪赵辛楣要叹气,“想中国真厉害,天下无敌手,外国东西来一样,毁一样。”今天,我们不少高校也在大张旗鼓搞所谓的国际接轨,生吞活剥国外办教育的经验,让大家为迎评估,搞考核,做工程,填报表疲于奔命,不亦乐乎,口口声声说是要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其实底气却虚得很,让香港等几所高校一搅局(还仅仅是招生一个环节),便有沦为国内二流之虞。成了大家茶余饭后谈笑的资料,实在有些滑稽可笑。这与当年三闾大学推行导师制所闹的笑话,又有什么区别!
三闾大学训导长李梅亭对导师资格的认定有深富“创意”的见解:“中西文明国家都严于男女之防,师生恋爱是有伤师道尊严的,万万要不得,为防患于未然起见,未结婚的先生不得做女学生的导师。”原本以为这是小说的夸张,最近才知道这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不是有南方某省教育主管部门日前作出规定(要知道如今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凡已婚男教师不得与女学生单独交谈相处,否则以违纪论处,要接受校纪校规的惩罚。看来此省高校的男教授、男副教授们今后是不能再动招收女博士生、女硕士生的念头了,不然,每次指导论文时总得另找个不相干的第三者来司陪同旁听之职,岂不是大大的麻烦。由此可知,“瓜田李下”之嫌及其防范,李梅亭与某省教育主管部门的想法的确是惊人的相似,这精神也可算是一脉相承了。
不必再一一引证下去了。我想,上面的例子已经足以说明历史的相似性是无处不在的。而正是因为这类历史相似性的普遍存在,使得大众热心于了解历史,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下,按照自己的理解与认识,解读种种历史现象。于是乎,相对于历史专业研究的“冷”,有关历史的认知与释读的大众化通俗化传播却显示出令人振奋的“热”。
静下心来思考现在历史的“冷”与“热”,同一学科境遇的大不同,不由得哑然发现,现实竟和几年前我在自己第一本随笔集《寻找本色》中所胡乱发的感慨不谋而合,“对于一个人而言,把研究历史作为他(她)自己一份业余的爱好,那是莫大的幸福;可要是把研究历史当做他(她)自己一只赖以谋生的饭碗,那便是真正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