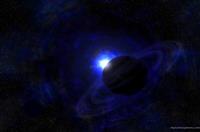「内容提要」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等人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抗战胜利前后,共产党人有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提法。1949年建国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基本延续了此前的定论。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性质、作用提出不同看法。上世纪90年代至今,除深入研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扩张的过程和途径、国家资本如何转化成了官僚私人资本外,不少人认为就性质而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实际上含有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两重性质。
2003年10月宋美龄在纽约辞世,其遗产仅有10多万美元(注:笔者2003年8月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查材料时,曾就近参观宋美龄所住的公寓楼。这是一栋并不怎么显眼的楼房,这种有几十年历史的公寓楼在曼哈顿比比皆是。宋美龄晚年赴美后主要靠孔家后人,即其外甥、外甥女养老,应是事实。),这件事使中国大陆人士颇感惊异。以往,随着历史真相的不断揭示,人们已知蒋家、陈家并没有多少财产,而断定孔、宋两家特别是宋美龄拥有巨额私人财富。现在看来,宋美龄并没有多少私产。至于宋子文,其第一手史料已可在史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查询,史实也会逐渐披露。所谓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家族个人资本,国营资本,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一提法是就经济意义而言,还是蒙上了更多的政治色彩?这些都需要今天的学者们去重新考虑、分析、研究。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人对中国的“官僚资本”问题进行研究和阐释。抗战胜利后国共斗争日趋激烈,共产党方面正式提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一说并对之加以批判。从那以后直到今天,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学术界一直延用这一称谓。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问题新的更准确的研究,首先要建基于该问题学术史的总结。但遗憾的是,史学界至今还少有这方面的学术综述文章。本文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围绕“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问题所发表的代表性论著进行了总结和评述,挂一漏万,还请学界同仁见谅。
“官僚资本”的提法,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注: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用的是“屈维它”的笔名。),首次使用了“官僚资本”一词。他将洋务派经办的官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一种”;将官商合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二种”。1929年,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一文中,揭露清代官僚举借外债时“从中渔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资本”。
1930年,日本学者橘朴在《中国社会的发达阶段》一文中,将官僚资本分为“梁士诒型”和“张謇型”两种。1936年,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将清政府创办的“国营事业的萌芽”统称为官僚资本[1](p492)。
总的说来,这时大家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指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办企业。抗日战争中后期,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国民党官僚利用职权、私人参与投资的企业或金融机构称为官僚资本。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一文中指出:“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治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2](p21)随着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膨胀,马寅初对官僚资本的抨击也愈加严厉,“所谓国营,实即官办”,“假公济私为通病,由来已久,莫可究诘……近来夫变本加厉,由暗偷私窃变为公开劫夺”,“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局面,已呈现于吾人的眼前”[3](p359)。他认为官僚资本会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陈伯达在《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一文中也断言:官僚与买办的经济垄断正从金融业向工业发展,“官营就是‘国营’,‘国营’就是官营”[4].
此时,大家还只是对官僚资本进行揭露和抨击,“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提法还未出现。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5](p1046)。这里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还是指国民党官僚的私人资本以及私人经济活动。
随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治斗争的日益尖锐,共产党人开始将国民政府的国家资产、官僚私人资产、党团资产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公产都划归为官僚资本。
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行了集中论述。他首次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并列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书中论述了四大家族怎样从内战起家,逐渐形成了对金融、商业、工业、农业、文化业的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垄断。他认为,官僚资本是代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是在政治上当权的人物利用政治的强制方法,通过掠夺农民及其它小生产者、压迫民族工业而集中起来的金融资本。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财富做出了初步估算,“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6](p147)。最后,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特点和历史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近代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封建的、买办的资本,是大地主大买办在经济上的联结物;四大家族和中中农交四大银行在经济上的独占,则是官僚资本最高、最集中的发展,是中国半封建或封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制度最后的产物;四大家族对农民、小生产者,乃至民族自由工业,进行了空前规模、空前集中的掠夺;四大家族经济独占是在反人民反革命的军事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掠夺方式是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超经济的方法;四大家族的经济独占,从金融、商业、工业、农业一直蔓延到文化业,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完全腐朽寄生的独占;四大家族的经济独占,是外国独占资本——帝国主义的附属物。[6](p153)
许涤新在1947年写了《官僚资本论》一书,认为官僚资本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他分析了官僚资本的社会根源、构成并指出其本质是封建性和买办性资本。书中分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投资情况,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划分为六种类型:官僚的私人资本;被四大家族控制的国家资本;与国家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民间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及民间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他认为完全属于官僚的资本是那些“利用政治特权获得”并“利用政治特权去运用”的资本;在国民党统治下,国家资本实际上是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7]
同样是在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以及旧式富农结合,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8](p1150)
至此,官僚资本由最初的官僚私人资本扩大到官僚管理下的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有关系的各种类型的资本。四大家族个人资本、国家资本、官僚资本三者间画上了等号,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模糊不清了。最后,人们干脆拿它代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一切资产。
1949年建国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大陆学术界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看法,延续了建国前陈伯达、毛泽东等人所下的定论,并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论述。
吴江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若干特点》一文中,指出在国民党建立政权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了官僚资本的限制和压迫;抗战以后,中国民族资本受官僚资本的排挤、兼并而变得“奄奄一息”。文章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来源、活动、形成、特性作了考察,指出国民党官僚资本同国家政权结合紧密,使国家政权为自己服务,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垄断性。吴江把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特点概括为:一开始便与国家政权结合,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没有任何独立性(对于国际资本主义来说);具有买办性;同封建地主阶级密切联系,有浓厚的封建性;完全从商业、银行投机起家。这种国家垄断资本性质的官僚资本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利益服务,具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是寄生、腐朽透顶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经济基础。[9]
肖灼基在1965年发表了《四大家族的公债投机活动》一文,详细论述了四大家族靠发行公债积累资本的情况。文章指出,四大家族用公债做银行准备金,大量发行纸币,通过发行纸币获取了大量财富。四大家族还利用政治特权对公债进行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并利用公债向其它银行“增资”,形成对金融的垄断。文章认为公债掠夺了农民,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10].
以上几篇文章起到了向百姓普及有关“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基础知识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重点在于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强调其对人民的剥削,和对历史的消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陷于停滞状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相关研究开始启动,仍有一些学者坚持十年前的传统观点。
全慰天的《中国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的形成》、孔经纬的《三重压迫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何干之和刘炼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黄逸峰等人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等论著都持传统观点。
全慰天认为,中国的官僚资本较多的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因此虚弱得多,落后得多;它较少进行资本主义积累,更多地进行原始积累。中国官僚资本的性质,只能是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的、腐朽的和反动的。[11](p350)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的途径和条件进行了概括,认为蒋家是四大家族的核心,由于掌握了政权,就利用财政特权垄断了全国的金融,并逐步对商业、交通运输业、近代工业以及分散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进行垄断掠夺。[11](p353)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孔经纬。他在《三重压迫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一文中,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2]
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共同编写了《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该书论述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将其积累资本的手段概括为:大量发行公债;滥发纸币,形成金融垄断;大搞金融投机、商业投机、外汇投机和黄金买卖;实施“统购统销”和专卖,对商业进行全面独占;借口“调整工矿业”,加强了对工业的垄断;通过大量征用农民土地、增加赋税对全国农民实行残酷的掠夺;在农村兼并土地,使土地更加集中,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成为农村最大的高利贷主。该书认为国民党官僚买办阶级从1927年开始形成,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具有深刻的买办性、高度的垄断性和浓厚的封建性,在政治上以独裁、内战、卖国为其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持传统观点的学者,迄今仍不乏其人。特别是不专门研究民国经济史的学者为数众多,囿于习惯,不少人仍在授课、撰文时因循旧说。
三新观点的陆续提出与新研究领域的拓展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大陆学者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虽然不少人坚持传统观点,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实际上是在政治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形成的概念,遂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评价。
在1985举行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首先围绕官僚资本的性质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些学者指出,从词义上讲,官僚资本应是指依赖政治特权、假公济私的私人资本。官僚资本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概念,使用这种概念去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是有道理的,它能够说明国民政府的本质特征,但拿它去研究经济问题就会导致概念上的含混和范畴上的模糊。另一种意见认为,官僚资本是相对于民族资本而言的,是中国近代经济特有的一种形态,可以沿用下去。只是应该把官僚资本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13]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性质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
同时还对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分别进行了研究,与之相关的论文有30多篇。新的史料也不断得到发掘与利用,使研究得以深入,新的研究视角不断开辟。
第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扩张途径及其历史影响。“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恶性膨胀的过程,及其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所起的影响,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何华国的《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膨胀》(《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郁培文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解析》(《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4期),李凯的《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经济之初探》(《延安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张兆茹、张怡梅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3期),赵兴胜的《战后国民政府国营事业民营化问题研究》(《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齐春风的《1946~1948年间中国走私贸易的影响》(《中州学刊》1999年第2期),李黎明的《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与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孟英的《蒋介石集团在大陆溃败的经济原因浅析》(《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彦宏、周忠的《通货膨胀与国民党政权的覆亡》(《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等文章都涉及到了这一问题,都把官僚资本恶性膨胀作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何华国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手段得以扩张:在内战中垄断军火买卖并不断发行公债;在金融方面形成了“四行二局”,垄断了法币、外汇和黄金,最终形成了金融垄断;控制国家资源和进口物资,最终形成商业垄断。抗战胜利后接受10万亿元敌伪资产,大大增加了四大家族的资产。何华国还对陈氏兄弟的党营资产作了分析,认为由陈果夫、陈立夫控制的党营事业基金达5000亿元。[14]
李黎明着重分析了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资本的恶性膨胀问题。他认为,四大家族的掠夺,破坏了国统区的工农业生产。日本投降后,四大家族接收了日伪开办的各种金融机构、厂矿企业,还将民营企业诬指为敌产予以没收,据为己有。四大家族大量盗卖民营工厂物资,使许多工厂由于缺乏设备而无法开工,使民族工业遭受打击。而名目繁多的各种捐税更是使举步维艰的民族工业背上沉重的包袱,难以恢复和发展。作者认为正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恶性膨胀,扼杀了国统区工商业和农业的生机,造成了国统区工商业、农业、财政经济的崩溃,这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述文章,多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作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来进行研究,对其性质则未作深入的探讨,仍然把国民党政府的资产和四大家族的私人资产视为一体。在对其进行评价时,也多强调它对国民经济的消极影响。
笔者认为,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评价应该建立在对蒋宋孔陈各自真正掌握的资产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对国民政府各种不同的经济机构和组织也应区别看待和评价。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国民政府下设的“资源委员会”——传统上人们视其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郑友揆、程麟荪、张传洪合著的《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一书,比较全面地评述了资源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该书论述了资源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初期活动;抗战前的建设计划;抗战时期各主要事业的建设情况;抗战后的接收以及经济重建规划;改进生产方法的努力;对于对外贸易主权的维护;对于中国神圣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积极支持;对国民党党部势力渗透的抵制;在大陆弃暗投明迎接解放等史实。郑友揆等人认为,用官僚资本概括资源委员会的性质并不恰当。一个原因是,将资源委员会称作官僚资本容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人们一提到官僚资本,就会自然而然地与反动、落后的事物联系起来。他们提出,“资委会的事业在旧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说资委会是一种反动、落后的事务,缺乏历史事实,言之为国家资本企业经营管理机构则更确切些”[15](p3)。
第二,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性质的新认识。在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性质的认知上,学者们有了较为客观、辩证的看法。
杜恂诚在《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是特指国民党时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它只是一个通俗名称,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定义;再加上后来一些人又把它的内涵不断扩大,把官僚的私人资本也包括了进去,并在时间跨度上向上追溯,一直追到清政府创办的企业。由于内涵混乱,时限不清,因此它的外延也变得十分模糊。实际上,它的界限已经无法确认了。[16](p4)
郑会欣追述了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指出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已经改变了以往将国营企业统称为“官僚资本”的做法,而用“国家资本”来代称。因为“国家资本”的提法内涵比较明确,不会将官僚私人的投资与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投资相混淆。作者认为,不能将国家资本、国营资本等同于官僚资本,但应看到“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中国长期以来官僚政治传统的影响下,官僚可以通过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以各种方式将国家资本转化为官僚私人的资本,而且这种转化往往都是以各种‘合法’的途径加以实现的”[17].
陈自芳对有关“官僚资本”的几种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仍应保留“官僚资本”这一概念。官僚资本中应包括官僚的私人资本,而对于官僚的私人资本也要辩证的看待,只有那些依靠政治权利、垄断性很强的私人资本才能定性为官僚资本。作者认为,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应被看做是官僚资本。[18]
武力赞成应将官僚通过特权获取的资本,与国家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区分开的观点。他还提出了官僚私人资本在国计民生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对国民政府的失败到底应该承担多大责任的问题。认为官僚资本只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现象;应将官僚作为一个社会人和经济人看待,他也具有谋取个人、家庭利益的本能和动力;应将官僚企业作为一个企业看,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它的目标;应将研究重心放在分析民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上,深入探讨旧体制与官僚资本形成的关系,细致分析私人资本是怎样利用政治体制的漏洞来谋取私利的。[19]
陆仰渊、方庆秋在其主编的《民国社会经济史》一书中,认为国家垄断资本具有以下三个特点:资本来自政府,并由政府官员经营;对国民经济的某一方面具有垄断性;对广大人民具有压迫性。而官僚资本则另有三个特点:资本不是来自政府而来自官僚的私人投资;经营权掌握在某个或某些官僚手中;掌握这种资本的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某一部门,投机倒把,损公肥私,中饱私囊。[20](p774)也就是说,所谓的官僚资本仅包括官僚私人资本,它和国家垄断资本不是一回事,这就改变了以往国家资本、官僚私人资本不分,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含糊不清的状况。
通过讨论,多数学者达成了如下共识:最好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分为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两部分。这样有助于人们在研究中更科学地看待有关问题,有助于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积累和经营做有区别的分析,更清晰、准确地认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历史作用。
除上述成果外,学者们对四大家族的私有资本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李茂盛认为私有资本应分为自有资本和自筹资本两部分——自有资本指个人拥有所有权的资本,自筹资本指通过各种方法筹集来的、仅拥有使用权的资本。他认为只有自有资本才是一个国民的独立财产。他对孔祥熙的自有资本进行了考察,对孔氏家族在工业、商业、金融业、文化业的资本做了估算,认为原来盛传的孔家约有40亿美元资产的说法是大大夸大了,实际上孔氏家族的资产约为50~100万美元。[21]
李立侠也认为孔家最多是百万而非亿万富翁。[22]两位学者都是将孔氏家族拥有所有权的资产作为评估的对象,改变了人们以往把孔家名义上控制的资产也作为其私有资产进行估算的做法,这样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有关问题。
此外,学术界对宋家资本进行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成果。如陆仰渊在《宋子文和孔祥熙的财产知多少》一文中,对宋子文在工业、金融业、商业三方面的资产进行了评估,认为宋家的资产大约有1000万美金。[23]至于蒋家和陈家的资产,人们的研究还不够充分,至今也没有说清楚其具体数目。
总的说来,学术界到目前为止,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纠正了以往较多地用政治概念理解“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而造成的一些不准确的认识。但由于掌握的史料有限,一些学者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性质的认识仍然因循旧说,在研究过程中就不免出现大而化之的现象;有关四大家族积累资本的过程和方法,相关论文数量虽多,但内容大致相同;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资产的准确数字也有待科学的查证;对四大家族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也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四大家族运用政治特权谋取经济私利的具体史实,也需做具体而微的查证、核实。只有这样,我们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才能有更清晰、准确、实事求是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M].上海;黎明书局,1937.
[2]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3]马寅初全集:第12卷[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4]解放日报[Z].1942-02-08.
[5]毛泽东。论联合政府[A].毛泽东选集(3)[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M].长江出版社,1946.
[7]许涤新。官僚资本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8]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A].毛泽东选集(4)[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吴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若干特点[J].经济研究,1955,(5)。
[10]肖灼基。四大家族的公债投机活动[N].光明日报,1965-09-13.
[11]全慰天。中国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的形成[J].孙健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12]孔经纬。三重压迫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J].北方论丛,1979,(5)。
[13]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研究学术讨论会纪要[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1)。
[14]何华国。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膨胀[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3)。
[15]郑友揆、程麟荪、张传洪。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16]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17]郑会欣。对“官僚资本”的再认识[J].民国档案,2003,(4)。
[18]陈自芳。论中国近代官僚私人资本[J],浙江学刊,1995,(6)。
[19]武力。重新审视官僚资本的几点想法一评<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2)。
[20]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21]李茂盛。孔祥熙私人资本初探[J].山西师大学报,1990,(1)。
[22]李立侠。孔祥熙与中央银行[J].工商经济史料丛刊。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
[23]陆仰渊。宋子文和孔祥熙的财产知多少[J].民国春秋,1994,(1)。
《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
李少兵,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