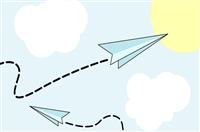
我在新近出版的《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这样写道:“今日之中国正面临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值此特殊时期,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今天遭遇的真正挑战决不仅仅是如何建立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富国或军事强国,而是正确理解中华文明在未来人类文明之林的位置。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决定未来中华民族能否永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人类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决不仅仅取决于是否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而主要取决于中华民族能否建立一种新型的、有独特价值和意义的文明。”
借用亨廷顿的用法,我把文明当作高级、发达、成熟而完整的文化实体,在相当广大的区域里发生影响力、而不局限于种族和国界。比如我们不称伊朗社会(作为一个文化实体)为“伊朗文明”,而认为伊朗是整个伊斯兰文明的一部分。同样,我也不主张日本或韩国现代社会代表一个独立的文明,而倾向于认为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东亚现代文明是可能的。此外,我主张一个可以称为“文明”的文化实体,必定在核心及主流价值、制度架构、社会整合方式、宗教及精神传统等方面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来,这也正是它能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发生持久影响力的原因所在。正如历史所多次见证过的那样,“文明”作为大的文化实体,其形成、兴起和衰落往往经历较长的时段,这不仅与外部的事件或影响(包括其他文明及自然环境等因素)有关,也与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有关。每一个文明都是矛盾的复合体,充满了深刻而剧烈的对立、斗争和融合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前进或倒退、兴起或衰落。
我们深深认识到,要正确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实现认识上的一个重要转轨,即从现代化范式到文明范式——:
(1)现代化范式的局限性
首先,我们知道,“现代化”在西方历史上并不是一个中性词,而是一个带有鲜明的价值立场的术语。这一术语主要盛行于18世纪以后,与当时流行的文化进化论相联,即相信有一种单线的历史进化过程,认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是人类所有民族所不能避免的。早在20世纪初叶开始,就有不少人开始批判这种文化进化观,因为它否定了文化的特殊性,把西方现代文明当作人类一切文明的最高阶段或共同目标,是典型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产物。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由于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学习西方,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化”特征。由此所带来的最深刻问题就是无法为人们回答现代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提供方向。
其次,“现代化”这一研究范式还有一个先天的理论局限性,即预设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这种对传统与现代的割裂,来源于近代早期此起彼伏的时代浪潮,肇始于18世纪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而非出于冷静理性的思考、客观科学的研究。今天我们认识到,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都往往成功地做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而不是最成功地抛弃了传统。尤其是那些后发现代化国家,能否成功地利用传统资源、实现制度创新,恰恰是决定能否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
最后,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广大非西方国家而言,“现代化”这一名词包含着极为复杂的情感和心理因素,它意味着学习西方发达的科学和技术,意味着追求民族富强以与西方抗衡;它包含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还包含在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找不到恰当自我定位等一系列痛苦挣扎。正是这一系列微妙复杂的心理左右支配着无数学人的心灵,影响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思路,造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学科体系和许多学术思潮。
(2)文明范式的必要性
一个多世纪以来,有良知的中国文化人在精神上最深刻的焦虑来源于失去了对一个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基本信念,找不到自己在精神上的真正落脚点。与此相应,无数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内心深处丧失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在中学与西学、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古代传统与现代文明等之间的相互激荡中彷徨四顾。这个问题不解决,使无数文化人在精神上无法摆脱无家可归的状态。由于中国人没有深刻的彼岸意识(即不以死后世界来规范现实生活方式,如在基督教等宗教中所见),高度注重世俗生活,一旦丧失了文明的理想,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和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文明的重建不仅关系着千千万万有教养、有良知的中国人心灵的自我安顿问题,而且是决定了中华文化今后数百年或更漫长岁月根本方向的大问题。
首先,文明重建意味着中国人需要走从对西方列强的消极防御或对抗心理,转变为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建设或再生心理。
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来自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一个多世纪倍受蹂躏和欺压的历史,那些难以忍受的割地赔款的屈辱,以及远远落后于世界强国的现实,都使得国人至今对那段历史耿耿于怀,不能正确看待过去,不能正确定位自己的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然而,将中国与列强对立起来、将中国文化置于其他文化之上,从来都是心理自卑的表现,是一个民族还不够成熟的标志。只要中国人还停留于对自身文化的孤芳自赏,中国人就不可能成为引领全人类进步的优秀民族;只要中国人还沉浸于对自身传统的顾影自怜中,中华民族就不能真正融入全世界。今天的中国人应当需要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走出“落后挨打”的历史悲情,再次拿出广阔的胸襟和恢弘的气度,在全世界色彩纷呈的文化之林中找到中华文明的正确定位。
在过去五千年里,中华民族曾经历过无数次被侵略和蹂躏,无数次分裂和战争,它之所以能历经风雨而不衰,不是我们的先辈擅长打仗,也不是由于中国的国力自古比别国强大,而是由于我们的文化价值理念或文化理想。其中最值得我们拾起的历史经验之一是,早在距今30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起,华夏民族就曾是一个在语言、宗教、制度、科技等方面远比周边民族发达的民族。正是文化的先进性才使得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每当中华民族走向衰微或被占领,它的文化仍然是别人学习的榜样,从而保证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延续。
今天,我们应该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华民族还能象在历史上那样,创造真正先进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复兴和宗教繁荣吗?我们应该相信:只有真正文明、进步的文化,才是一个民族持久生命力的象征;只有令全世界望风而从的文明生活,才能让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真正找到文化自信。孔子云:“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
其次,文明重建不是着眼于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界格局中赢得一时一地的国家利益,而是着眼于它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长存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曾几何时,我们忘记了祖先的教训,把一切寄托在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上,寄托在有一天能够打败某些大国上,寄托在所谓的“实力”上。这其实是心灵空虚的表现,也使我们变成了别人眼中的野蛮人。综观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永远保持经济繁荣,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永远保持国力强盛,而文化的底蕴、文明的信念、人性的活力等等,才是一个民族长治久安的根本,是一个文化长盛不衰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今天的国人,有几个认识到了这一点?一些宣扬儒学的学者,口口声声大谈“和而不同”,但一遇到国际争端,马上想到诉诸武力,强调实力决定一切。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他们内心深处缺乏文化自信的典型写照。
我们非常可悲地发现,多年来,我们在强调“落后挨打”的同时,很少有人强调过:我们应当如何来包容、理解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民族,中国人应该如何学会尊重和爱其他的人从而使其获得拯救,包括那些与我们对立、仇视我们的人们。我们从来认识不到,只有我们学会了尊重和爱每一个与我们不同种族的人,学会了包容和宽恕那些曾经深深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这个民族才能真正成熟,在这个世界上站起来,赢得世人的尊重。
综观历史我们发现,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的最高理想从来都不是追求成为一个经济富国、政治大国或军事强国,也不是为了追求主宰人类事务或凌驾于他人之上的霸权,更不是为了证明来自于华夏中心论的种族优越性;而是追求一个伟大文明的理念,一种可使一个民族长治久安、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文明理想。儒家“夷夏之辨”认为,一个真正文明、进步、合乎人性需要的生活世界,必定会赢得千千万万人的衷心拥戴,只有以善养人的文化才真正有生命力,只有以德服人的民族才无敌于天下。
其三,文明范式意味着彻底摆脱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从文化理想、主流价值、各项制度、社会整合等不同角度来积极建设自己的现代性,以实现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东方与西方之间创造性的融合。正如我们今天在日本、韩国乃至欧美各国经验中所学到的那样,现代化不是传统资源的摒弃,而是其创造性的利用;不是地方性知识的清除,而是其积极的再生;不是东西方必然的对立,而是其有张力的结合。
文明范式不是文明冲突范式。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预设了各国文化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对于不同文化价值体系如何与现代西方文化价值融合发展,基本上持悲观态度。更重要的是,它虽然主张文明的多样性,但对于今日世界各国文化如何结合西方现代文明进行创造性的融合,重建自身新的文明模式或文化价值系统,并无任何任何积极的思路和深入的探讨。由于享廷顿关注的是世界政治问题,他更多地看到的不是文化的融合与创新,而是文明的冲突与战争。
(3)文明重建的主要任务
文明重建的首要任务,是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所谓文化的最高理想,我指一个民族对于共同体生活最高境界的梦想或追求,或通向这一境界的核心价值。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人性体验永恒价值、实现自我超越、找到安身之本的文化价值,可以给一个民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带来无穷的生机与活力,成为激发无数人奋斗不息的无尽的精神源泉,和该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真正找到自信的精神支柱。一个文化的最高理想往往表现在该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或文化理念中,为文化中有教养的人士所阐发或论证,为不同阶层的精英分子所广泛接受和崇尚;它往往是志士仁人们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精神动力,和一个民族在残酷的打击和磨难中坚强地站起来的精神支柱,或成为该文化中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鞠躬尽瘁追逐的人生梦想。
让我们从“夷夏之辨”来谈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儒家“夷夏之辨”的精神实质在于对文明与野蛮的区分。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人把中国等同于文明,把少数民族等同于野蛮,使夷夏之辨演变成中国文化中心论甚至于文化霸权主义,但是我们从古人的学说中可以发现,这种中国文化中心论或文化霸权主义从来不是儒家夷夏之辨的精神实质。“修文德以来远”(《论语•季氏》),“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才体现夷夏之辨的根本精神。
从“夷夏之辨”出发,今日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或者可以这样来表述: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生命尊严与价值的实现,潜能与个性的发挥,幸福与自由的确保。这些或许可表达为八个字:“保合太和”,“各尽其性。
文明重建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重新确立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岁月里,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由孔子等人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奠定了的,包括仁、义、忠、信、孝、礼等。20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对西方文化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等的崇拜中,忘记了中国文化的正确方向。我曾在有关文章中指出,
如果问什么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品质?你也许举出忍辱负重、自强不息、勤劳朴实、将心比心、善良厚道、老实本分等,但决不可能举出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权这些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利益膨胀为特点、很少“反求诸己”的价值。[在中国历史上,]仁、义、忠、信可以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核心价值,但是民主、自由、人权则不能,原因在于它们可能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平衡被打破,导致无止境的纷争、仇恨甚至杀戮;当面子被彻底撕破,当人情不复存在,中国人之间是很难相互妥协的,严重时导致社会分裂、解体或剧烈动荡;一旦分裂发生,战争和杀戮少则几十年,多则数百年。这里面的逻辑十分简单,那就是我们无法逾越中国文化的习性。惟其如此,与其提倡抛弃它,不如研究和认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它,以及如何对症下药地诊治它。比如,今天我们崇拜的英雄人物,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的,包括孙中山、鲁迅在内,都是为他人、为民族而献身的人,而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者。
相反,在西方文化中,真正的英雄往往是那些将个人自由看得比生命还高贵的人。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习性决定的,同时也说明了个人自由在不同文化中的功能并不一致,也不必强求一致。但这决不是说,中国人不需要自由、人权和平等,我只是说相对于仁、义、忠、信等来说,它们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中华读书报》2010年5月26日)
显然,未来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可能局限于仁、义、忠、信、礼、孝等,也不可能排斥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价值,但是只有我们正确地理解了儒家所曾倡导的那些价值为何曾长期成为推动中国文化进步的核心价值,我们才能找到重建中国文化基本或核心价值的正确道路。
文明重建的第三个重要任务是实现行业及社会的自治及理性化。我曾在有关论著中指出,那种认为儒家将治国希望寄托于个别人的道德与人格、而不能落实于一套制度体系这一流行观点过于地简单化了。正如狄百瑞在《亚洲价值和人权》等书中所揭示的那样,中国文化中自古不乏促进行业和社会自治的优良传统;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在儒家思想中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源,是儒家王道思想的自然要求。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借助于行业传统、职业规范和社会风尚,来约束大多数人和一代代后来者,可以达到与西方的“法”同样的功效。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代表了中国文化中尊重人的尊严、个性和价值的传统,却避免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形式至上和过份倚重个人权利的缺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乃至未来中华文明的样式有启发意义。须知西方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形式至上特点和个人权利绝对化倾向,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文化土壤。
文明重建的第四个重要任务是制度创新。我曾有关地方指出,只有理解了中国文化的习性(即以人情和面子等为枢纽的关系本位等,包括梁漱溟、费孝通、许烺光、黄光国、Richard Nisbett等人对此多有研究),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中国文化中的制度建设适合于走“礼大于法”的道路。与此相应地,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文化不适合于走一条以抗争和大众运动为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民主,而是说以儒家贤能治国所代表的政治制度模式与现代民主政治未必是相互矛盾或冲突的。显然,我们不可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思考,以分权为特色的西方法治模式如何在中国文化中演变为一种相对自治而不是绝对独立的法治模式。
(原发表于《文汇报》2012年2月27日。发表时有删节,此文以发表前原文为基础修订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