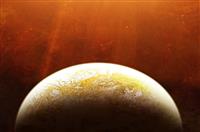尼克斯•卡赞扎斯基在《希腊行》中说:“如果我们懂得如何倾听,如何去爱,那么我们对于希腊的美景就不会只有无知的震撼。这里的风景有其姓名,它们与记忆紧密相连——我们在此受辱,我们在此荣耀;圣像上的鲜血从土里长出,风景立时变成丰盈且无所不包的历史,希腊朝圣者的整体精神因此陷入混乱之中。”
异邦人很难理解卡赞扎斯基这个现代希腊人的纠结心情。当雪莱说:“我们都是希腊人。”我相信他真正想说的是:“我们都是古希腊人。”
的确如此!行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持续不断地沉醉于一个连最小的悬岩都能让人联想到那里有神和英雄居住”的奇妙体验。而在雅典卫城脚下的agora(古市场)里徜徉时,我们期盼遇见的是伯里克利、克里斯提尼、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伊克提努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正是这些2500年前在一两个世纪里以奇迹般的方式麇集在这座希腊小城的天才们,造就了一个短暂而辉煌的黄金时代,并为西方文明的整体气质定下基调。在深受古典文化熏陶的异邦人心目里,希腊的精神世界似乎应当是而且永远是通体闪耀着理性、光明、和谐以及无尚的光荣,混乱和困顿从来与它无缘。
然而,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现代希腊人来说,历史并没有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希腊后戛然而止。他们不但生活在2500年前那个伟岸的背影中,同时还要面对和消化马其顿人、罗马人、斯拉夫人、法兰克人,加泰罗尼亚人,弗罗伦萨人,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对他们身体的劫掠与统治,以及精神的同化和异化。这种重重复重重的记忆累积,让卡赞扎斯基绝难天真地沉醉于“神和英雄”的故事,因为古典时代那短短一两个世纪的光明不足以照亮此后漫长的混乱与黑暗。
神和英雄居住的城市
雅典的诞生是一个神话。
这里的山很低,天很近,神与人所以常往来。传说腓尼基人打算在阿提卡半岛的南端建城,海神波塞冬与智慧女神雅典娜闻风而至,竞相争夺保护神的地位和命名的荣耀。万神之王宙斯于是定下规则,那个能为人类提供最有用之物的神将最终获胜。波塞冬用三叉戟敲打地面变出一匹战马,雅典娜则用长矛变出了一棵橄榄树,前者代表战争与武力,后者象征着和平与富裕,腓尼基人踌躇再三,决定选择雅典娜作为他们的守护神。
雅典娜的庇护并没有为雅典人立即带来和平与富裕。大约从公元前9世纪直到公元前6世纪,当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纵横捭阖,成为希腊人公认的领袖时,雅典只是希腊诸城邦中二流甚至三流的角色。甚至到了公元前510年,波斯国王大流士还曾经好奇地问道:“雅典人是些什么样的人?”
波斯人很快就有机会了解雅典人。公元前490年,大流士在马拉松平原上遭到雅典人的顽强抵抗,铩羽而归。10年后,大流士之子薛西斯率领10万波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再次进犯希腊,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率三百勇士在温泉关拼死抵抗仍以失败告终,波斯人继续向南挺进,很快兵临雅典城下,断续绵延长达十年的希波战争到了最后关头。大敌当前,雅典人被迫弃城入海,退守萨拉米斯岛,他们隔海相望波斯人焚烧他们的房屋,毁坏卫城上的神殿,尽管人人“怀着恐惧和沮丧的心情”,但还是下定决心与波斯人决一死战。
这是一场智慧对于武力的胜利。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派奴隶到波斯军中诈降,谎称希腊人将乘夜色从萨拉米斯湾的西面出口撤退,波斯人信以为真,遂遣主力战船前往堵截,结果在狭窄的萨拉米斯湾中自乱阵脚、挤作一团,希腊人于是一举扭转战局。据称薛西斯巍然坐在岸边观战,清晨时分他曾清点过海上的万船千帆以及十万雄兵,可当夕阳西下之时,薛西斯只剩下悲叹之声:“他们在哪里呢?”
萨拉米斯战役的胜利意义重大。经此一役,薛西斯心灰意冷,返回小亚细亚,并且一去不返。“现在希腊不再只有一个领袖,而是两个”,英国学者基托用史诗般的语言这样颂扬雅典的崛起:“这个尚处于少年时期的平静的城邦,如今同英雄的城邦斯巴达并肩而立,受到所有人的景仰。”
雅典人的卓越与荣誉
雅典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希波战争中,至少有一个波斯人部分接近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是薛西斯的堂兄弟,特里坦塔伊克美斯,当他听说希腊人在奥林匹亚运动会上获得的奖赏不是金钱而是一顶橄榄冠时,他向所有在场的人们说:“哎呀,玛尔多纽斯啊,你率领我们前来对之作战的是怎样的一些人啊,他们相互竞赛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金钱啊!”
荣誉的确是所有希腊人最为看重的东西。不过特里坦塔伊克美斯不了解的是,雅典人看重的荣誉与斯巴达人大有不同。大约50年后,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初期,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公葬典礼上发表演讲,比较了雅典与斯巴达的差异:
“我们允许任何人进入我们的城邦,我们不会由于害怕外人看到太多而定期将他们驱逐,因为在战争中我们依靠的是我们自己的勇敢和胆略,而不是阴谋诡计。我们的敌人为了备战,从小就受到非常艰苦的训练;我们过我们的安逸生活,但面对危险我们信心百倍。事实上,没有其同盟的帮助,斯巴达从不敢单独地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勇敢来自于天然的气质,而不是法律的强迫。因而,我们拥有两方面的好处,一则我们无须基本的艰苦训练,二则当考验来临时,我们同他们作的一样好。我们热爱艺术,但不作过度的炫耀;我们爱好智慧,但不会就此变得柔弱。”
伯里克利的这番言论无疑有其修辞学上的夸张,但他描述的图景基本真实,实则,他本人就在实践着这样的文明理想。
关于伯里克利,有这么一件让人心驰神往的逸事:大约公元前450年前后,伯里克利率领一支希腊舰队在爱琴海上的一个岛屿附近抛下船锚,准备翌日清晨发起攻击。夜幕降临之时,伯里克利邀请他的副手们一同把酒畅谈,当一个年轻的侍从为他们斟酒的时候,伯里克利目睹少年俊美的面庞,有感而发,引用一个诗人的文字形容他的脸上闪烁着“紫光”。旁边那位年轻的将军不大同意:他从来认为那个形容颜色的词选得不合适,他更喜欢另一个诗人把年轻的脸庞形容成玫瑰般的颜色。伯里克利反对他的看法,谈话就这么进行下去,每个人都援引一句适当的话来应答对方,仿佛战争的阴影从不存在。
我们很难想象斯巴达人会在温泉关战役前夜,在餐桌上进行优雅玄妙的文学讨论。斯巴达的公民从出生起就要接受拣选,病弱的孩子要被抛弃,强壮的留下接受战争的训练,文化教育被认为是无意义的事情。他们从小就被教导,话说得越少越好,想得越少越好。斯巴达人相信,战争是人类最高尚的活动形式,战死疆场是此生最大的荣誉。雅典人则与此完全不同,他们靠辩论和劝说来做出决定,习惯去“思考、观察、理解、怀疑、质问每一件事物”。雅典城邦的男性公民会在战争来临时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但平时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匠、建筑家、诗人或者哲学家。雅典人从不认为战争是一件好事,然而又务实地承认战争是必要的,就好像他们从来不认为战死沙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并不妨碍他们会为了公共的利益和城邦的荣誉赴死。
古希腊文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arete,后世把它翻成“美德”或者“德性”,其结果是“丧失了所有的希腊风味”,因为美德或者德性是一个评价道德的词汇,但在古希腊文中,arete“被普遍地运用于所有领域中”,最为合适的翻译应该是“卓越”。当“卓越”一词被运用到人的身上,“它意味着人所能有的所有方面的优点,包括道德、心智、肉体、实践各方面。”
人因“卓越”而获得“荣誉”。当伯里克利率领雅典军士在前线英勇作战,与哲学老师阿那克萨戈拉探讨nous(心灵)的意义,大战前夕与副手探讨形容词的精确性,在阵亡将士公葬典礼上发表震古烁今的演说,他的“卓越”令人目眩,因为他全方位地实现了人在道德、心智、肉体和实践的潜能。相比之下,斯巴达人企图把自己的孩子培育成战争机器,虽然不乏英雄主义的特性,但依旧是对“卓越”的狭隘理解。也正因为此,在人类的文明史上雅典人获得的荣誉最终要远多于斯巴达人。
雅典帝国的兴
希波战争后,雅典迅速步入一个生机盎然、元气充沛的黄金时代。
雅典人有充分的理由自感高贵。基托说:“那些目击这场胜利的雅典人,从他们的父辈那里得知,梭伦如何使阿提卡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走向富裕,同时奠定民主的基石;他们自己亲眼看到庇西斯特拉图将粮种借给穷人,并使平静的雅典逐步成为颇受其他希腊人注目的城邦;中年时,他们看到了僭主制的消亡以及一种新的自由制度由克利斯提尼一手建立起来。”而今,雅典人又在萨拉米斯战役亲身证明了自由和理性要比专制和恐惧更强大。
从公元前467年到公元前428年,雅典迎来了长达四十年的伯里克利时代。斯时的雅典自信而博大,吸引着最具才华的希腊人来此汇聚,这些以集体形式涌现出来的天才为此后2500年的西方文明奠定基石,以至于诗人王尔德感叹说:“实际上,我们现代生活中的一切都受惠于希腊人。”
作为十将军之一,伯里克利虽然貌似与其他九位将军分享权力,但通常都由他一人定夺大事。修昔底德对此的评论是“以民主的名义,行一人执政之实。”然而,雅典仍不失为一个民主的政体,因为伯里克利的权力必须要通过一年一度的选举来赋予,他之所以能够担任如此之久的公职,全赖他的卓越才能和公正品格。
雅典成为提洛同盟的领袖之后,势力急遽扩张,雅典帝国的轮廓已经呼之欲出。公元前454年,伯里克利做出了一个影响后世的重大决定:提洛同盟的总部与金库迁往雅典,直接受雅典支配,盟金实质上变为“贡金”。与此同时,他提议把盟金用来修复被波斯人摧毁的雅典卫城上的神殿,让雅典成为一个“人们为了任何目的都乐于前往的城市”。
投票表决这个计划之初,多数雅典人主张把钱款分摊给个人,以满足他们的一己之私欲,伯里克利回应道:“好极啦,这些建筑费不要列在你们的帐上,归我付好了;在上面刻字的时候,刻我的名字。”雅典人听他这么一说,都齐声高喊:“叫他尽量花……工程完成前不要节省用钱。”
伯里克利终于如愿以偿。公元前449年,他委托建筑家伊克提努斯和雕塑家菲狄亚斯等人兴建供奉雅典娜的帕台农神殿,11年后主体建筑完工,雕刻工作则延至公元前432年才告结束,此时距离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仅有一年时间。普鲁塔克赞扬这些建筑“给雅典带来了最赏心悦目的装点,也给人类带来了最大的惊异。”任何亲眼目睹过雅典卫城的人都不会觉得他在耸人听闻,哪怕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饱经炮火摧残和劫掠的残垣断壁。
这是雅典最为辉煌的时刻,同时也是一个即将走向衰败的时刻,历史的起承转合总是如此富于戏剧性。
雅典帝国的衰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战火断断续续蔓延了27年之久,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被卷入到这场战争中。战争的真正起因众说纷纭,一个流行但略显讽刺的观点是,雅典帝国正在逐渐丧失其至大中正的特性,对同盟者变得异常专横拔扈,结果导致斯巴达“自告奋勇跳将出来充当希腊的自由斗士”。
战争初期,雅典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辉煌将被终结。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0年那次传颂千古的著名演讲中骄傲地宣称:
“我们的政体名副其实为民主政体,因为统治权属于大多数人而非属于少数人。在私人争端中,我们的法律保证平等地对待所有人。……雅典的公民并不因私人事业而忽视公共事业,因为连我们的商人对政治都有正确的认识与了解。只有我们雅典人视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为无用之人,虽然他们并非有害。在雅典,政策虽然由少数人制定,但是我们全体人民乃是最终的裁定者。”
今天看来,伯里克利的这次演讲有如天鹅之歌,既是对雅典伟大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礼赞,又像在总结陈词他个人的成就以及政治上的理想。
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降临雅典,城邦中约四分之一的生命被夺去,垂垂老矣的伯里克利亦未能幸免。战争仍在继续,局势几经起落,雅典虽有机会扭转乾坤,终因失去了伯里克利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以失败告终。据说雅典陷落之后,斯巴达人一度要彻底摧毁这座城市,就在暴行实施的前一夜,斯巴达人召开盛大的庆功会,席间有人背诵了欧里庇得斯的一段诗歌,真不知是应该感谢欧里庇得斯的绝妙章句,还是要感谢斯巴达人血液里终究流淌着的古希腊精神。总之,在那一刻斯巴达人聆听着那美妙的、动人的诗篇,忘掉了胜利,忘掉了复仇,“他们一致认为一个能产生这样伟大的诗人的城市绝对不应该遭到毁灭。
”
公元前399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第5年,此时的希腊政治正处于“混乱、乏味并且令人沮丧”的时刻。斯巴达人赢得了战争,但他们从未做好准备担当起希腊人的领袖,失败者雅典则陷入了极端的无序之中。令人扼腕的是,斯巴达人没有摧毁雅典的城市,雅典人却自行结束了伟大的黄金时代。这一年,重新夺回政权的民主派人士开始反攻倒算,他们找到70岁的苏格拉底作为靶子,以蛊惑年轻人和引进新神为由判他死刑。威尔•杜兰在《希腊的生活》中认为,“黄金时代随着苏格拉底之死而结束。雅典的躯体与灵魂都已经衰竭,只有用长期战争极度的痛苦败坏了雅典人的品格,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残酷地对待米洛斯岛,对米蒂利尼岛的狠毒裁决,将凯旋而归的将领集体处死,以及将苏格拉底献于一个衰亡信仰的祭坛上。”
亚历山大大帝与希腊化的世界
漫步在今天的雅典卫城脚下,最让人侧目的风景之一是三三两两倒卧路边的狗,不管是清晨还是午后,它们总是四肢舒坦、矢志不渝地酣然大睡,只有亲身体会雅典阳光的炽热和清透,才会恍然大悟于犬儒主义(Cynicism)的词源为何出自古希腊文“Kynikos”(狗),以及第欧根尼为什么会对虚心拜访的亚历山大大帝出言不逊:“走开,别挡住我的阳光!”而后者的反应也适足表现出一个来自野蛮民族的征服者对于文明的尊敬,据说他在扫兴而归的路上感叹:“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那么我宁愿是第欧根尼。”
亚历山大对雅典的尊敬比对第欧根尼尤甚。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征服希腊后,旋即挥兵北上多瑙河,不久雅典城内盛传亚历山大战死,希腊人蠢蠢欲动准备独立,亚历山大闻讯暴怒,掉转马头南下,一举扫平了希腊北部城邦底比斯,将其夷为平地,子民则贩为奴隶。然而他却原谅了雅典的背叛,不仅如此,他还将亚洲之战的许多战利品奉献给雅典卫城,把波斯国王薛西斯掳走的雕像运回雅典,并在一次艰苦的战役之后说:“啊!雅典人呀!你们相信为了得到你们的赞美,我曾历尽艰险?”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远征东方,此后再未踏入希腊领土半步,但是他对希腊的崇敬之情却从未消减,马其顿铁蹄所到之处,希腊的建筑、戏剧、哲学乃至习俗风化也落地生根。亚历山大在东征的12年里共建立了70多座希腊式的城市,而且多派遣希腊人而非马其顿人屯戍,因为亚历山大希望当地的土著居民习惯于城市生活并竭力模仿希腊文化。亚历山大本人在东征期间,一直让亚里士多德的侄儿随侍左右,在他酒醉自以为是阿喀琉斯之时为其吟诵荷马史诗。
“亚历山大的名字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个崭新的时代便是“希腊化”(Hellenistic)的时代。此时的雅典依然作为文化的圣地继续被世人景仰;但是与此同时,昔日那咄咄逼人的自信却日趋衰颓。
我们都还记得“荣誉”是希腊人最为看重的东西,但是恰如德尔斐神殿的箴言“凡事勿过度”所警示的那样,对荣誉的过度追求会助长个人的野心且带来无尽的争斗。全盛时期的雅典一度能够维持这妙到毫巅的平衡与节制,但不久便被帝国的野心所吞噬。
当一个元气充沛的黄金时代逐渐消逝时,反映在哲学思想上就是对何谓“至善生活”的举棋不定。亚里士多德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两个备选答案,一个是政治家的政治生活,一个是哲学家的沉思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后者才是更高的境界,因为与哲学家的至善生活(沉思)相比,政治生活的荣誉显得太过肤浅——荣誉取决于授予者而不是取决于接受者。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固然很有哲理,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希腊人对于“幸福”的古老定义:“生命的力量在生活赋予的广阔空间中的卓异展现”,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当哲人们开始贬抑荣誉的地位,反求诸己寻找内心的自足和平静时,希腊人正在远离那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到得犬儒主义与斯多葛派成为主流哲学,希腊人“以严冷的目光”只看见“一个喜悦全无的世界”。
“小希腊人”
在希腊被罗马征服之前,希腊内部早已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威尔•杜兰说得好:“任何大国在未经自我毁灭之前是不会为他国所征服的。”幸运的是,希腊人再次遇到一个对其文明心向往之的征服者。
公元前156- 155年,日薄西山的雅典政府为求减轻罚金,派遣三大哲学学派的领袖前往罗马游说,分别是柏拉图学派的卡尼阿德斯,斯多噶学派的巴比伦的第欧根尼,以及亚里士多德吕克昂学园的克里托劳斯。其中,卡尼阿德斯的演讲在罗马引起轰动,思想的魅力让罗马人趋之若鹜、如痴如狂。虽然这三人最终被罗马元老院放逐,但是从此希腊的道德、哲学和艺术在罗马上流社会风靡,几乎所有的罗马皇帝都是斯多葛派的信奉者,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沉思录》的作者马可•奥勒留。
文化上的征服无法挽回国力上的衰微,仅仅十年后,也即公元前146年,雅典人被强大的罗马军团击溃,希腊从此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公元前86年,雅典再次遭到罗马大将苏拉的洗劫。这一时期的雅典穷困潦倒,他们被迫出售萨拉米斯这座凝结着希波战争光辉记忆的岛屿,柏拉图的雅典学园也因战火从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摩迁入城内。尽管如此,作为知识中心,雅典仍旧吸引着东西方的无数学者前来朝圣。
罗马诗人贺拉斯有句名言:“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其野蛮的征服者,将文艺带进了粗野的拉丁姆。”到公元前2世纪末,希腊语已经成为罗马人教育中的第一语言,从非洲到意大利,从高卢到埃及,希腊的语言和文化畅行无阻。
罗马人以一种果敢的姿态从希腊文化中为自己攫取营养,为世界播撒光明。这种亲希腊主义到哈德良皇帝在位时期达到了最高峰,他曾三次到访雅典,并于公元131年兴建哈德良拱门,这座凯旋门把当时的雅典城分成新、旧两区:以东为哈德良所扩建的新市区,以西则为古市区。拱门的框缘两面各雕刻有一道题字,面向雅典卫城的那一面写着:“这里是雅典,忒休斯的远古城市。”而面向新城的那一面则写道:“这里是哈德良的城市,而不是忒休斯的城市。”
这一正一反两道题字折射出罗马人的复杂心态:对于文明的古希腊始终心怀尊崇,面对“当代无精打采的希腊人”又难掩心中蔑视。与此相对,作为被征服者,希腊人的内心更加五味杂陈,其中“有仇恨,也有钦佩、惧怕、感激、愤怒、失望,尤其还有慌乱。”
一个至今让希腊人耿耿于怀的例子是,希腊人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就一直自称“Hellenes”,然而罗马人却用语含贬义的新创字“Graeculi”(意为“小希腊人”)蔑称之,这个词最终化为“Greece”并沿用至今。
昏沉与困顿
罗素说:“基督教出世精神的心理准备开始于希腊化的时期,并且是与城邦的衰颓相联系着的”。希腊化后,帝国太大,城邦的政治关怀不复可能。身处一个苦难深重的世界里,人民不会关心“如何才能创造一个好国家”,而是孜孜以求“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并且,这幸福的实现通常不在现世,而在彼岸。
然而,当圣保罗于公元51年初抵雅典时,发现雅典人并未做好信仰基督教的心理准备。圣保罗看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知之神”,于是企图调和基督教的观念与希腊哲学,劝说希腊人相信这“未知之神”就是“创造宇宙和万物的上帝”。这是雅典人第一次与基督教思想亲密接触,雅典人对于圣保罗的反应是:“看看到底这个捡破烂的家伙,他想要证明什么?”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将罗马帝国的首都从罗马迁至拜占庭,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至此罗马帝国一分为二。西方的罗马帝国信奉天主教,东方的拜占庭帝国信奉东正教。为了彻底根除异教思想的影响,公元529年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宣布永久关闭柏拉图的雅典学园,这一事件被认为是雅典历史的“转折点”——支撑着古典主义理性世界的最后一根柱子坍塌了。从此帕台农神殿里不再供奉雅典娜,它成为了圣母的教堂;希腊人不再自称希腊人,而是自称罗马人;雅典不再是“人们为了任何目的都乐于前往的城市”,不再是知识中心与自由思想的发源地,而成为拜占庭帝国一个无足轻重的省城。
由此往后的雅典历史充满羞辱、黯淡无光。公元582年,斯拉夫人入侵雅典,这一次入侵和以往都不同:雅典被彻底地摧毁了——不是征服而是摧毁,史书记载雅典直到两个世纪后才慢慢恢复过来。再以后则是法兰克人,加泰罗尼亚人,弗罗伦萨人,威尼斯人……
最后占领这座城市的外来者是土耳其人。公元1453年,奥斯曼帝国灭拜占庭,改君士坦丁堡为伊斯坦布尔。3年后,奥斯曼帝国征服希腊。
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实在是一件微妙难解的事情。希腊历史上曾经被四个帝国长期统治:马其顿、罗马、拜占庭以及奥斯曼帝国,对于前三者希腊人似乎都已经欣然接纳为“我”的历史。比方说,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的讲解员在自我介绍时会骄傲地宣称“我与亚历山大大帝同一个姓”;可是当我们与一路陪同的希腊姑娘聊起伊斯坦布尔时,她会坚称那是君士坦丁堡,仿佛一切都还停留在拜占庭时期,过去的悠悠500多年历史从未发生过;当被问及奥斯曼帝国给希腊人留下了什么,雅典国家美术馆馆长玛丽娜女士的回答最为巧妙:只有多尔玛与木萨卡!翻成中文是白菜饭卷与碎肉茄子蛋!
太近的历史总让人呼吸困难,更何况这其中还有种种难以言表的痛苦与回忆。
威尔•杜兰用“昏沉”一词来形容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希腊。据考古学家考证,到1676年,雅典已经衰败成为一座人口不到7500人的乡村小镇,而且她马上就要面临一次最具毁灭性的打击。1687年9月26日,威尼斯人围攻雅典,一枚炮弹击中帕台农神殿,当时里面存放着土耳其人的弹药,剧烈的爆炸声中神殿顷刻间变成废墟。拉伯德伯爵后来痛惜地说:“我们将永远哀叹一座建筑完美、历经两千余载、岁月的摧残和人世中的野蛮行径都无法将它奈何的宏伟古迹竟毁在了基督教欧洲的手里。”
雅典不是悲剧
叔本华说,分析到最后,悲剧的快感是一个接受问题。古希腊悲剧反复想要阐明的一个道理是:既然事情非如此不可,那么好,我现在就来完成你的意愿。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慨然接受,它固然与斗士的反抗精神无关,但也与默认和屈从不同。换言之,古希腊的悲剧精神在于,“它接受生活,是因为它清楚地看到生活必然如此,而不会是其他的样子。”
1687年那次爆炸之后,帕台农神殿与卫城的噩运并未终结,此后100多年里,雅典历经西方列强的洗劫,大量艺术珍品被运往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慕尼黑雕刻陈列馆以及巴黎的卢浮宫。雅典似乎注定是一个悲剧,然而19世纪的希腊人并不准备接受它,这不是因为他们遗忘了古希腊的悲剧精神,而是因为他们保存着“对希腊古代自由、马拉松战役和温泉关战役的记忆”。
就在《米洛的维纳斯》运抵巴黎的时刻,希腊独立战争的第一次起义爆发了。这些身着短裙、头戴蓝流苏红便帽的希腊民兵们决定“在祖先的坟茔上”为了自由而战。
1827 年,支持希腊独立的英法俄三国组成联合舰队,在纳瓦里诺湾全歼奥斯曼帝国舰队,从军事的角度看,是这一胜利最终促成了希腊的解放。但是对于希腊人来说,这场独立战争只让他们记住了一位英国诗人的名字:拜伦。
拜伦于1823年8月抵达希腊,次年因风寒不幸去世。他的死未曾换来任何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对于一个神和英雄驻留过的民族,还有什么比唤醒他们的卓越与荣誉更重要的?是拜伦的死奏响了久已喑哑的竖琴声,是拜伦的死激发起早已沉寂的英雄颂歌,所以希腊人才会给拜伦最高的礼赞和荣誉。
在《哀希腊》中,拜伦写道:
火热的萨弗在这里唱过恋歌;
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并兴,
狄洛斯崛起,阿波罗跃出海面!
永恒的夏天还把海岛镀成金,
可是除了太阳,一切已经消沉。”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说:“希腊人拥有相同的血缘、相同的语言,共同的神殿、祭礼和共同的习俗。”2500年之后,雅典大学的哲学教授佩里格里尼斯这样比较古希腊人与现代希腊人的共同之处:“我们生活在相同的地域,拥有相同的语言。仅此而已。”
每当夏天来临的时候,希腊群岛上的太阳依旧会把海岛镀成金色,但是神和英雄们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