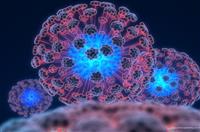(河北大学 哲学系,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本体”虽是哲学的核心性概念,但又常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事实上,本体大致可归结为三种不同的形态:其一,作为“事实本体”的“客体”形态;其二,作为“价值本体”的“主体”形态;其三,作为“客体”与“主体”之融合一体的“道体”形态。概括地看,传统西方哲学之所重者在“客体”形态,传统中国哲学之所重者在“主体”形态,而就未来整个哲学的发展来看,作为“客体”和“主体”之结合与超越的“道体”乃可能是一种代表哲学发展方向的本体形态。
“哲学”作为一门在超越层面研究事实与价值的学问,自发生之以来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回顾哲学史不难发现,本体论几乎伴随了哲学的发展历程,甚至本体论常常可以成为哲学的代名词。例如,熊十力曾说:“谓哲学建本立极,只是本体论,要不为过。”(《熊十力全集》第3卷,第15页)之所以如此,在于本体论乃形而上学的核心,而形而上学乃哲学的主体内容。不过,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本体往往呈现为不同的形态。也就是说,伴随着哲学界对本体探讨的不断深化,本体之形态并不是固定且一成不变的,而是表现为一定的阶段性。所谓本体形态,是指本体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属性。对于本体形态进行厘清和展望,不仅助于对哲学本质的理解,亦有助于对哲学发展方向的把握。下面,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整个世界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圣经》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圣经·创世纪》)不仅西方经典如此,中国经典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人也是神创造出来的。例如,“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说文解字·卷十二》)“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絙泥中,举以为人。”(《太平御览·卷第七十八》)根据中外经典这些记载,可以推导出两点认识:其一,神是无限的、完美的、圆满的;其二,人是有限的、欠缺的和不圆满的。对应地看,前者指神的本性,即“神性之实”;后者指人的本性,即“人性之实”。当然,从经验上讲,对于“神性之实”,我们既不能证成,亦不能证伪,所以不能妄下论断。不过,对于“人性之实”,我们仅凭经验即可下论断。即,其一,人生是短暂的,与永恒之间存在着张力。其二,知识是相对的,与绝对真理之间存在着张力。其三,意义是相对的,与终极价值之间存在着张力。由此来看,无论就人的肉体生命和人的知识,还是就人的价值追寻,人所表现出来的都是有限性。正是基于此,我们才说“人性之实”乃是有限的、欠缺的和不圆满的。质言之,人是有限的。
然而,人虽是动物,但非一般动物;一般动物是绝对有限的,而人的有限性是相对的,因为人类总是力求突破有限以追求无限。历史地看,人类这种突破有限以追求无限的努力表现为对于智慧的追求。具体来讲,相应于上述人之三个方面的有限性,人类对智慧的追求亦表现于三个方面:其一,突破生命的有限性,追求长生不老。这是人类一个古老而天真的梦想,史料对此有相当丰富的记载。比如,秦始皇曾派谴徐福率童男童女入海求长生不老之仙药。(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其二,突破已有知识,向绝对真理追寻。此种追寻表现为对已有知识的突破,故人类知识不断积累与增加,以至于曾出现“知识爆炸”之类的概念。其三,突破相对价值,追寻终极价值安顿。即,不断进行价值的探索,以寻求心灵的最终安顿。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这三个方面的追寻促生了三种智慧:第一个方面的追求促生了宗教。人类为了超越生命的有限性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探索:一是直接追求肉体的不朽,即长生不老。然而,这种追求是一条“死胡同”。二是追求灵魂不朽。尽管不同宗教的主张各不相同,但追求“灵魂不朽”乃是所有宗教的发生学原因。第二个方面的追求促生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即,对于自然界之知识性的探索促生了自然科学,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促生了社会科学。第三个方面的追寻促进了人文学科的产生。即,基于人类心灵世界而对价值的探索促生了人文知识。
不仅如此,就生命演化的历程来看,人类是地球上出现的惟一能够“反思”的物种。所谓“反思”,是指对思考本身进行再思考,即对理性本身进行再思考。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类对于上述智慧的“反思”促生了“哲学”这门学问。因此,方东美认为从原始神话到理性思考的发展“孕育”了哲学,即,哲学作为一门学问的产生缘于人类理性的发展。(参见方东美,第27页)不过,方东美的论断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哲学发生所依赖的“理性”非一般理性,而是作为“反思理性”的理性之“反思”的能力。因此,黑格尔说:“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所以哲学思维无论与一般思维如何相同,无论本质上与一般思维同是一个思维,但总是与活动于人类一切行为里的思维,与使人类的一切活动具有人性的思维有了区别。”(黑格尔,第38页)由此来看,哲学作为一门学问与上述三种智慧既相关联,又有不同。具体来讲,哲学作为一门学问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哲学是可学的,此相对于宗教而言。哲学奠基于“理性”基础上,而宗教奠基于“信仰”基础上。因此,“宗教以信为本,哲学以疑为本。”(《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361页)既然哲学建立在“理性”基础上,故哲学就是可学的,而不是如同宗教般是“可信”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性”还是“天”,尽管它们无比深奥、高远,但均是可以学习并掌握的。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其二,哲学是超越的,此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具体学科而言。哲学作为对于具体知识进行“反思”的学问,它所揭示的是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道”,而不是关于经验世界与心灵世界之“技”的层面的具体知识。也就是说,哲学之“道”不是通常所谓道,而是指天地万物存在与变化的基础与根源;其极至乃是作为“天地之始”的“无”与作为“万物之母”的“有”。如《道德经》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一章》)
基于这样两个特征,哲学在发展过程中渐渐积淀出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等若干个部分。不过,就其作用来看,在所有这些部分当中,本体论乃是其中的根本。熊十力说:“本体论,一名形而上学,即穷究宇宙实体之学。……唯本体论是万理之所从出,一切学术之归宿处,一切知识之根源。”(《熊十力全集》第5卷,第537页)也就是说,本体论作为对一切智慧之根源的探讨,乃“一切智智”,亦即是一切哲学问题的根源。因此,“哲学思想本不可以有限界言,然而本体论究是阐明万化根源,是一切智智(一切智中最上之智,复为一切智之所从出,故云一切智智。),与科学但为各部门的知识者自不可同日语。则谓哲学建本立极,只是本体论,要不为过。夫哲学所穷究的,即是本体”(《熊十力全集》第3卷,第14-15页)。可见,本体论之探讨乃基于“以本贯末”理念所进行的“培本固元”式的工作。也就是说,哲学之使命乃须“穷究”本体;若不穷究本体,自宇宙论言之,万物无本,万化无源;自人生论言之,人迷离颠倒,没有归宿;自知识论言之,知识没有了来源,也没有了方向。因此,“哲学的做法,最重要的是根源性,由根源性而确定性。根源性必须是越过了表象的对象才有可能,再由此而能论确定性”(林安梧,2011年,第256页)。由此来讲,本体论是不能否定的,否则不仅会消解所有哲学问题,而且会将哲学这门学问也一并消解,从而陷入否定真理的“戏论”。熊十力说:“若只认现象为实在,而悍然遮拨本体,则宇宙无原,人生无原,是以浅躁之衷,自绝于真理,余未知其可也。”(《熊十力全集》第6卷,第739-740页)
既然“本体论”如此重要,而本体论又是关于“本体”的理论,那么,何谓“本体”呢?所谓“本体”乃“根本的体”,即载体性的存在。比如,在中国汉代,京房认为,由纯阳爻和纯阴爻构成的乾坤本初卦体是“本体”。他说:“乾分三阳为长中少,至艮为少男。本体属阳,阳极则止,反生阴象。”(卢央,第473页)在宋明儒者,本体通常是指“知”和“行”的依据和归宿。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传习录·卷上》)到了现代,熊十力则认为,本体“是浑一的全体,是遍一切时及一切处,恒自充周圆满,都无亏欠的”(《熊十力全集》第3卷,第249页)。综上所述,作为载体性之存在的“本体”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本体是天地万物存在和变化之最终的根源和依据。其二,正因为本体是事物存在和变化的根源和依据,它同时也是事物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和最终的归宿。其三,与一切相对和欠缺相对照,本体是绝对的、圆满的。(《熊十力全集》第7卷,第14页)正因为如此,本体应具有周延的解释力,即对于所有哲学问题能够提供最终的依据性的解释。
二
正因为本体乃载体性的存在,故历史上多数哲学家都肯定并重视本体,并且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本体论。具体来讲,西方哲学史上出现了“存在”、“理念”、“实体”、“物质”、“精神”等众多形态,中国哲学史上则出现了“仁”、“理”、“心”、“良知”、“生命”等若干形态。在同时面对这些本体形态时,人们常会有无所适从之感。实际上,若以哲学的研究对象为视角,这些本体大致可归结为两类。按照休谟的理论,由事实之“是”无法推演出价值之“应该”,“事实”与“价值”二者是二分的,故世界无外乎由“事实”与“价值”两个部分组成。(参见休谟,第509-510页)基于此,哲学的对象可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事实”,一类是“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下,哲学才可称为在超越层面研究事实与价值的学问。(参见程志华,2011年,第1-6页)对此,方东美认为前者指“客观的世界”,后者指“人类生命精神”;前者对应于“理”,后者对应于“情”。(参见方东美,第35页)因此,哲学的功能亦可相应区分为“度理”和“衡情”两个方面。他说:“约而言之,哲学的能事尽在于此:(一)本极细密的求知方法穷诘有法天下之底蕴,使其质相,结构,关键,凡可理解者,一一了然于吾心;(二)依健全的精神领悟有情天下之情趣,使生命活动中所呈露的价值如美善爱等循序实现,底于完成。”(方东美,第34页)由此来看,基于对“事实”之“度理”可形成为一种本体形态,基于对“价值”之“衡情”也可形成为一种本体形态。对应地讲,前者可称为“事实本体”,后者可称为“价值本体”。以此来衡断,“存在”、“理念”、“实体”、“物质”、“精神”等可归为“事实本体”,而“仁”、“理”、“心”、“良知”、“生命”等则可归为“价值本体”。
所谓“事实本体”,是指对“事实”之超越性的研究所建构的本体形态。历史地看,这种本体形态源于古希腊。泰勒斯第一个提出了“什么是世界的本原”的问题,并认为“水”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因为水有滋养万物的作用,万物的种子亦都具有潮湿的本性。(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6页)之后,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都对宇宙的本原进行了探讨,分别提出万物的本原是“数”、“火”或“原子”等。(参见同上,第18页、第21页、第47页)不过,这些探讨显然都属于“经验模拟”,因为其所谓本原多停留在可感事物上,而没有达及超越的层面,
故还不是真正的“事实本体”。与之不同的是,后来的巴门尼德认为,“存在”是宇宙的本体,千变万化的事物只是“不存在”。在他看来,“存在”具有如下特性:其一,永恒性。即,“存在”是自生的而不是生成的,是不生不灭和无始无终的。其二,连续性。指“存在”是“连续的一”,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就是其体现。其三,完满性。杂多和变化都是不完满的,只有不动的“一”才是完满的,而“存在”就是这完满的“一”。(参见同上,第32-34页)相对照地看,巴门尼德的“存在”已超越了对可感事物的“经验模拟”,而是对“事实”之超越性探究所建构的本体形态,故已为真正的“事实本体”。
之后,“事实本体”作为一种传统在西方哲学史上流衍下来: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还是唯物论的“物质”、唯心论的“精神”,都延续了这种本体形态的特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精神”和“物质”两种形态。在黑格尔,“绝对精神”是万物最初的原因与内在的本质即本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它的外在表现。具体来讲,“绝对精神”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一,逻辑阶段,指“绝对精神”作为纯粹抽象的逻辑概念之超时空、超自然、超社会的自我发展。其二,自然阶段,指“绝对精神”“异化”为自己的对立面——自然界;自然界从低级到高级发展,最终出现了人类。其三,精神阶段,即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指“绝对精神”否定自然界的束缚而“回复”自身的发展。(参见黑格尔)费尔巴哈则认为,“物质”作为一切感性的有形事物的总和,是惟一的客观实在和永恒的实体。因此,“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即,“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他说:“思维和存在的真实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应为“主词”——引者),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存在的根据在它自身中。”(费尔巴哈,上卷,第115页)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精神”和“物质”有着上述地位上的根本区别,但它们都是源于对“事实”之超越探究所形成的本体。也就是说,“精神”作为本体并非源于对“价值”之超越探究,而是与“物质”作为本体一样,源于对“事实”之超越研究,故均属于“事实本体”的形态。
客观地讲,“事实本体”的建构有其重要意义,因为它能够对于“事实”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具备解释力。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以“事实本体”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孔德认为,形而上学以思辨的虚构代替了对世界的实证研究,这实际上乃是人类精神“不成熟”的产物。他主张,既然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和基础,故凡是不能被经验证实的都须排除于知识范围;既然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不能被经验所证实,故应该“拒斥形而上学”。(参见孔德,第29-35页)在此脉络之下,哲学界进而出现了“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呼唤。(参见哈贝马斯,第320页)归结起来看,形而上学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困境,源于“事实本体”之解释能力的局限,即它只能解释基于“事实本体”范畴的“事实”世界,而对此范畴之外的“价值”领域却无能为力。如前所述,世界是由“事实”与“价值”共同组成的,哲学的研究对象相应地亦为“事实”与“价值”两部分。由此来看,所谓“后形而上学时代”并不真正地意味着形而上学的终结,也不意味着本体论的终结,因为除了“事实本体”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本体形态——“价值本体”。那么,何谓“价值本体”呢?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价值本体”肇端于对生命意义的困惑和反思,它所关注的是人的存在本身,着力于对意义之本、价值之源的探究。质言之,所谓“价值本体”,是指基于对“价值”之超越性研究所建构的本体形态。在此意义下,就本体形态的特征来讲,如果说“事实本体”可以称为“客体”形态的话,那么,“价值本体”可以称为“主体”形态。
历史地看,“价值本体”这样一种本体形态成熟于中国哲学。例如,王阳明遥承孟子的“心性之学”,在对佛、道进行汲取的基础上,建构起“良知”本体论。在他看来,自然界的知识意义、道德意义和审美意义均来自于主体的赋予。其一,“良知”作为认识主体,可将自然界作为认识对象,从而获至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他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传习录·卷下》)其二,“良知”作为德性主体,可以赋予自然界以道德意义。他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同上)其三,“良知”作为审美主体,可以将自己与自然界融为一体,从而体验其中的情感愉悦,感受“人心与天地一体,故‘上下与天地同流’”(同上)的审美境界。基于这样三个方面,王阳明认为“良知”即是天地万物之本体。他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同上)很显然,王阳明的“良知”不是基于对“事实”之超越探究而建构的“事实本体”,而是基于对“价值”进行超越探究所建构的“价值本体”。
相较于王阳明所建构的“价值本体”来讲,牟宗三对于“价值本体”的建构更有自觉,因为他对于“价值本体”有明确的意识。他认为,“良知”本体包括三个“我”:一是“物自身的我”,是知体明觉之“真我”,由“智的直觉”以应之。二是“心理学意义的我”,是“现象我”,由“感性直觉”以应之。三是“统觉我”,即“认知我”,由“形式直觉”以应之。在这三个“我”当中,“认知我”既不是“物自身的我”之“真我”,也不是“现象我”之“假我”,而乃“真我”为了成就经验知识经过“自我坎陷”而形成。三个“我”虽各不相同,但最终都统一于“物自身”之“真我”:“真我”是“智的直觉”之自视之“我”,“现象我”是以“感性直觉”应对“真我”时所起现之“我”,“认知我”则来源于“真我”之“自我坎陷”。(参见牟宗三,2003年a,第216-222页)牟宗三认为,“现象”与“物自身”之“超越”的区分是康德哲学的重要命题,但从其对“物自身”的论述看,康德并没有把它“稳住”,因为“物自身”由“纯粹理性”是不可知的。(参见牟宗三,2003年b,第11页)之所以如此,在于康德将“物自身”限定为“事实性存在”;要解决康德的困境,须将“物自身”由“事实性存在”“转”为“价值性存在”。他说:“在我们身上,无限心与识心有一显明的对照,即执与不执之对照;我们即由于此对照而有一标准,以之去决定物自身是一个价值意味底概念,并能显明地决定我们的知性、感性(即识心之执)之所知定是现象,而不是那有价值意味的物自身,并能充分地决定这分别是超越的分别。”(同上,第12-13)由此自觉,牟宗三的“价值本体”建构比王阳明更进一步。
客观地讲,“价值本体”的建构确有其积极意义。一个方面,它对于“事实”之外的“价值”领域具备了解释力,从而弥补了“事实本体”的不足。另一个方面,它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开出了“认知我”,从而亦对“事实”领域具有一定解释力。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化解了实证主义的责难和“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呼唤。(参见程志华,2009年,第29-35)不过,“价值本体”亦有明显的理论限制,此亦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其一,“价值本体”表现出明显的“主体主义”倾向,即过分地凸显了主体的能动性。(参见林安梧,2011年,第295页)在西方哲学,康德认为人与上帝有着天壤之别,但“牟先生将康德哲学中原属于上帝之任务者,全收于人之主体心灵而处理之”(林安梧,1996年,第210页)。这样,人的能动性等同于上帝的能动性,“价值本体”等同于了“价值主体”。因此,这种理路被余英时冠以“良知的傲慢”而加以批评。在他看来,与以“独占”真理而自负的科学主义者的“知性的傲慢”相类,道德主义者亦以独得“道体”而自负,将“良知”置于世界的巅峰,从而表现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良知的傲慢”。(参见《余英时文集》第5卷,第39页)其二,“价值本体”只是完成了“形而上的保存”,而缺乏“实践的开启”。(参见林安梧,1999年,第18页)无论是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还是牟宗三的“良知”本体,其意义之高远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恰是这种高远的境界使得它忽视了整个生活世界,也忽视了社会历史总体,因而与人间社会相隔绝。而且,尽管为了理论上的周延,牟宗三主张由“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知性,但“开出说”只是一种理论的诠释,而不是真正的“实践的开启”。总之,“价值本体”的建构只具有形而上的理论意义,并不具有真正的实践意义。
三
既然如此,探求新的本体形态便摆在了哲学界的面前。在此方面,林安梧提出从“牟宗三而熊十力”之发展可能的主张。所谓“由牟宗三而熊十力”,实质是“上遂于道,重开生源”。(参见林安梧,1993年,第373页)即,由牟宗三的本体形态回到熊十力的本体形态。质言之,此乃通过对熊十力哲学的诠释而建构一种新的本体形态。那么,熊十力的本体形态是什么呢?在熊十力看来,若依着佛教之“缘起说”等理论,“境”和“识”均不具有实在性。他说:“一切物没有不是互相为缘而现起的。所以,一切物都是没有自体的。换句话说,所谓一切物,实际上只是毕竟空、无所有的。”(《熊十力全集》第3卷,第51页)不过,并不能因“缘起说”而否认宇宙本体之存在;否则,不仅宇宙没有了根据,人生也会失去价值方向。关于何为宇宙之本体,熊十力依着其“体用不二” 3的宗旨,认为本体之根本属性有“虚寂”而“生化”两面,而同时具备这两面属性的只有“本心”,因此“本心”即是本体。不过,“本心”不是指与物相对的“妄执之心”,而是指超越的、“绝待”的“本体之心”。当然,也不能将“本心”理解为一形而上的“敻然之体”,它乃是一“场域之始源”,是即“众沤”的“大海水”之体。也就是说,“本心”不是“一元”的主体本体,而是包含“事实”与“价值”于一身的本体,即作为客体、主体之总体的本体。显而易见,熊十力不是一种“主体性思维”,而是超越了主客对立展开的“整体性思维”。正因为如此,“尽管熊十力仍然极为强调‘本心’的重要性,但毕竟他所重视的是‘乾元性海’”(林安梧,2003年,第272页)。
进而,为了避免人们对“本心”的误解,从而“滑落”为“妄执之心”;也为了凸显本体之“绝待”,从而超越对客体、主体之一端的偏执,熊十力将“本心”亦名为“乾元”。在他看来,“乾元”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乾不即是元”(《熊十力全集》第7卷,第523页)。即,“乾”作为本体之势用,“元”作为万有之本体,二者不可绝对等同。其二,“乾必有元”(同上)。即,就“乾”来讲,宇宙万有不是从空无幻化而来,它必有“根源”即本体作为依据。其三,“元者,乾之所由成”(同上)。即,“元”作为万有的本体,并非存在于万有之外,而乃存在于万有之中。基于这样三个方面,熊十力界定了“乾元”本体的特征:其一,“实体内部含藏复杂性”(同上,第567页);其二,“实体是万物的内在根源”(同上)。前一个特征指本体乃“乾元性海”,一切大用流行皆自此流出;后一个特征指由大用流行可证明“乾元”之真实无妄。换言之,前者之含义在于“即体成用”,即“不易”之本体因其含藏“复杂性”而发为大用流行;后者之含义在于“即用识体”,即由大用流行之中即可识得本体。在熊十力看来,这两个特征乃关于“乾元”本体之“至论”,其义乃哲学之“洪宗”,因为它们使得本体“周流完备”。(《熊十力全集》第3卷,第922页)
显而易见,如此解释的熊十力的“乾元”本体不是一元的“价值本体”,亦不是一元的“事实本体”。依着林安梧的理解,这样一种本体可以“存有”来界定。所谓“存有”,不是指作为一切存在之所以可能的最高的、超越的普遍性概念,而是天、地、人交与参赞所构成的总体根源。或者说,
“存有”不是被认识的概念或认识的结果,而是指人参与其中的“活生生的实存而有”的世界。《道德经》曰:“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林安梧对此解释道:人居于天地之间,是具体的、实存的,此乃“人法地”;人生存于天地之间是朝向一高明而普遍的理想的,此乃“地法天”;这高明而普遍的理想又得回溯到总体本源,此即“天法道”;这总体本源有一自生、自长、自在的调节性生长机能,此乃“道法自然”。就这样一个过程来看,“存有”并非认识论意义下的“本体”,而是人参与进去、相互融通状态下的总体根源。(参见林安梧2009年,第114-115页)林安梧说:“‘存有’并不是一夐然绝待、离心自在的东西,而是‘天地人我万有一切交融’的状态。就此源出状态而说为‘存有的根源’,相当于华夏文化传统所说的‘道’。‘道’是‘人参赞于天地万物而成的一个根源性的总体’,它是具有生发功能的总体之根源。”(林安梧,2002年,第16页)这里,“存有”所凸显的乃是“根源性”的“总体”。
因此,此“存有”不同于西方哲学认识论意义下的“存有”。西方哲学的“存有”作为“事实本体”,它片面强调“事实”的一面,从而边缘化了“价值”的一面。此为其一。其二,此“存有”亦不同于王阳明和牟宗三的“良知”之中国哲学的“价值本体”;“价值本体”片面强调“价值”的一面,表现出“主体主义”倾向和实践意义的缺乏,从而边缘化了“事实”的一面。与此等均不同,此“存有”相当于中国哲学之道家哲学的“道”。“道”不仅涵盖宇宙,也包括人生;不仅包括“事实”,亦包括“价值”。质言之,“道”乃是“人参赞天地万物”所成的“根源性总体”。因此,“道”作为本体,既不同于“事实本体”,亦不同于“价值本体”。或者说,它既同于“事实本体”,又同于“价值本体”,因为它包含二者于自身。质言之,“道”是对于“事实本体”和“价值本体”的结合与超越。在此意义下,如果说“事实本体”属“客体”形态,“价值本体”属“主体”形态,那么“道”则属“客体”和“主体”之“总体之体”的“道体”形态。或者说,“道体”乃是对这“总体之体”之超越性的研究所建构的本体形态。也就是说,“道体”乃是对“客体”形态和“主体”形态的超越和发展。此即是“客体”、“主体”和“道体”三者的关系。因此,林安梧说:“由牟先生的‘一心开二门’再返回熊先生的‘体用合一’的格局,进而再返回王船山的‘乾坤并建’的格局,或将可以恰当而如实的处理道体、主体及客体这三端的结构性问题,而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方始有一崭新的可能。”(林安梧,1996年《序言》,第9页)
基于“道体”这样一种本体形态,林安梧进而展开讨论了其“存有三态论”,以建立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从而将“道体”的解释力予以具体化。所谓“存有三态论”,指“‘道’开显之三态,所成之论也”。(参见林安梧,2009年,第116页)首先,“道体”是超乎一切话语系统之上、不可言说的一切存在的根源。即,“道体”原初处于“境识俱泯”的状态,为一空无寂静的境域,即“无名天地之始”(参见《道德经·一章》)。此是意识前的、“寂然不动”的状态,是形而上之“道”的状态。此为第一层状态——“存有的根源”。其次,“道体”不能永远处于不可说的状态,它必经由“可道”而“开显”。所谓“道可道”,即指由不可说而可说,即“道”必然“开显”为“象”,此为“不生之生”;此“不生之生”为“境识俱起”而未有分别的状态,即“感而遂通”的状态。此即第二层状态——“存有的开显”。再次,“道体”经由“可道”开启后当落在“名”上说,否则不足以为说。即,“象”必经由“可名”而走向“名以定形”(王弼注,第14页),经由“可名”之彰显而为“有名”;“有名”是指经由命名即对象化活动使对象成为决定了的“定象”,此为“有名万物之母”(参见《道德经·一章》)。此即第三层状态——“存有的执定”。(参见林安梧,2011年,第297-298页)在林安梧,“存有”不仅是依着上述“顺向”的基本框架来展开,亦可“逆向”地对“存有三态”反过来解释。即,从“存有的执定”开始,把“执”打开、把“定”解开,回溯到“存有的开显”,最终再上溯、回返到“存有的根源”。(参见林安梧,2001年,第174-175页)这样一个双向过程乃是“存有三态论”之完整的基本框架。
由这样一种基本框架不难看出,“道体”作为一种本体形态,不仅克服了“事实本体”之限制,因为它具有对“价值”领域的解释力;更重要的是它亦化解了“价值本体”的缺陷,从而具有更广的解释力。其一,“道体”克服了“主体主义”倾向,因为“道体”不是“主体”,而是作为“客体”与“主体”之结合的总体根源。不过,它并未否定主体的能动性。在“存有三态”当中,“存有”的开显乃缘于“人”这个独特要素的存在。即,因为人具有“参赞”的能力,“存有”即“道”才可能“开显”。林安梧说:“当我们说‘道’的时候,是天地万物以及人通而为一的,不过人跟万有所不同的是人具有灵性,具有参赞的能力,就人具有参赞的能力,这时候才会有存有的开显,道的开显的问题。”(林安梧,2011年,第296页)其二,“道体”不仅完成了“形而上的保存”,而亦具有“实践的开启”。就“形而上的保存”来看,“道体”的建构和由此而展开的“存有三态论”,毋庸置疑乃是基于“以本贯末”理念而进行的“培本固元”工作。不过,“道体”作为万有的本体,不是超越的、“绝待”的他者,而是天、地、人交与参赞所形成的总体根源。因此,“道体”不仅重视整个生活世界,也重视社会历史总体。就“实践的开启”来看,“道体”作为天地万物的内在根源,它内在于大用流行之中,故它可为“实践的开启”直接提供支持。具体来讲,它强调的不是由儒学在理论上去“开出”民主与科学,而是在民主化与科学化的过程中,儒学如何扮演一个“调节者”、“参与者”的角色。(参见林安梧,1999年,第26页)如此来看,“道体”的实践意义已凸显无疑。
四
综上所述,哲学作为在超越层面研究事实与价值的学问,本体论是其核心内容。总的看,本体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一,基于对“事实”之超越性的研究所建构的“事实本体”,它的特征在于凸显“事实”,故可称为“客体”本体。“客体”本体有其价值和意义,但亦有明显的局限性,即它边缘化了“价值”的方面。其二,基于对“价值”之超越性的探讨所建构的“价值本体”,它的特征在于凸显“价值”,故可称为“主体”本体。“主体”本体对于克服“客体”本体的局限性有其贡献,但它亦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即具有“主体主义”倾向和实践意义的不足,从而边缘化了“事实”的方面。其三,基于将“事实”和“价值”融为一体的“总体之体”之超越性研究所建构的“道体”。作为一种本体形态,“道体”融合“客体”和“主体”二者于一身,避免了将二者偏执一端的局限性。即,它不仅克服了“事实本体”的局限性,亦克服了“价值本体”的局限性。就中西哲学之总体情况来看,传统西方哲学所重者大致为第一种本体形态,即“客体”本体;传统中国哲学所重者大概为第二种本体,即“主体”本体。对照地讲,第三种本体即“道体”形态,既然它是对“客体”本体和“主体”本体的结合与超越,故它可能是代表未来整个哲学发展方向的一种本体形态。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意识。也许,沿此方面进行深耕易耨,“上遂于道,重开生源”的愿望便可实现。
参考文献
《熊十力全集》,2001年,湖北教育出版社。
古籍:《圣经》、《说文解字》、《太平御览》、《史记》、《孟子》、《道德经》、《传习录》。
方东美,1937年:《科学哲学与人生》,商务印书馆。
黑格尔,1980年:《小逻辑》,贺麟 译,商务印书馆。
《蔡元培全集》,1997年,浙江教育出版社。
林安梧,1993年:《存有·意识与实践:熊十力体用哲学之诠释与重建》,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6年:《当代新儒家哲学史论》,台湾明文书局。
1999年:《解开“道的错置”——兼及于“良知的自我坎陷”的一些思考》,载《孔子研究》第1期。
2001年:《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台湾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科技、人文与“存有三态”论纲》,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
2003年,《从牟宗三到熊十力再上溯王船山的哲学可能——后新儒学的思考向度》,《玄圃论学续集——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9年:《关于<老子道德经>中的“道生一、二、三、万物”问题之探讨》,载《湖北社会科学》第9期。
2011年:《儒学革命: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商务印书馆。
卢央,2004年:《京氏易传解读》,九州出版社。
休谟,1980年:《人性论》,关文运 译,郑之骧 校,商务印书馆。
程志华,2009年:《道德的形上学与“后形而上学时代”》,载《哲学研究》第11期。
2011年:《哲学概念三解》,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1981年,商务印书馆。
费尔巴哈,1984年:《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荣震华、王太庆、刘磊 译,商务印书馆。
孔德,1996年:《论实证精神》,黄建华 译,商务印书馆。
哈贝马斯,2004年:《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牟宗三,2003年a:《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牟宗三先生全集》(20),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b:《现象与物自身》,《牟宗三先生全集》(21),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余英时文集》,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弼注,1996年:《老子道德经(外一种)》,上海书店。
Object·Subject and Tao
——on the forms of noumenon
Cheng Zhi-hu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Hebei University, Hebei Baoding, 071002)
Abstract: "Noumenon" is the core concept of philosophy, which is often a controversial concept. In fact, noumenon generally comes down to three different forms: first, "Object" form as the "Fact Noumenon"; second, "Subject" form as the "Value noumenon"; third, "Tao" form as the form beyond "Object" and "Subject". Generally speaking,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emphasizes the "Object" form whil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emphasizes "Subject" 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uman philosophy, "Tao" form may be a reasonable noumenon form.
Keywords: Philosophy; Noumenon; Object; Subject; Tao
1 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牟门弟子研究》(编号HB09BZX001)阶段性成果,并获得“河北省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2 作者简介:程志华(1965-),男,哲学博士,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儒学、中西比较哲学。
3 熊十力说:“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积测日久,忽然悟得体用不二。……余之学自此有主而不可移矣。”《熊十力全集》第7卷,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