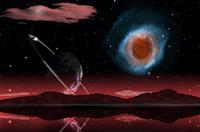法国哲学始终关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对重大政治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是法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福柯要求发挥我们的政治想象力,关注特殊的、局部的政治问题,做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福柯意识到人类主体既可以由历史和经济学在生产关系以及由语言学和语义学在意义关系中得到把握,也同样可以由谱系学在极其复杂的各种权力关系中得到把握。鉴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局限于探讨宏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忽视了边缘的、局部的、微观的社会政治问题,福柯指责马克思主义缺乏政治想象力。
纵观其学术生涯,福柯热衷于研究被传统学界所忽视甚至轻视的但在他看来极其重要的“边缘”问题(癫狂、犯罪、性)。这些边缘问题都渗透着重要的政治意蕴,需要发挥政治想象力才能加以深入研究。在福柯看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固守其意识形态立场,而专注于研究国家、阶级、政党等宏大的政治范畴,忽视了社会政治生活状况的特殊性、历史性和相对性,从而束缚了人们的政治视野,造成了现代政治想象力的贫乏。
一 人是经验的动物
福柯的政治想象力聚焦于死亡、癫狂、犯罪、性这样一些“界限-经验”,因为“人是经验的动物”,而特殊的、具体的、看似细小但重要的“界限-经验”却能使福柯摆脱绝对的主体观和宏大的政治叙事。福柯既不把“经验”看做感觉经验,也反对把经验看做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把“经验”理解成“文化中的知识领域、规范性(normativité)形态与主体性形式之间的相关性(corrélation)”①。这样的经验也就是科学理论、强制性实践和主体性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在西方社会具有其特殊的历史形式。于是,福柯相继研究了癫狂作为经验的历史、犯罪作为经验的历史、性作为经验的历史。可以说,福柯毕生都在探讨人的具体经验,探讨人之如何成为主体的历史;因为无论是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强制实践的层面上,抑或在人成为关切自身的主体的伦理层面上,人都是历史境遇中的经验主体。认识主体与被认识客体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经验过程中被构建起来的。显然,空洞的、说教的、抽象的宏大理论思考一般不会关注这样的经验主体。传统政治哲学不是满足于阐发宏大政治范畴的要义,就是想方设法提出并解决原本复杂但被简单化的普遍的政治问题。长期以来,围绕棘手的政治问题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基于不同的阶级和政党立场,学者们卷入无休止的、无谓的争论也就不足为奇了。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发挥政治想象力,政治思维极其刻板、短视、狭隘,政治活动极其软弱、无效、无益。福柯以为改变这种混乱局面的有效方法,就是脚踏实地,立足当下社会政治生活,聚焦局部问题,凸显权力运作和实施的机制。
尼采、巴塔耶、布朗肖、克洛索斯基(Klossowski)因设法通过经验达到尽可能接近生活之不可能性的、处于边界的生活内涵,从而使福柯摆脱了当时法国大学哲学教育盛行的、旨在把握整个经验可能性领域的黑格尔主义和现象学。按照福柯的说法,法国马克思主义渗透着现象学和人道主义,并以主体主义基调把异化理论看做了能把马克思的经济和政治分析转变成哲学术语的理论基础。而阿尔都塞则表明了马克思的分析本身并未表明有关人性、主体、异化的人的想法。为此,福柯的政治想象力就是要像尼采、巴塔耶、布朗肖那样聚焦于“界限-经验”,像他们和阿尔都塞那样从事去主体的事业,把主体从其自身中“撕裂”开来,使得主体不再是其所是,完全不同于其自身,是其自身的否认和与其自身的分离。让主体处于它自身的不可理解性的界限。福柯要在具体的特殊的经验中来质疑“主体”范畴及其首要性和原创功能,造成主体的摧毁或分裂、爆炸或剧变成完全“有别”的某物。“人是经验的动物,人无限地处在一个过程之中,这个过程通过确定对象领域而同时改变人、扭曲人、改造人并把人变形为主体。”②传统哲学中先验的、普遍的、奠基性的主体观占据主导地位,而福柯“非常怀疑和敌视这个主体观”③。福柯坚持,这样的特殊经验观和特殊主体观反映在政治思考中就是倡导微观权力分析。
在强制性实践中,主体就像客体那样被构建,主体双重含义得以彰显出来:施动者和受动者。要理解那种既把癫狂构建为客体又把主体构建为能理解癫狂者的经验,就必须把这种经验与作为特殊的规范化社会的诞生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这种特殊的规范化社会的诞生相关于禁闭实践,相关于与都市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确定的经济和社会境遇,相关于与经济和国家的需要相抵触的波动的和分散的人口等。主体在“界限-经验”中发生分裂,知识的阐发导致主体自身发生变形。在福柯看来,在西方社会中,人们在认识确定的、客观的一组事物时又在确定条件下把自身构建为主体。例如,西方人在被构建为理性主体时认识癫狂,在被构建为劳动主体时认识经济学,在被构建为犯罪主体时认识法律等④。在界限-经验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同时构成。这也是尼采、康吉莱姆和福柯等人共有的观点。福柯设法表明人们如何把自己的某些界限-经验(癫狂、死亡、犯罪)归结为认识对象。
“微观权力生物学”所说的政治想象力首先体现为要不同寻常地对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生活进行政治思考,进行别样的政治思考,而不是对现成秩序和理论做合法化证明,不是对民众的言行进行指手画脚。福柯不同时期在瑞典、波兰、突尼斯先后经历了当地民众的严重不满甚至暴动,这主要是因为国家或其他机构和压抑团体对当地日常生活实施了一种恒久的压抑。实际上,福柯当时之所以离开法国去这些国家谋职,也是因为感到当时的法国日程生活太过压抑。看来,压抑无处不在。这种令人生厌的、难以忍受的压抑来自于权力。福柯反对依据一种本质(压抑、法律、经济)来理解权力,而是要询问权力如何实施。不仅有国家权力,还有通过极其不同的渠道、形式和机构而在社会机体内实施的权力。无论在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往关系中,还是在恋爱的、制度的或经济的关系中,一个人总是想方设法操控另一个人的行为,这就是权力无处不在的明证。于是,人们开始质疑“辖治”的方式。当然,在福柯看来,权力不仅不能说明一切,而且权力本身是必须被说明的。
权力不再神圣,权力不再至高无上。福柯反对本质主义的权力观,而主张对权力做非本质主义的分析,研究权力机制的运作,分析权力关系的实施方式,探讨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强调权力不只起消极压抑作用,还具积极生产作用。福柯质疑权力的内在合理性,抗拒权力机制对个体施加的支配和控制。权力的机制、程序、技术和效果,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许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典型的压抑形式。在福柯看来,启蒙的允诺,通过理性的运用获得自由这一允诺,已经在大写理性本身的领域内被推翻了,与其所追求的自由渐行渐远了。
发挥政治想象力,也就是弘扬自由主义精神,驱除笼罩在国家上面的神圣光环,要剥夺人们通常赋予国家权力的优先性、基础性和根本性。因为西方社会经历了三种国家治理的形式:产生于封建型领土权的司法国家,产生于边疆型领土权的行政国家,以及依赖于人口和经济知识的辖治国家。权力不再神圣,国家的首要性同样受到质疑。现代国家权力至少奠基于其他权力形式之上,正是其他权力形式才使得国家权力存在的。“我们如何能说存在于两性之间、成人与儿童之间、家庭中、办公室中、病人与健康人之间、正常人与非正常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派生于国家权力的呢?如果人们想改变国家权力,那就必须改变在社会中运作的各种权力关系”⑤。具体的、多重的、发散的、自主的社会-民间权力是抽象的、单一的和集权的国家权力所无可替代的。不仅如此,福柯还揭示了所有现代国家的两个深层特征: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去屠杀民众和控制个体。
福柯之所以选择癫狂、犯罪和性这些人类边缘经验,不仅因为他对它们有着浓厚兴趣和较深刻的理解,而且更因为他可从中把握癫狂与理性、非法与合法、不正常与正常之间关系的演变史和文化意蕴,他可以从中探知主体是如何与自身相分离和撕裂的。人是经验的动物,思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政治想象力当然得关注这些人类具体的、历史的经验。
虽然都反对工具理性,反对极权主义,逃避“文明”,但福柯的政治想象力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们的政治想象力。按照福柯的说法,这种差异取决于他们各自对马克思的“人产生人”这个命题的不同解释。法兰克福学派把“人对人的生产”基本上理解为:把人从相关于合理性形式的压抑体系中或相关于阶级社会的剥削压抑中解放出来,而在福柯看来,“人对人的生产是一个摧毁我们所是、创造完全不同事物、全新事物的问题”⑥。鉴于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恢复我们“丧失的”身份,解放我们被束缚的本性,揭示我们最深层的真相,而福柯则必须要造就尚未存在而且我们不知其将如何存在和存在为什么的人,必须造就出并不与自身相等同的人。前者是恢复已有者,而后者是创造未有者;在此意义上,福柯的政治想象力要比法兰克福学派丰富得多,创新得多,也困难得多。
福柯关注局部问题、特殊问题,是否意味着福柯不关心整体问题、普遍问题?福柯是否就不想改变世界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二 特殊知识分子的政治想象力
知识分子因其地位和言论而政治化(politisation)了,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权力制度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要与那些既把他们当做对象又当做工具的权力形式作斗争。于是,理论就是实践⑦。从事这种实践的知识分子只能是特殊知识分子。这是因为民众已不再需要知识分子来获取知识和表达自己的诉求。伏尔泰式的、萨特式的作为社会良心和代言的普遍知识分子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特殊知识分子的政治想象力不仅要不断改变自己的思想,从事别样思考,而且还要改变世界。但关注特殊经验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社会民众的代言人,并不是作为立法者和预言者的普遍知识分子,而是作为实践者的特殊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不是告诉别人必须做什么。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呢?请记住知识分子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已设法阐述的所有预言、承诺、指令和计划。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不在于塑造其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即在他或她自己的领域内从事分析,重新询问证据和假定,改变行动与思考的习惯、手段,驱逐平庸的信仰,对规则和制度进行新的评估……这是一件参与政治意志构成的事情,知识分子被要求在这件事情中履行作为公民的作用。”⑧
作为公民,尤其作为二战以后的法国公民,福柯与当时许多年轻知识分子一样要急于摆脱曾遭受纳粹主义蹂躏、后在戴高乐将军领导下摆脱了纳粹主义的旧世界,而尽快去创造一个截然不同于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新社会。显然,倡导连续可理解性的黑格尔主义不能满足这个要求,而坚持主体具有首要性和根本价值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更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唯有尼采的间断性想法和巴塔耶的“界限-经验”才能引导福柯去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在福柯看来,尽管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主义和存在主义一样也对哲学思想进行连续主义读解,但福柯当时相信通达新世界的理智之路似乎就是共产主义。福柯对尼采或巴塔耶的兴趣并不意味着他远离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福柯当时成了一名“尼采式的共产党”:因此,正是在对马克思所知不多,要拒斥黑格尔主义,对存在主义局限性感到不满的情况下,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福柯在1950年决定加入法共⑨。两年之后,福柯在得知了所谓犹太医生行刺斯大林事件的真相后,在信仰与事实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福柯断然选择了事实,福柯对苏联式共产主义信仰感到幻灭,福柯就脱离了法共,与法共保持距离。政治说教苍白无力,党派争论没完没了,而政治问题依然如故。福柯拒绝睁眼说瞎话,摒弃冷冰冰的无谓的争论。福柯亲身经历了1968年3月突尼斯爆发的学生运动,这次真实的政治经历真正改变了福柯。因为为了反抗资本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突尼斯学生义无反顾参加斗争,置生死于度外。在这场学生运动中,身体介入是首要的,而理论参照是次要的。福柯由此坚信,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对激发斗争这一目标来说不可或缺,而理论的精确性和科学性却完全是次要的问题,理论能否指导行动这一点也成了问题。福柯厌倦并远离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争论、大咒骂、内讧和结派,怀疑空洞的政治理论的适用性,转而关注特殊和局部的政治问题,亲身组织或参加一系列政治行动,用具体的和明确的言词在确定的境遇中提出种种自特殊到一般的问题。
作为特殊知识分子,福柯的政治想象力始终聚焦于局部的特殊的经验问题,而不相信西方社会所能给出的主要话语,
不相信知识分子能指向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关键问题。福柯以为,只有走进经验生活,与非知识分子一起工作、合作,才能提出和探讨局部的经验问题:精神病患者说什么?精神病医院的生活如何?护士的工作是什么?病人如何反应?等等。再从局部化问题来提出一般问题。比如,为何以“理性”的名义,某人的权力能在他人上面确立起来呢?社会如何确立起自己与癫狂的关系?社会以何种方式被确认为个人化的合理性?为何社会把权力赋予给理性?合法如何区别于非法?这些就是很普遍的问题,旨在探究社会的运作和历史⑩。问题是否普遍,这并不是政党的过滤器就能说了算的。虽然福柯始终分析非常确切和局部的现象:如戒律体系在18世纪欧洲的形成,但福柯反对我们由此得出结论:福柯认为西方文明在所有方面都是一个“戒律文明”,戒律体系是由一个团体适用于另一个团体的。福柯的权力分析有着明确的时空定位,在专制君主制和封建制社会中,不可能在个体上面实施像18世纪那样塑成人格的戒律权力。福柯费力地想充分说明为何戒律体系产生于确定的时期、确定的国家,符合确定的需要。而传统政治思想笼统地围绕极权制和民主制的区分展开的讨论却不足以说明权力机制的特殊性。宏观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也看不到权力机制的历史相对独立于发展起来的经济过程。福柯敏锐地发现,由民主制(尤其是19世纪成熟的自由主义)展开的极其强制的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确定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自由”的抗衡力。
通过思考牵涉到日常生活的癫狂、犯罪和性等复杂的和困难的经验问题,福柯要详述知识的构建与权力的实施之间的关系。知识的运作、生产和积累不一定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人类解放的重要保障之一,因为重大的知识体系的构成也具有屈从和规则的效果和功能。“言论权利和政治想象力必须转向这些问题”(11),转向特殊的经验问题。由于福柯确信癫狂与理性、生与死、非法与合法、性常态与变态等日常问题都是深深触及我们同时代人生活、情感和焦虑的根本性问题,因此福柯并不想研究国家与公民或者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游戏,而是热衷于研究极其有限的、极其谦卑的、在哲学中并无高贵地位的权力游戏:围绕癫狂、医学、疾病、病体、刑罚和监狱的权力游戏。通过考察这些权力游戏、抵抗和斗争,福柯发现当代许多反抗、抵制和斗争都旨在实现权力实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漠视政治体制或经济制度或社会结构的,它们既不涉及经济剥削,也无关于政治不平等,并不具有与传统政治或革命运动相同的目标。如人们批评医疗机构在身体上、在病人的痛苦上、在其生死上施加一种不受控制的权力。当代许多抵抗和斗争还具有直接性,这些斗争指责所有直接施加在个体上的一切权力,这些直接的斗争也并不指望在未来某个时刻(革命、解放、阶级的消失、国家的消亡)能解决种种问题。没有暴风骤雨式的革命了,而只有卑微的、平庸的通常细小的抵抗、骚动和斗争。这些斗争“绝对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了,不是全国、全民、全阶级的全面的和联合的斗争,不是彻底推翻现有权力、毁灭其原则的斗争,不是确保总体解放的斗争,不是要求所有其他斗争都服从于它的绝对迫切的斗争”(12)。特殊知识分子参加的斗争,既非针对政治司法权力的政治斗争,也非针对经济权力的经济斗争,也非针对种族统治权力的种族斗争,而是针对牧师权力(pouvoir pastoral)的特殊斗争。福柯在特殊的局部的经验中发现了牧师权力。牧师权力凭借灵修指导、灵魂关切等手段来辖治每个个体从降生到死亡的每个生存细节。“辖治”无所不在。
福柯谈论的“辖治”是广义上的,不仅仅是指国家及其代言人的统治,也包括那些通过规则、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大众传媒)组织人们日常生活的“辖治”。福柯所做的只是设法勾勒出某些机构以“理性”或“规范”的名义,通过把个体称为非正常者、癫狂等,最终把它们的权力施加在团体或个体之行为、存在、行动或讲话方式上去的方式(13)。可见,权力并非像某些传统政治思想所说的愈来愈官僚化和国家化,而是更加个体化了。
鉴于福柯始终关注特殊的、局部的经验问题,有学者就指责福柯不像政党那样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福柯的答复是这取决于他的政治选择,他的使命是探测问题的所在、揭示出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而不是规定问题的解决措施。也就是说,特殊知识分子要了解具体的问题,即使把握了具体问题也不能充当问题的解决者。因为福柯认为当今知识分子的使命并不是立法、提出解决措施或进行预言,而是像公民那样参与政治意愿,否则就会有助于在他看来必须加以批判的政党权力机制的运转了,就会落入政党布下的圈套:诱使知识分子提出问题的解决措施然后加以批判,或者另提问题的解决措施。福柯要探讨社会机体内的特殊问题,但不主张包括自己在内的个人来承担解决特殊问题的责任。
在福柯的政治想象中,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并不存在理论对立。因为传统政治理论所反复研究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理论对立并不富有成果。权力实施和权力关系的显现才是关键,而普遍、抽象的理论表述却是次要的。福柯不考虑国家作为权力持有者并在市民社会上施加其统治权的出场,在他看来市民社会本身并不是类似的权力过程的仓库。他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不想做说教家或预言家”(14)。因为在福柯看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道德上,民众的心智都已成熟了,民众已开始个体地和集体地做出行动的选择了。而福柯作为特殊知识分子所做的就是揭示某个统治体制的运作机制,以便那些被塞进某个权力关系之中的人们有可能通过反抗和抵制行动而逃脱权力关系。虽然福柯拒绝提供问题的解决措施,但他相信处于权力关系之中的个体,为抵制或逃避权力关系,有许多事情可做。由此观之,福柯的政治想象力并不倡导一种消极认命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而是基于绝对乐观主义的假定之上。
三 现代政治想象力贫乏的根源
福柯要求人们把政治想象力集中在癫狂、死亡、犯罪、性这样一些特殊的、局部的社会政治问题上,批判传统的宏观政治哲学思考,尤其把现代政治想象力贫乏的根源之一归咎于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福柯之所以对癫狂、精神病学、监狱和性等人类边缘的经验领域和“新的政治想象领域(nouvel imaginaire politique)”(15)感兴趣,就是为了要唤起新的政治想象力(imagination)。在福柯看来,鉴于在18和19世纪,从卢梭到洛克或到空想社会主义者,西方社会充满着社会-政治想象力的丰富成果,而20世纪的人们则不幸地生活在政治想象力极其贫乏的世界上。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代政治想象力的贫乏呢?福柯直言:局限于研究宏观政治哲学问题并阐发普遍的政治理论和原则,而轻视甚至忽视特殊的、局部的经验问题和细小的但复杂的权力关系机制,是导致现代政治想象力贫乏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国家哲学和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又对当代政治想象力的贫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福柯强调把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的重要性。马克思只是一位历史人物,是一个正确无误地解释了某些事情并作为历史事件的确凿的、无法否认的存在,而马克思主义则有所不同,大致具有“历史科学”、“预言科学”和“国家哲学”这样三种形态,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厚实的政党、国家基础。当今不少国家仍需要利用马克思主义才能作为国家而运作的理论工具。无论作为这三种形态的哪一种,马克思主义都不可避免地与整个权力关系内在相关,形成了权力关系的动力学(16)。摆脱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开始成形的国家哲学,就是要摆脱与实施着三重功能的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权力关系的动力学。
福柯充分肯定马克思在19世纪的欧洲国家所起的几乎决定性作用,甚至断言历史学中的马克思堪比物理学中的牛顿或爱因斯坦,但又认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的这个决定性作用只限于19世纪的欧洲。这就否定了19世纪的欧洲的马克思能具有超越时空的预言作用。福柯要削弱那些与预言特征相联系的权力关系,要削弱马克思主义作为权力样态所施加的影响,要削弱马克思主义作为政党的喉舌而标明的权力关系,以凸显癫狂、犯罪、性这些文化经验问题的政治意蕴。
福柯的政治想象力否认马克思与西方整个文化视域做了认识论决裂,从而拒绝拔高马克思思想及其革命内涵的重要性。基于人文科学考古学的探讨,基于对现代三大经验科学(经济学、生物学、语言学)的诞生、发展和衰变的梳理,福柯在《词与物》中把马克思归结为19世纪知识型内的一个插曲,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一般的话语规则属于一类在李嘉图时代成形的话语构成,马克思的经济学话语可以分享19世纪特有的科学话语之构成的标准。福柯反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圣经般欢呼,这种欢愉归功于马克思主义之诞生于19世纪却在20世纪仍有重大影响的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命运(17)。在福柯看来,一个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知识分子的最低职责就是,要凭着完全不受制于马克思的真实情感,去系统地检验马克思主义对于与马克思本人的话语相联系的权力所作的每一个表述。
福柯不能接受作为预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的预言几乎都是错的。如马克思在分析1851-1852年间政变后的形势时做出的帝国即将崩溃的预言,马克思就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和资产阶级独裁统治的终结方面所做的预言,马克思做出的国家行将消亡的预言,无不如此。而国家哲学往往用政党意志、集体意志取代了个体意志,从而忽视了斗争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偶然性。福柯批评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政治想象力的贫乏,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作为政党的喉舌仅仅关注阶级的划分以及参加斗争的阶级立场,而忽视了具体的、生动的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具有重要政治意蕴的历史事件和经验素材。权力机制、戒律体系并不仅仅存在于国家机器之中,像家庭、性生活、疯人、同性恋、男女关系等素来被认为是边缘的和次要的日常生活问题却在当代政治领域中占据着关键的地位。要改造社会,必须先改变这些新型的微型的政治关系。
福柯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主要分歧集中在对政治问题做微观的还是宏观的把握、对政治现象做历史的还是非历史的考察。福柯的政治想象力注重历史维度和经验层面,因而具有实证主义精神,开启了微观政治哲学思想维度。如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也乐于人们称他为实证主义者。
四 几点评论
对于福柯的政治想象力问题,笔者拟作以下几点评论。首先,在二战以后的世界社会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在意识形态铁幕笼罩的年代里,人们太多地关注国家、阶级、政党等宏大的政治范畴和普遍的政治问题,而轻视了人口、生命、健康及其相关的安全、财富和资源问题,甚至忽视了癫狂、犯罪、性等边缘问题,福柯所说的政治想象力贫乏这样的情况确确实实存在着,东西方两大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各党派之间的纷争不仅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变得尖锐和突出了。这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都是相同的情形。
其次,“要解放政治想象力,就必须摆脱国家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福柯这个观点有其合理之处。福柯去世以后,苏东发生剧变,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似乎验证了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所做出的理论分析。但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国家意识形态是否就必定束缚政治想象力呢?不一定。这取决于在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如何寻找适当的平衡点。当今,国家、阶级、政党的意蕴和功能发生了一定的甚至较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特殊经验问题进入了政治思考的视野,源自于日常生活的越来越丰富的政治词汇进入了人们的头脑。面对全球化、恐怖主义和金融危机等重大问题,世纪之交的政治想象力出乎寻常地丰富,有时甚至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藩篱和党派争端,这恐怕是福柯当时所没有想到的。
再次,对于政治想象力,笔者以为“恰当”与否是最重要的,而“丰富”与否倒是次要的。无论是国家层面上的权力机制,还是日常生活层面上的权力机制,政治想象力都必须恰如其分、一视同仁地地加以研究。因为在当今社会中所有权力机制都形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环环相扣,密密交织。谈论哪个权力机制重要,哪个权力机制次要,这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毫无意义。有此视野,宏观政治哲学思考与微观政治哲学思考就可以相辅相成,携手安顿既作为理性动物又作为经验动物的人。与其把福柯的微观生物权力思想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宏观政治思想的对立面,不如看做是对后者的一种理论反拨,一种把政治视野从云端拉回大地的有益尝试。
最后,拥有恰当的政治想象力,也就是具备了政治智慧。所谓的政治边缘问题与中心问题其实并不对立和冲突,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共同组成了当今社会政治生活的完整整体。福柯真切地看到了这种联系,在边缘问题被轻视甚至被忽视的情况下,福柯想要凸显边缘问题相对于中心问题所具有的基础作用。福柯曲折地展现了其独特的政治智慧。德里达在去世前不久就“新启蒙”发表的看法中就表现出了这样的政治智慧。德里达拒绝在美国霸权、中国崛起和阿拉伯-伊斯兰神权政治之间做出选择。既要继承和保存欧洲的启蒙遗产,又要充分意识到并悔恨过去的极权主义、种族大屠杀和殖民主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既批评美国霸权又不至于被指责为同情萨达姆伊斯兰政权,既批评以色列和美国的中东政策而不至于被指责为反犹太主义。既要反对全球化,又要承认全球性组织所起的积极作用(18)。显而易见,“恰如其分”并不就是折中和妥协,而更类似于辩证综合。笔者不能认同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和做法,即先是不加区分地把20世纪60年代那一大批法国哲学家统统贴上后现代主义者的标签,然后以偏概全概括出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征,最后硬是给这一大批所谓的“后现代哲学家”扣上所谓的“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帽子,加以简单批判、打发甚至摒弃。
注释:
①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2, l" Usage des Plaisirs, 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84, p. 10.
②④⑥⑧⑨⑩(11)(13)(14)(17)Michel Foucault, Remarks on 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ombadori, Semiotext (e), 1991, p. 124, pp. 70-71, pp. 121-122, pp. 11-12, p. 51, p. 152, pp. 158-159, p. 145, p. 172, p. 105.
③Michel Foucault, "une esthétique de l" existence", Dits et crits, IV, 1980-1988, 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 733.
⑤Michel Foucault, "La société disciplinaire en crise", Dits et crits, III, 1976-1979, 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 533.
⑦Michel Foucault, "Les intellectuels et le pouvoir", Dits et crits, II, 1970-1975, 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 308.
(12)Michel Foucault, "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 de la politique", Dits et crits, III, 1976-1979, 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 547.
(15)(16)Michel Foucault, "Méthodologie pour la connaissance du monde: comment se débarrasser du marxisme", Dits etcrits, III, 1976-1979, 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 599, p. 601.
(18)Jacques Derrida, "Je suis en guerre contre moi-mme", Le Monde, le 19 aot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