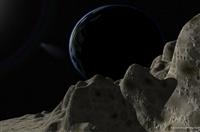当下,“宪政”一词成了学界比较敏感的话题。要使“宪政”问题在有价值的学术意义上科学地加以探讨,必须要对“宪政”概念作为汉语的专门术语其辞源学的意义加以认真考察,同时还要对“宪政”概念“能指”的社会现象做出正确的评估,否则,在学术上简单地抛弃“宪政”一词会引发更严重和复杂的理论问题与政策上的被动。
从法理上来看,要考察“宪政”概念所指向的社会现象,应当明确地区分两个学术命题:一是“宪政”在当下中国是否已经发生?二是已经发生的“宪政”未来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前者是指事实状态的“宪政”,后者指应然状态的“宪政”。
就事实状态的“宪政”来说,“宪政”的辞源学考证和相关历史文献的考察都可以明确地给出答案,即“宪政”在当下中国是已经发生的社会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与“宪法”一词从古汉语产生,后被日本借用,通过日本学界的演绎赋予了不同于古汉语的价值内涵,成为指称现代意义上的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又被传回中国,成为现代汉语所认可的法律术语的汉语词汇演变的历史[1]不同的是,“宪政”一词没有“出口转内销”的学术背景,从作为汉语词语被使用的最初开始,就具有非常明确的内涵。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宪政”概念作为汉语词语起源于梁启超的独特贡献。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定义“宪政”的学者。他在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期间写作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宪政(立宪君主国政体之省称)之始祖者,英国是也。英人于七百年前,已由专制之政体,渐变为立宪之政体。……以至今日非徒能不失旧物而已,又能使立宪政体益加进步,成完全无缺之宪政焉。”[2]梁启超首创“宪政”一词当时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在1901年6月7日《清议报》中发表的著名《立宪法议》一文中,他提到:“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因此,在梁启超的视野中,“宪政”想要获得的就是“有宪法的政治”。只要在政治生活中制定了宪法,并且按照宪法的规定来安排国家的政治生活,即实现了“宪政”状态。
按照梁启超的“宪政”标准,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已经有了“宪政”,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已经制定了四部宪法,其中1982年宪法作为现行宪法,虽然经过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修正,但目前仍然有效,故在“宪政”就是“有宪法的政治”这个辞源学意义上来考察,“宪政”在我国当下是已经存在的事实状态,而不是一些人心中的所谓“宪政梦”。
“宪政”概念所指向的社会现象作为已经存在的事实状态,在建国后领导人的一些重要讲话中也得到了充分肯定。刘少奇同志在1954年9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制定宪法是以事实做根据的。我们所根据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国人民已经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取得了彻底胜利的事实,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的事实,就是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的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在一步一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事实。
从这些事实出发,我们制定的宪法当然只能是人民民主的宪法。这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类型的宪法。
我们提出的宪法草案,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刘少奇同志上述讲话非常肯定地表述了1954年宪法的诞生是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就是说,新中国的“宪政”的客观基础是有了“1954年宪法”,新中国的“宪政”延续了中国近代以来“有宪法的政治”的宪政运动的历史。
2008年3月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受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吴邦国委员长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在工作报告中,吴邦国委员长明确使用了“宪政”一词,并充分肯定了“宪政”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的现实存在。吴邦国委员会指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宪法,成为我国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吴邦国委员长上述讲话也非常明确地肯定了“宪政”就是“有宪法的政治”这一历史事实,并且还对“宪法”与“宪政”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较好的描述,即现行宪法四次修改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宪法,作为“有宪法的政治”,中国当下的“宪政”也因为“宪法”内涵的丰富而变得更加有意义,“成为我国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
据上可知,从辞源学上来考察,作为“有宪法的政治”的“宪政”一词,从梁启超首创之后,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在政治生活的实践中一直是存在着的客观社会现象,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如果在学术上简单地否认或回避这一历史事实,那么,“宪政”一词就无法在科学的意义上继续探讨下去了。
当然,也要看到,虽然作为“有宪法的政治”的“宪政”在当下中国已经存在,但是,“宪政”本身也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宪政”是一种进行时,但是,“宪政”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又随时面向“未来”,具有“未来时”的要求,对此,又产生了学术上以及实践中对“宪政”发展目标的不同期待,确实存在着一个“宪政”发展的价值目标问题。
当下关于“宪政”问题的时文中,由于没有在学术上严格地区分事实状态的“宪政”与价值状态的“宪政”,导致了一些在学术上似乎严重对立的学术观点的出现,这种似乎不可调和的立场不仅不利于科学地探讨“宪政”概念的内涵与意义,也不利于我国今后“宪政”的健康发展,应当引起学界与政界的认真关注。“宪政”问题无小事,只有秉持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立场,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结合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才能在“宪政”发展的价值目标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迷失方向。为此,必须要在学术上认真对待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一是认为“宪政”的主要要素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忽视了“宪政”概念的历史发展,没有区分事实状态的“宪政”与作为价值目标予以追求的“宪政”。“宪政”概念在辞源学上非常清晰地指向“有宪法的政治”,如果连我国当下已经存在“宪政”的事实状态都予以否认的话,其实践的消极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那样会严重地削弱现行宪法的权威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甚至会演化为否定我国现行宪法存在的意义,继而严重威胁以现行宪法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正当性,在理论上会导致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确性的重新论证,有可能产生理论上的重大风险,严重影响中国式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当然,主张“宪政”要素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学术观点对我国“宪政”发展目标的担心也是应当重视的,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发展格局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对各种非社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思潮保持高度警惕,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宪政”之名将一些非社会主义性质的错误观点塞进“宪政”的价值内涵,并以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这一方面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敏锐性和坚定性是很有必要的。
二是要紧密结合我国现行宪法的实施来谈论中国“宪政”未来发展的价值目标和方向。在当下关于赞同“宪政”的学术观点中,离开宪法单独谈论“宪政”的倾向也很明显。作为“有宪法的政治”,我国的“宪政”是依托现行宪法的存在而存在的“宪政”状态,不能随意脱离“宪法”单独谈论“宪政”的意义。就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学术观点来说,如果要在规范和科学的学术意义上来探讨我国“宪政”的发展目标,应当将理论着力点放在“社会主义宪法”的完善和健全上。刘少奇同志在1954年9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的是1954年宪法“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类型的宪法”。因此,在学术上旗帜鲜明地讲“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社会主义宪政”一词在学术上能否精确地指向基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而存在的“有宪法的政治”,这个问题还需要认真探讨,也就是说,在宪法与宪政关系还没有从法理上非常清晰地给出解决方案的前提下,在学术上对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潮可能会利用“社会主义宪政”内涵的不确定性“做文章”的言行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除非执政党已经在“社会主义宪政”问题上产生了非常成熟的认识。“宪法”只是“宪政”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宪法”不等于“社会主义宪政”,这里的辩证逻辑在法理上也是非常清晰和有力量的。因此,当下,将“社会主义宪政”立足于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正式施行三十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所强调的“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这样的基本判断是,在学术上比较可靠,在政治上也比较稳妥。
总之,在“宪政”问题上要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既要对基于我国现行宪法建立起来的“宪政”事实表示充分肯定,同时也要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慎重应对各种形形色色非社会主义思潮利用“宪政”概念可能导致的混淆视听。要积极应对,敢于担当;不要消极避战,以偏概全。要以理服人,不要简单压制。要高屋建瓴,从大局出发,从长远着想;也要慎重应对,方寸不乱。通过“宪政”概念争议产生的学术问题可以发现,在我们大张旗鼓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对各种形形色色的非社会主义价值形态也要及时归纳总结,不断加以澄清,以达到正本清源的效果。
注:本文为莫纪宏教授授权的原稿。原作首发于《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标题为《“宪政”词源溯》,正稿较原稿有修改。
注释:
[1]中文的“宪法”一词很早就出现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左丘明编撰的《国语˙晋语九》:“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 公元604年,承袭隋唐政制的日本出台了《圣德太子宪法十七条》,虽然无法精确考证为何使用汉字“宪法”一词,但是,确实是日本借用汉字“宪法”的最早明证。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学者箕作麟祥在翻译法国法律时创造许多新词,其中1874年出版的《法国法律书:宪法行政法》明确将汉字“宪法”用来指称近现代意义上作为根本法的“宪法”。1882年,伊藤博文出使欧洲各国调查立宪政治时,宪法的名称在日本被正式确立下来。在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出台当年,中国出洋游历使臣傅云龙在《游历日本图经》中将《大日本帝国宪法》翻译到中国。1894年郑观应出版《盛世危言》使用“宪法”一词,要求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宪法”一词流行于1904年,当时许多外国宪法著作被翻译到中国。在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后,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宪法”一词成为中国正式使用的法律术语。
[2]梁启超:《梁启超法学文集》,范忠信编,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版,第2页。
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依宪治国”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