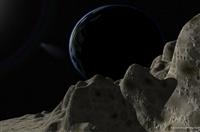1. 法律人的豪言壮语
进入中国政法大学之后,每个学生都会感受到话语的分量, 如:“一生一世法大人”—一个有关人和机构依附关系的隐喻;又如:“本校是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一个有关自己和同行关系的自我评价。中国政法大学本科学生的入学誓词是一个典型的拔高法律人形象的话语:
“当我步入神圣政法学府之时,谨庄严宣誓:
我自愿献身政法事业
……
挥法律之利剑 持正义之天平
除人间之邪恶 守政法之圣洁
积人文之底蕴 昌法治之文明”
在这里,法律代表着正义、法律人就是(或者应当是)正义使者,“利剑”、“天平”具有强烈的符号色彩,话语背后的权力跃然而出……。如果法律真是一柄利剑,那么,持剑武士和剑锋所指的人不会是同一人。然而,现实并不像演绎推理那么简单。
2. 法律人走麦城
2.1 中国政法大学知名校友录
(1)黄松有,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前教授、前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首位钱端生奖获得者。犯受贿罪,2010年获无期徒刑。
(2)许宗衡,双硕士(1996年,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硕士;1999年,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MBA), 深圳市前市长。犯受贿罪,2011年获死缓。
(3)曹文庄,药监局司长,2005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论文“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犯受贿罪,2007年获死缓。
(4)田长友,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破产庭法官,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犯受贿罪,2008年获刑6年。
(5)郭生贵,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函授学院毕业,犯受贿罪,2008年获死缓。
(6)杜保忠,商务部条法司,中国政法大学93级研究生,犯受贿罪,2008年获刑。
(7)麦崇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生,犯受贿罪,2003年获刑15年。
(8)田凤歧,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犯受贿罪,2003年获无期徒刑。
(9)李汉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2008年因受贿罪获刑。
(10)贾永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生,2001年因受贿、贪污获无期徒刑。
(11)宋晨光,中国政法大学在职研究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犯受贿罪,2012年获死缓。
(12)袁宝璟,中国政法大学85级学生,企业家,犯故意杀人罪,2005年获死刑。
在以上名单里,本应添加上王立军,他已经被提名为中国政法大学博导,只是在中国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会批准提名之前,他就走进了美国领事馆,又从那里走进了监狱。黄松有曾经是4-5所名牌法学院的博导,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界共同的审美观留下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
在以上“知名校友”名录里,所有的官员都是因同一错误——“受贿”——而丢失了“知名校友”的荣耀。与此同时,还有更多不那么知名的校友(如律师校友)陷入了贿赂食物链的中端或者低端。为什么法律人(特别是成功的法律人)会无师自通地走进“贿赂门”而成为“同门师兄”呢?
2.2 法律人通病的患者似乎不限于中国大陆。台湾大学是台湾的最高学府,也有自己的“杰出校友录”,以下一位是台大法律系的“杰出校友”:
陈水扁,1950年出生;1970年,以最高分考入台大法律系;1973年,以全台第一名通过律师资格考试;1974年,台大法律系毕业,全系成绩排名第一;2000年,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2012年11月1日,台湾“高等法院以贪污、受贿、洗钱罪判处合并执行18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5600万元。陈水扁所做的事情是,将机要费、机密费挪为私人支出;以不实犒赏诈领机要费、机密费;以私人发票诈领非机密费。此外,在龙潭购地案以及陈敏薰人事案中,这位杰出校友也犯了同一错误——“受贿”。
台湾还有一位“杰出”法律人:台北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刘伟杰——台湾理律律师事务所的法务专员。2003年,刘盗卖客户寄存的股票,获新台币30多亿元,用以购买钻石。其后携钻石逃离台湾,至今仍在追缉中。时任理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带领律师事务所度过危机的陈长文或有感于刘伟杰事件,而在2006年出版了专著“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
2. 3 那么,在太平洋彼岸——在台湾同行常常称为“法制先进国家”的美国——法律人又如何呢?2012年,在水门事件40年之际,曾任尼克松政府白宫总顾问的John Dean发表了题为“水门遗产”的报告,报告提到:1973年6月26日,John Dean在参议院作证,提交了一份参与水门事件和掩盖事实真相的人员名单,大部分人的名字旁边都有加上了“*”号。在回答参议员提问“为什么添加“*?”的时候,Dean说:
“……当我列出名单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糟糕,这么多律师卷进去了。’因此,我在每个律师的名字旁边添加了一个星号,包括Mitchell, Strachan, Ehrlichman, Dean, Mardian, O”“”“Brien, Parkinson, Colson, Bittman, and Kanlmabach.” Dean又补充说,带星号的名单还没有包括美国总统尼克松,以及当时已经声名狼藉的Gordon Liddy和数十名在水门事件中充当了某种角色的律师。为什么这么多法律人卷入了水门丑闻?Dean总结了四个原因:胆大妄为、能力不足、对客户愚忠和错认客户 (Arrogance, Incompetence, Unquestioning loyalty to the client and Confusion about the identity of the client) 。
3. 法律人学坏的原因浅探
试图罗列所有的原因,建立因果关系,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大致把一些经验事实作为原因,并对原因进行大致的分类。
3. 1 角色冲淡对错,“关系”变乱角色
3.1.1 按照经典看法,律师只遵循角色界定的伦理规则(role differentiated ethics):律师只从客户关系的立场考虑道德问题,不必关心超越这一关系的其他道德问题。针对这一看法的批评意见是:其一,在律师与客户的关系中,律师的行为充其量是系统内的道德中立,可是,在系统之外,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律师的行为常常是是不道德的,律师可能常常在与所有的人作对;其二,在与客户的关系中,律师总是处于支配地位,掌握着父爱式的、控制他人的权力 ,而这种权力常常会被滥用。
对抗式诉讼犹如竞技,竞技规则以确保程序公平为唯一目标。在团队竞技中,队员最重要的“职业道德”就是效忠自己的团队,合力对抗另一团队。在竞技规则的边界内,“我方”和“对方”的身份政治决定着队员有关好坏对错的判断——凡有利我方的,就是“好”,应当喝彩,反之则否。一旦进入对抗,非胜即负、赢者通吃的伦理就代替了好坏对错的伦理。
律师与客户分别组成相互对抗的团队。然而,什么样的人会经常购买律师服务呢?在每个社会,需要律师服务并且有付费能力的客户通常是大公司、政府机关、文教机构、黑社会、名人和有钱人,律师不可避免地与这些客户为伍。律师与谁对抗,取决于他的客户需要与谁对抗,“律师-客户”关系决定律师的立场,金钱决定“律师—客户”关系。律师是在决定与谁为伍、与谁为敌之后才进入“角色”的。
3.1.2 角色伦理也许是支持律师、客户关系正当性的最坚实的基础,但是,如果在同一案件中发生角色串演,角色界定的伦理基础也就彻底动摇的。我们常常看到,利益关系导致法官与律师的合作,在合作过程中,法官变为律师,律师变为法官。例如,在北京的金宝花园“窝案”中,律师、法官共谋,律师虚构当事人向法院起诉,法官按照律师的要求作成判决,双方共同分配胜诉利益—当事人、律师、法官三重角色相互串换,诉讼成为一场逐利游戏 。
在中国,客户与律师签约之前常常会打听或者直接询问律师:“与法院有什么关系?”律师也会标榜他们和法院的关系,以赢得客户。
“关系”具有自我复制的能力,是一个具有无限扩张能力的网络,一次交易的“关系”会延伸到下一个交易,交易产生的“关系”又变成可以交易的商品。有“关系”的人会现价销售或者赊销他的“关系”,没有“关系”的人会投资“关系”或者临时买进“关系”,结果是驱动更多的人围绕“关系”而生活。
诉讼中的“关系”真是那么可靠吗?我有许多的理由对此表示怀疑。
首先,“关系”投资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一方当事人并不知道诉讼对手的“关系”投资策略。除非知晓对手“关系”投资的对象、金额、方式和预期回报,任何“关系”投资都是在盲目的状态下进行竞争。
其次,即使得知诉讼对手的“关系”投资策略,律师也不是最称职的“关系”投资代理,因为,律师从来不是接近投资对象的最佳人选——律师无法和法官的亲属、朋友和上司竞争接近法官的能力。
再次,很难想象一个律师能够预测可能影响本案一审、二审和再审的所有法官,并且事先把他们一一“搞掂”。
最后,一个出售“关系”的律师,颠覆了公私关系的全部伦理:他从一开始就试图影响公正审判,从而背离了他应当效忠的法律制度;他把自己和法官的“友谊”出售给客户,使他的法官朋友面临当事人举报的巨大风险,在私交中陷人于不义乃是最为人所不齿。像这样的律师,怎么可能保持“投资”诚信,而将客户委托的资金全部用于发展“关系”呢?
“关系崇拜”或者“关系恐惧”已经成为一种路径依赖或者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迷信。在“关系”的围城中,人们甚至没有勇气去开发一个无涉“关系”的法律服务市场——并不是所有的客户都需要律师的“关系”——那些只有法律服务而没有任何关系的律师本来也可以发展出自己的客户群体。
3.1.3 Wasserstrom教授认为:律师充当某种制度角色,只有当制度本身值得信任并且得到信任的时候,律师的角色伦理才有立足之地;如果律师并不真正相信他自己是在充当制度安排的角色,那么,律师就应当“为虚伪和不诚实缴税” 。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已是老生常谈。问题是:在司法过程中,权力与腐败如何形成相关性?在诉讼中,法官最终决定当事人胜诉或败诉 ,当事人相互竞争,影响法官的决定:正当的影响是在诉讼程序限定的范围内陈述、提供证据、质证、辩论;不正当的影响就是引诱法官偏离中立。
3. 2 深谙法律弊端,法律人易生轻侮法律之心
如同其他制度一样,法律不可能是完善的,法律的缺陷、漏洞和错误能给一些当事人带来利益,给另一些当事人造成困境,律师因而有机会向客户出售他们利用法律缺陷的能力。同样,当成全或挫败当事人请求在法律上都能说得过去的时候,法官作出偏向一方当事人的决定,并不会面对不可逾越的道德障碍。法官不是,也不应当是法律文本的崇拜者;深信只要遵循文义,每个案件都能从法律条文找到现成答案的法官,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多见的。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是一句重复了无数遍的套话。事实上,法律并不总是得到执行,正义并不总是得到伸张,绝大多数违法者只受到自身的良心而不是法律的惩罚。相信当事人只要“拿起法律武器”,正义就会得到伸张,更是无稽之谈,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追寻正义的代价,担心“拿起法律武器”将会造成更大损失,绝大多数人受到侵害之后都会选择放弃求助于法律。
洞悉法制弱点越多,越容易低估违法风险,于是,就有一而再,再而三的越界,直至一发而不可收拾。
3. 3 法律人的学坏与制度混乱
1997年,黄松有是广东省湛江中院的执行庭庭长,拍卖当事人财产属于黄的职权范围。在“湛江中美化工公司”破产案,黄委托两家公司拍卖破产企业的资产,两家公司收取佣金高达1540万元,其中的一半(770万元)分给湛江中院,湛江中院党委又决定将其中的308万元分配给一家名为湛江中院所有、实为个人所有的拍卖公司,拍卖公司又将308万元分配给三个人,其中黄获得120万元。2010年,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黄松有13年年前分得的120万元为贪污 。
法院开设拍卖公司,承揽法院执行自身判决的拍卖,拍卖收入在全体或部分法院工作人员之间分配——在这里,审判权蜕变为一种营利手段。在营利冲动下,法院可以制造不必要的拍卖,可以高估拍卖资产而收取高额佣金(佣金是按成交价的一定比例收取的)。
在黄松有案,如果法院与执行拍卖的公司分享佣金是违法的,那么,法院、黄松有和所有参与佣金分配的人都在同一意义上违法,黄松有应将佣金返还法院,法院应将佣金返还给当事人。如果法院与执行拍卖的公司分享佣金是合法的,而且,法院经商办公司也是合法的,那么,法院将一部分佣金分给它的全资公司,后者再分配给黄松有就未必非法。因此,黄松有是否贪污,与法院参与拍卖佣金分配是否合法、法院经商是否合法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当法院参与营利活动,并且将审判权变成营利手段之后,好和坏、合法和非法的界限也就消失了,法律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恶,制度本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 4 法律人学坏与法学教育
陈忠林教授认为:中国法学教育对法律人学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法学教育的沉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3.4.1 公立法学院的营利冲动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大学的每个学院都赋予了“创收”的职能。所谓“创收”,就是开拓预算外收入,并将这些收入用于员工福利。于是,大学各个院系、各个部门纷纷以大学名义“创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创收”收入并不进入大学财务账,在大学和院系之间、在院系和经营者之间进行分配,分完之后,一切如风吹过,不留痕迹。要而言之,创收就是把灌水学位销售给那些不可能通过入学考试、不可能完成学位课程,但又需要学位的人,于是,为这些人量身打造的“博士研究生课程班”、“硕士研究生课程班”、“在职研究生班”、“专科升本科班”、“在职法律硕士班”如同雨后春笋,四处窜冒,只要随意作一在线搜索,我们就可以发现:除极少数例外,几乎所有法学院、系的名称都和这些“创收”项目的招生广告结合在一起。2002年夏季,我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在昌平开办了28个法学自学考试班(简称:“自考班”) ,也就是说,在昌平城,挂有“中国政法大学”招牌的场所当时有28处之多,以至当时流行一句话:“如今,不是中国政法大学在昌平,而是昌平在中国政法大学。”从2006年开始,中国政法大学停止招生“自考班”,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级的“研究生课程班”、“博士课程班”和“司考班”。
法学院不仅被营利扭曲,而且呈现出一种浅薄的势利,主事者往往不加掩饰地围绕金钱和权力编制关系网,争相把教授、博士、博导的头衔奉送给那些有钱或者有权的人。法学院面对金钱、权势的种种媚态给学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3.4.2 法学教育游离于“有用”和“无用”之间
教授常常面对学生的疑问:“学这个有什么用?”“讲这个有什么用?”“读这个有什么用?”然而,中国法律职业的行业准入规则恰恰排除法学院教育成为一种“有用”的教育,因为,无论有无法学学位,均有资格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没有法学学位的考生的司法考试通过率还超过了法学院毕业生 。“既然学校课程与司法考试没有什么关系,学了又有什么用?敷衍一下,混个毕业也就得了。”这是法学院学生的一般心态。
法学教育未必与学生跨进法律职业的门槛“有用”,这也许是教育自身无法控制的体制问题。但是,如果法学教育不能证明它自身的知识含量,那就面临真正的危机了。按照休谟的的经验主义,知识来自经验,脱离“语境”的法律概念辨析、法律条文文义解释和逻辑分析都不会带来新知,只有将法学概念、法律条文和它们适用于具体情形的推理过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可能形成新的知识。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法学教材大部分已经“去知识化”,因为,它们遵循从清末开始的同一套路:追溯法律的西方源头,重述西方法律原理,以同一句法表达法律概念的定义,将相似概念放在一起比较,解释和分析法条——这一切都是脱离经验的形而上学,但法学绝对不是形而上学的自说自话。中国法学教材还有一个通病,那就是不显示信息来源,然而,如果作者无需参考文献就写一本法学教材,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读价值;如果作者参考了许多文献而没有显示来源,那就涉嫌剽窃,法学教材不应当成为剽窃的示范。
3. 4. 3 法学教授身份的多样化和师生、同学关系的朋党化
现有的评价机制主要看重教授的“江湖”能力,如:教授在官方学会的头衔,教授现有和曾有的行政职务,教授在政商界呼风唤雨的本事,教授是否有可用于为学校争取“211”、“985”和“博士点”的“关系”,教授是否政治正确,教授能够获得多少研究经费,等等。至于教授是否有思想和学问,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教学,基本上无人在意。
在这样的评价系统下,尽可能减少用于校内教学的时间和精力,这对于教授是一个在经济上合理选择。于是,法学教授兼任律师、法律顾问、咨询专家、行政官员、司法考试学校股东,就成为一时之风气,任教、为官、经商、揽讼,亦此亦彼,亦彼亦此,分不清主业和副业。当任教只是教授若干职业之一的时候,法学院作为一个知识传授和生产机构的能力大大削弱,法学教育的品质大打折扣。
学生在教授开设的律师事务所“实习”,学生为教授撰写“法律意见书”,学生为教授介绍需要法律服务的客户,这是当今流行的师生共同经营模式。学生毕业进入法院、检察院之后,放下身段请托学生的法学教授也不乏其人 。
毕业之后,“校友”属于“人脉资源”。学校看重那些权大钱多的校友,把他们罗织到学校“董事会”,组成一个常来常往的俱乐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董事会”和谐并存,构成了中国大学治理结构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在中国政法大学,校方公共关系的方针之一是“牵手富校友” ,“牵手”颇显浪漫,在闽南语,丈夫称妻子为“牵手”,大学青睐富校友,与之“牵手”,这确实很时尚。
法律人的时风流弊,并非始于今日。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制,为解决“生员”的学习和就业,政府采取了一项重要的“维稳”措施,这就是开办“法政学堂”。于是,法政替代科举,成为“易学、速成、致仕”的新途。民国初年,法政学堂占全国大专院校总数一半左右。法政学堂造成了人们对法学教育和法律人的坏印象 。
4. 结语
水门事件把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摆到了所有法律人的面前:为什么法律人的道德障碍比一般人脆弱?尽管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但是,从中都看到了法律职业的道德危机,都意识到了整个法律行业都面临着失去公众信任的风险。于是,在美国律师协会的推动下,法律职业伦理成了法学院的必修课和律师入门考试的单考科目;法律职业行为规范也一再修订,以树立法律人对整个法律制度的责任心。教化和规诫并举,能否带来实质改变,现在作出结论还为时太早。但是,从公共关系的角度观察,这至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诉讼在美国是过度对抗,在中国则是对抗不足。在过度对抗的诉讼中,律师为讼斗士,不遗余力地为客户争取利益,从而也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角色决定对错的伦理在此发展到极致。当诉讼本身对抗不足的时候,当事人可能在法庭之外、法眼目力有所不及的地方开展另类“对抗”。我们很难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律师扮演着同一角色,制度差异决定着角色差异。
法律职业并非具有理所当然地具有正当性。法治社会使律师、法官和其他法律人成为正当“角色”,每个角色都有义务,单独和共同证明他们在法治社会的存在具有持续的正当性。如果制度造就的角色成为制度无法控制的力量,冲击制度的价值和整体结构,那么,角色就发生了“异化”。在某种程度上,法律职业伦理的作用是制约法律职业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