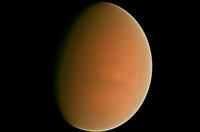应该说,中国领导人迫切希望推行司法改革,动力并非源自创建西式法治的意愿,而是他们渴望重建党的公信力。
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著作《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 ),二百多年来促使许多西方人相信中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是缺乏民主合法性及压制个人自由所致。这种常见的误解源自对中国政治历史的无知。西方观察人士往往认为,“法治”与“依法治国”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指西式的司法公正,而后者是依照法律条文进行专制统治。
中共最近召开了四中全会,西方媒体的评论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这毫不令人意外。然而,如果认为中国只是为了巩固政权而实施“依法治国”而非“法治”,则未免过于简化乃至误读了。
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从长远来看,共产党的利益必须与人民保持一致,否则政权就将崩溃。中国人习惯从儒学的角度理解政治合法性,即他们期待政治精英们遵遁正确的道德标准,共产党也不能例外。因此,中共判断合法性的公开原则,所讲求的也是儒家式的 “行为合法性”,而不仅仅是“程序合法性”。前者反映 “道德精神”的有机层面, 后者则基于机械论的“法的精神”。
当然,并非所有党内精英都将人民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腐败及权力寻租有愈演愈烈之势。党内纪律机制的功能失调,令腐败官员得以利用程序上的种种缺陷和漏洞贪赃枉法。长此以往,不免让人担心皇帝新衣的故事会在中国重演。
好在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当机立断,习近平从履新的第一天起就公开讲,腐败愈演愈烈终必亡党亡国。中共最高层明智地意识到,有必要通过司法改革来挽救党的声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应该说,中国领导人迫切希望推行司法改革,动力并非源自创建西式法治的意愿,而是他们渴望重建党的公信力。正如最近召开的新古田会议所显示的, 党的公信力深深植根于其辉煌的历史,并建基于习近平所说的“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
在这个时刻,法治成为政改的亮点,因为只有推行司法改革才能重建民众的希望和支持,为中国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推行真正的改革扫清道路。
从这层意义上说,司法改革的核心目的是要通过依法治国(假设法律完善)去管控党的官员,而并非全盘实施西式的法治。关键的改革目标,是要避免党内高层直接干预司法程序。中共希望引入半自治的巡回法院体制,将司法程序与行政权力分离,并借此实现这一目标。
四中全会上提出的改革建议,尽管不是突破性的一步,但其潜在影响很深远,因为党巨大而无处不在的权力将首次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制,亦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习近平语)。
更重要的是,如果拟议的司法改革有效,未来有可能出现中国司法与西式法治相融合的趋势,中国司法的部分传统仍有可能留存。中国数千年来,王朝的兴衰并不是由特定的决策机制决定的,它取决于领导人的表现。中国的政治与人的伦理行为有关,与空间无关。权力与人的性格和行为息息相关,又如何能够转化成孟德斯鸠所提出的“三权分立”?
所谓法治,建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西式的法治以个人权利为基础,法律是捍卫个人权利免受国家侵犯的最终保护手段。但中国传统以来,个人权利从不曾高于集体权利。制定法律是作为社会礼仪的补充,利于阐明行政职责,以便在维持社会稳定的过程中,填补社会礼仪存在的缺陷。
因此,可以将中国法律的演进形容为一条下行曲线——礼仪无效则退化为法律、法律无效则退化为惩罚。从制度上来讲,中国从未创建过“司法”部,仅是创建了“惩罚”部门,即刑部。孔子曾任鲁国“惩罚”部的长官(古称“司寇”),并以中国的法律思维解释了“耻”的原则:“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
西方的契约式法律概念源于虚构的“社会契约”。中国传统没有契约论,儒家对任何没有历史根据的假想社会没有兴趣。比如霍布斯的所谓“自然状态”, 在儒家看来不过是荒蛮世界,不可能产生理性的契约。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唯一与霍布斯思路相似的论点,但他基本出发点是反儒家的。无怪乎苏轼说,“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契约式法律是重商社会的产物,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法律背景下没有什么意义。
即使在今天,对中国人来说,“律师和诉讼越多表明社会越稳定越公平”的治理思维仍然是难以被民众所接受的。反之,他们会认为这是社会动荡和普遍道德沦丧的象征,其前景令人担忧。
实际上,如果不从西方法学理论的角度来看,现任的中国领导层已经在法治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时,中共如今已经接受了法治的某些普遍性原则。但要中国一刀切断“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传统,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因此,习近平反覆强调重建党德的重要性,同时开拓适当的法律程序,作为管控政治精英的补充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