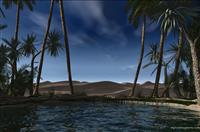中国宪法学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在100多年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宪法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之间形成了一种混合的制度体系与学术体系。尽管在旧中国宪法发展中脱离宪法理性的制度与文本所占的比重比较大,但就整体学术脉络而言,不同时代学者们所提供的宪法学知识保持着不同形式的学术关联性,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1]特别是,宪法学作为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提倡知识与学术的历史传承,使宪法学说成为连接知识与经验、现实与历史的纽带。
宪法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宪法制度史、宪法思想史和宪法学说史等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其中,宪法制度史是从宪法发展的制度变革层面来研究宪法的发展历程;宪法思想史是从宪法发展的思想流变层面来研究宪法的变迁过程,凡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宪法问题有关的观点、主张等都可以属于这一知识体系,其本身的理论体系化程度并不是判断宪法思想史成果的标准;而宪法学说史则是从宪法发展的学术积累层面研究宪法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考查宪法的历史积淀,旨在探讨特定概念与范畴体系化、整体化的过程。它既不同于宪法发展历史,也不同于特定时代宪法思想的记载,是对学术对象变迁的“再认识”。当然,在宪法学说发展中制度、思想与学说又保持着关联性,在互动中寻求发展。
在中国,宪法学说史描述与再现了历史事实。在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前后,我们建立了初步的知识体系,追求着一种宪政理想,但学说的历史带有深沉的政治影响。[2]以控制国家为目标的宪法,往往在国家的主导下获得宪法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中国宪法学说具有浓厚的“国家学说”色彩,特别是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关联性中寻求发展。由于“富国强兵”成为中国立宪的指导理念[3],通过学术活动论证国家的正体性与统治的合理性也成为宪法学说发展的内在动力。宪法学者们试图通过学术论证自己国家的“正体性”,即体制的历史基础与渊源。在他们看来,没有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与把握,不可能产生维护正体性的信心与责任。在一百年的中国法学发展史上,宪法学历来是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学科,承载着不同时代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制宪、修宪,还是公共政策的调整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生活对宪法学的需求以及宪法学发挥的社会功能。同时,中国宪法学在各种政治现实面前努力保持着学术自主性,传承学术传统,使宪法学的脉络得到了延续。
近百年来的中国宪法学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宪法思潮、理论、主张以及不同学派的学术风格。对百年宪法学学术传统与遗产,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学术立场?笔者的基本思路是:我们需要全面梳理(清理)百年宪法学说史的历史,找出经验与教训,在客观地评价宪法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宪法学中国化”的进程。
首先,通过研究宪法学说史,我们可以寻求宪法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因素,获得对宪法学的整体性认识。如前所述,在宪法制度、宪法思想与宪法学说的三者关系中,宪法学说史的研究对于宪法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宪法学说史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宪法学的相应发展,而另一方面,宪法学的良性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宪法理论的良性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判断一个国家的宪法理论与宪政实践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志之一是这个国家是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宪法学说。所以,系统的研究中国的宪法学说史,对历史上存在过的宪法学说进行细腻的卓有成效的梳理,不论是对于中国宪法研究的发展进程,还是对于中国宪政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次,宪法学说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国际化时代,保持宪法学主体性,突出宪法学的“中国问题意识”。由于存在着宪法与法律功能的差异性,法律“全球化”空间是比较大的,但宪法作为充满“民族性”的社会共同体最高规则,始终体现着特定的文化与传统,而这一特点在宪法学说的发展过程中表现的尤为突出。面对全球化的新的背景,西方的宪法研究成果和理论依据固然可以成为我们参考、学习的经验,但是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差异,它无法直接成为我们宪法研究和发展的依据。因此,中国的宪法学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还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宪法文本,面向中国的宪法实践。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学者们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风格,这些不同时期学者的努力延续下来,形成一条既各具特色又互相关联的思想脉络。这种思想史上的绵延关系就构成了中国宪法学说史的知识谱系,也构成了中国宪法研究和发展的基本框架。因此,中国宪法学面对的是中国的宪法文本和宪法历史,必须依靠中国宪法学的本土资源和理论框架。所以,宪法学说史研究的首要价值就在于中国的宪法研究和发展必须要依靠中国学者的自身努力,必须要以中国宪法学说为基本的理论依据,否则,纯粹意义上的中国宪法学研究就会出现知识结构上的不平衡和空白。
第三,中国宪法学说是宪政建设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4],这句话揭示了宪法在宪政建设中的突出地位和根本作用。要想发挥宪法在宪政建设中的作用,就要对宪法进行历史和现实整体性的研究,从而在理论上深刻揭示宪法和宪政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同修建房屋需要图纸、蓝图指引一样,宪政建设也需要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论指导。在中国的宪政建设中,这种更高层次的理论指引主要是指对中国宪法发展的一种总括性研究,也即是对中国宪法学说史的研究。就像中国的宪法研究和发展必须要以中国宪法学说为理论依据一样,中国的宪政建设也必须要以中国宪法学说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中国宪法学说只是中国宪政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并不是唯一的资源。因为在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法治、宪政、人权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结晶,是人类共享的价值。正是因为法治、宪政、人权在人类文明成果意义上的价值相通性,所以,我国的宪政建设可以充分的借鉴、吸收西方宪政发展的文明成果,从而加快我国宪政建设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百年宪政的历程之中,既有宪法被虚置、宪政被破坏的惨痛经历,也有宪政建设逐步走向正轨的成功经验。如何汲取宪政失败的惨痛教训,总结宪政成功的合理经验就成为关系我国宪政建设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宪法学说史的研究恰恰是从历史的视角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种宪法学说和宪法实践的成败优劣进行一种冷静的理性分析,从而为我国宪政建设提供一种历史意义上的参考与借鉴。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宪法学说史的研究成为中国宪政建设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之一。
第四,要探索中国宪法学历史起点,必须系统地梳理宪法学说史的历史文献。
宪法存在于历史过程之中,历史的事实是解读宪法价值的基本标准。尽管各国的宪法史有着不同的研究内容与对象,但通常包括宪法规范与宪法现实两个方面。宪法规范中我们可以发现制宪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争论、特定宪法的性质与形态、社会共同体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结构等。以规范或法典形式存在的宪法规范首先被纳入宪法史研究的视野之中。在这个领域中,宪法学文献的发掘、整理是十分重要的。国外关于宪法学说史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比比皆是,不仅对于宪法自身的理论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学说体系,而且对于宪政实践也有一整套比较完善的思想体系。当我们汲取西方国家的宪法理念、研习西方宪政经典的时候,通常会为西方学者眼花缭乱的流派与观点之争而由衷的叹嗟不已,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观点迥异而又自证其成的学说观点与学术流派,使得西方的宪法理论和宪政实践在智慧的撞击中螺旋前进,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宪法学理论体系,进而推动了整个宪政事业的发展。
但是,囿于学术研究中的某些实践性和功利性因素,当前的宪法学界对中国宪法学说史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尽管从宪法制度史、宪法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宪法历史的著作和文章屡见不鲜,但是,真正从宪法学说史的角度对近百年宪法发展进程进行系统的学术梳理的成果却少之又少,几近阙如。虽然,从表现形式看,宪法制度史、宪法思想史和宪法学说史最终都表现为特定的宪法理论成果,但是,宪法学说史与宪法制度史、宪法思想史的区别决定了对宪法思想史和宪法制度史的研究代替不了宪法学说史的研究。宪法学说史是从学术传承、学术积累角度对历史上存在过的宪法学说的一种整理和归纳,而宪法制度史和宪法思想史则仅仅是从制度沿革和思想发展角度对宪法历史过程的一种描述,两者存在着不同的学术理念和价值追求。与其他学科相比,中国宪法学体系的不成熟性是比较突出的,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宪法学不重视对自己学术传统的继承。如何改变宪法学的不成熟状态,如何提升中国宪法学的学术品格就成为每个宪法学人的社会使命。
第五,宪法学说史研究有助于我们避免重复性研究,进行学术创新。从学术史发展历史看,所谓的学术创新首先建立在对已有学术成果与传统的系统梳理,要了解本学科或具体研究主题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但遗憾的是,我们仍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形成的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背景与渊源缺乏必要的了解。有学者指出:“不知前贤已有的研究,而以为是自我作古,由已原创”。其实,现代社会面临的有些学术命题我们的学术前辈们已作过系统的研究,但我们仍在进行简单的重复性研究。学术的生命力在于挖掘新资料,寻求新方法,而新观点的“新”在于全面把握本学科的学术脉络,从丰富的学术渊源中获取文化的支撑点,并引导方法的更新。在这种意义上,注重宪法学学术背景与学术关联性的研究,有助于保持宪法学的主体性,从而使宪法学研究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少走弯路。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系笔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07BFX07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 详见韩大元〈中国宪法学:20世纪的回顾与21世纪展望〉,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2]有学者在分析“清末宪法草案乙全本”的篡拟时认为,它“是20世纪初中国法学界对以往学习西方宪法学、政治学的成果作出的一次全面总结,其内容涉及了宪法学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部完善的中国早期宪法学体系。俞江:《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的发现及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6期
[3] 1906年9月4日,由光绪皇帝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提出“……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同,博采众长,明定国体,以及筹备财政……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析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之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3]
[4] 胡锦涛:《在纪念宪法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