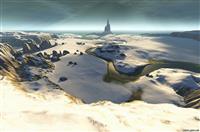如一般所理解的,在民主社会当中,国家的治理权被要求允让其公民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并对这些权利的行使给予法律的保障。在这样的宪政安排下,公民得以自由地结社,以从事各种活动,并且公开表达、出版各种言论,或者参与政治。这些事务在某种程度上皆具公共性的倾向。民主体制既然允让公民这些权利的行使,那么,我们可以说公民权利之行使促使民主政治之公共领域的开展。各种不同的言论穿梭在这个领域内,相互辩论、批驳,并藉由传播媒体的帮助,言论的表达与论辩普遍性地扩张,而为公民全体所关注。也在这个领域内,公民透过自由的结社,得以针对某种政治议题或政策,形成各种不论是抗议或支持它们的行动联盟与社会运动。
尽管公共领域是由国家治理权允让基本的公民权利及其法律的保障,而得以开展出来的;但它并不成为民主体制的一项制度安排,如国会或者地方性的各种议会。从这里引发一项理论解释的问题:公共领域与国家权力彼此形成什么关系?它是“外于权力”(extrapower)的共同空间,或者是内在于国家主权的场域?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也涉及“公共性与私人性”(public/private)的区分。本文从这问题的取向,阐释公共领域之概念的意义。在这方面,本文尝试论证以下的主题:“公/私”的区分是人类各文明社会皆有的概念;但是公共领域的开展是在欧美之现代性的进程中方出现的。在此脉络中,公共领域的出现伴随着资本主义之市场经济(特别是“印刷业之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发展。就此而论,公共领域的形成是跟国家主权脱钩的,但是又必然跟国家主权有所关联。公共领域的这种既开放又受限制的处境是使得现代民主有所进展的关键之一;但也构成民主政治的问题。如我们所见,公共领域随着欧美现代性的进程,容受繁复多样的需求,以及辩解这些需求的各种言论或者意识型态。它们彼此交锋、彼此抗衡。时至晚进的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公共领域受到各种阶级的、种族,或者文化、性别的认同意识及其论述所分割。公共领域的界线愈显得模糊,也显得零碎化。不仅如此,这些争议也愈难取得共识。面临这种处境,本文最后针对民主的共识及其公共领域的规范性的议题提出某些观点。
一、公共领域的古典意象与现代诠释
当代公共领域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1906-1975)启其端绪。她提供了思辨的资源与解释的基本架构。在1958年出版的《人之境况》中,鄂兰以人之vita activa(活动之生命)的范畴区分为解释架构,对于人之公共言行之实践(praxis)提出了“剧场式”(dramaturgical)之阐释,其基本论旨在于,人的“实践”活动必须落实在一开放的、平等的人际之公共空间。在其中,个人彼此争胜,以表现其优异的言行。犹如在一剧场中,个人把他最优异的言行表达给在场的其它人。在这里,鄂兰不讳言以古希腊城邦的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agora(广场)为意象,阐释人之实践活动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进一步言之,是跟人的内在心灵(如意志的活动与良知的反省)、家庭生活(包括人际的亲昵关系)、经济活动(包括任何营生的活动)…等区分有别。在1963年的《论革命》,鄂兰以现代革命的实践为解释的脉络,对于人的实践活动,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观点,即“公民之结社”(societas,civic association)之理念,它强调行动者藉由相互的信赖、以及承诺的约定与实践,彼此合作,形塑公民之权力(civic power),共创新的政治空间,营建得以维系此自由空间的宪政制度①。鄂兰所立的这种实践与公共领域的理念引发了如Seyla Benhabib所举的两种公共领域模式〔一是争胜式的,另一是协合式的(associationist)〕的解释及其政治思想之定位(鄂兰是共和主义,抑或自由主义?)的争议②。姑且不论诸如此类的诠释性的争议,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她的公共领域的理论跟现代性的处境难以产生接合之点。这来自于她对西方现代性的重要建制,如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主权国家以及自由主义的意识型态,给予否定性的批判。③因此,她的公共领域的理念如何在现代处境中呈现意义,就显得闇然不彰。
跟鄂兰同一时代的英国政治思想家麦可‧欧可秀(Michael Oakeshott,1901-1990)就质疑鄂兰的公共领域的政治解释。欧可秀在其晚年的著作《论人之行为》中,对“何谓政治性”(what is the political?)的问题,进行阐释,而触及了“公共性”与“政治性”的议题。④基本上来说,欧可秀承继霍布斯式的自由主义传统,以主权国家与“属民”(或公民)的关系,分辨与界定“政治性”(或“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意义,因此,所谓“政治性”(或公共性)意指主权国家之宪法与各种法规构成的,为公民在其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条件。如是言之,“从事政治活动不需要特别地被界定于某一个地方或场合。它是一种公共性质的活动。在进行或追求此活动当中,‘法治之条件’(a civil condition)可能被遵循,公共关系也可能是重心。然而,政治活动并不必然在公共领域才能进行。”⑤针对鄂兰式的公共领域的解释观点,欧可秀特别地指出其基本的意义在于,公民公开讨论宪政法规的议题,而跟公民从事的oikos(家计与产业管理)的活动有所区别。
从欧可秀的这种观点,也多少可以看出自由主义者不甚强调公共性的空间观念,而毋宁关注公/私的人际关系以及思辨“私人性”之关系与生活如何不受他人(包括政府、社会与舆论力量)的干涉。
鄂兰所建立的公共领域的理论虽然有其内在的论证的“弱点”,但也启发当代有关此概念的各种不同的阐释及其理论的开展。尤根‧哈伯玛斯(Jű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的理论即是典型的代表。如果说鄂兰的公共领域理论无法承载西方现代性的意义,那么,哈伯玛斯是从鄂兰所否定的现代性的脉络中,提出了另一种公共领域的理念。他强调,推促此公共领域开展的力量来自拥有私产的所谓“资产阶级”(或称“布尔乔亚”)。就这阶级的世界观而言,他们所关注的是个人经营的产业与金融业,他们所追求的是资本的积累,他们所形成的人际关系是相互竞争。然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无限扩张以及它们的经济网络与机制的愈为复杂,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无法如古典共和时期的公民一样局限于oikos(家庭式的产业),而必须跨出这个私人的领域,进入更广大的阶级的关系网络,即所谓的“布尔乔亚的市民社会”。在这个地方,家庭与家族不再是经营生计与从事经济活动的场域,而成为家属成员维系亲昵之情感,个人发展其个性,学习人际之基本礼节的地方(但也免不了有家户长式的支配与情感之摩擦,家属之间的倾轧)。哈伯玛斯在阐释现代性之公共领域的形成时,并没有割裂家庭之私领域的关联。然而,问题在于,“资产阶级”本为关注私利以及注重家庭生活的人格,他们如何形成其公共领域?针对这个问题,哈伯玛斯从十八世纪市民社会的“非官方”的制度(如沙龙、咖啡厅、俱乐部…等)以及文字媒体(如报章杂志、期刊以及各种文艺刊物…等)的形成,说明这些制度与文字媒体成为 “资产阶级”集会以及言谈,沟通的场所与媒介。这些地方既是集会,沟通的场所,自然地会形成公众之意见或舆论,并且藉由文字媒体的传播,得以广延开来。这些舆论,就其谈论的课题与对象而论,并不纯然是“政治性”的。依照哈伯玛斯对 “资产阶级” 性格的了解,他们不像贵族阶层一样,敌视或对抗当时的 “君主制”(monarchy)。他们反而要求一个一统性的最高权力,以保护他们从事的私人企业,并透过有效的政府治理与法律的规范,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全发展。这种对国家主权的态度使得“资产阶级”没有强烈的野心推翻当时的王权及其体制,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其最高权力能受基本人权的限制,而且公共领域的舆论能成为监督政府的机制。以Jean Cohen与Andrew Arato的阐释,哈伯玛斯的公共领域是“资产阶级”所属,但也同时是自由,也是民主性格的⑥。
就当代公共领域的论述而言,鄂兰与哈伯玛斯分别建立两种型态,一是具古典共和理念与精神;另一则是具现代资本主义性格与自由民主理念。除此之外,在说明公共领域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上,两人的阐释观点相重迭的地方在于,公共领域是脱离国家主权的。以鄂兰激进的观点来说,公共领域甚至可以凝聚强大的权力,在国家权威扫地之时,足以颠覆、推翻它,另创新的体制(如在革命的处境中)。相对而言,哈伯玛斯的公共领域虽与国家主权脱钩,而成一自发性与自主性的领域,如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一样。然而,从公共领域的针对性而言,公共领域的舆论是用来批判、监督与约束国家主权的。就此而论,公共领域亦涉入国家的主权,两者形成某种程度的紧张,甚至对立的关系。扣紧这个论述的主题,哈伯玛斯亦广延地思辨公共领域、市场经济与家庭等私人领域在互动关系中形成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之公共领域的限制。不详论哈伯玛斯对他自己所建立的公共领域的理论反思,对当代公共领域之论述而言,他确立了现代性之公共领域的模式。
承袭鄂兰与哈伯玛斯的公共领域的理论,当代另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亦提出他的理论见解。基本来说,泰勒的公共领域是现代型态的。他强调公共领域的理念是西方现代之社会之特征,也是社会想象构成的要素之一(其中尚且包括市场经济体系、人民主权或自治以及人权的理念)。除此之外,公共领域与其它构成的要素都是超乎或外于权力之上的,而且成为权力论述其正当性的根据⑦。泰勒采纳哈伯玛斯的观点,认为公共领域的形成源自十八世纪,“它是社会想象的转变,是现代社会进展的关键,是(现代社会)长征的第一步。”⑧在这里,笔者不再重复说明泰勒对公共领域的基本界定以及公私领域的区分。这些基本的限定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如公共领域是人们相互讨论、结社,而且大众媒体贯穿期间的公共空间;人们所讨论的是他们共同关注的课题;在进行这些讨论或沟通时,参与者肯定“不偏私”的公共理性以及设定并遵守一定的程序;公共领域跟经济、家庭生活及其亲昵之关系、个人主体性及其内在心灵与感情,以及美感的享受与品味…等(即所谓的私人性事务)区分有别。
泰勒的公共领域理论饶有意义的地方,是他区分公共领域的两种型态,一是“主题性的共同空间”(topical common space);另一则是跨越主题性的公共空间(metatopical common space)。前者意指区域性之集会,后者是指足以含括各种“主题性之集会”的广延性的空间,其广延性甚至可以跨越国界。能形成这种公共领域的条件之一在于,欧美自早期的“印刷之资本主义”到当前信息媒体之科技的进展。泰勒所阐述的公共领域即是这种跨越性的共同空间。关于这个公共领域的理论,有两项主题必须说明的:一是它的现代性格,或者说,它与古典时期的koinōnia(政治共同体)的区分;其次是它的规范性地位。
1、泰勒在阐释公共领域的现代性格上,乃跟随哈伯玛斯的基本观点,亦即这个共同的空间乃是人结社、理性讨论、争辩与沟通的场域。这个场域是自发自主的,其形成“不受任何政治结构所赐予,相反地,它独立于政治结构之上。”⑨。尽管泰勒的阐释步随哈伯玛斯,但在说明构成这个公共领域的行动主体时,泰勒不强调其阶级性(如哈伯玛斯的资产阶级),而是在现代社会中互为陌生的人们。这跟古典的koinōnia的“政治同侪”不同。他们彼此陌生如一盘散沙的人群,他们之所以可能形成一个共同的空间乃借助文字媒体的传播。是故,各地区(不管远近)发生的事情、事件经由文字媒体的传播,都有可能成为共同关注、谈论的议题。⑩
在这里,泰勒有时把公共领域的这种人们之结合,称之为“文人之共和”(the Republic of Letters),这个共和的构成是外于政治的。如他所说明的:公共领域犹如一个统一性结社的共和,它是由所有开明的参与者结社而成,也跨越了政治的领域。是故“一个政治社会的所有成员应视之为形成一个外在于国家的社会。这个社会比任何一个国家更为广大;它有时为某种目的,而延伸到文明欧洲的所有人。
”11
其次,泰勒强调公共领域之现代性乃在于它的“根本的世俗性”(包括世俗性之时间意识)。世俗性并不表示传统社会的基督教信仰(或者任何信仰)在现代社会的处境中式微,而是特别指人们在现代性之处境中,对于自我了解以及共同行动的正当性论据,不再援引某种超越性的论据,如上帝的理念,或者如“存有之炼”(the Great Chain of Being)的理念,或者传统的法律,如“古宪政”(ancient constitution)的理想。在过去,这种“超越性之论据”可以把人们的自我了解与行动安置在“一个架构内,而得以使人相系相连,结合一起,塑造成一个社会。”12除此之外,涉及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创建,世俗性意指人们不再相信有一“根基性的行动”(the foundation acts)以及一个特殊的、神圣性的“根源的时刻”(a time of origins);这种时刻表示“它与我们的行动不相类属,也不是框架我们的先行者,但与我们有因果连属的行动。它不只是早先的,也是另类的时间,一种典范性的时间。”13
现代性的公共领域即是这种“世俗性”的开展。在现代的处境中,人们的共同行动形成某种结社,继而构成公共领域;就此构成而言,人们的共同行动与共同的了解即构成公共领域本身,不必援引“一种需要建立在确定的‘行动之超越(actiontranscendent)层次上的基本架构,不论是藉由上帝的行动,或者在‘存有之炼’当中,或者凭借我们不知其所以然来的传统。这即是造就公共领域之‘根本世俗性’(radical secular)之所在;同时,这也是让我们得以认识它之所以为新之关键。”14
2、泰勒在提示公共领域之规范地位上,他从公共领域之“外于政治”之性格,阐释公共领域呈现理性彼此的批判性论辩,而不是反映一般的民意。理想地来说,透过这些理性之批判性论辩,而得以形成“开明的”(enlightened)舆论,这种舆论对于政府的作为与政策具有针砭之作用。政府应当听从此舆论,俾能修正与改革其政策与行为的缺失。公共领域随着参与者的扩大,也形成“人民是最高权力”的理念。此理念在十八世纪末叶,透过两次革命,成为自由民主政府论证其存在之正当性的理据15。对于公共领域的规范性地位,泰勒做了如下的陈述:
在公共领域当中的讨论端赖开明的、客观的的社会了解与理念,不论这些理念是经济的、政治的与法律的。公共领域的基本性格亦表现在这里。从某个角度来看,舆论被视为理性的——是理想上的理性。它是冷静且理智的讨论的结果。从公共领域的另一个角度来看,公共领域也不可避免地被视为一种共同的行动。公共的讨论有其结论:它凝聚成舆论、公共的心灵或者集体的判断。更终极地说,这舆论逐渐地,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正当性的原则。16
哈伯玛斯与泰勒分别以不同得阐述途径,建立了自由与民主之公共领域,或者说,理想模式之公共领域。但是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什么的作为与理念导致公共领域徒具空间形式,甚至造成它的消逝?时至当前的晚近现代社会,公共领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二、现代性之公共空间面临的问题
如上所述,公共领域的形成,是与国家主权分离的,而呈现“外于政治权力”的性格;同时,基于它所形塑的理性之开明的舆论以及人民主权的理念,在现代自由民主的体制中,公共领域成为国家权力运作的正当性理据。在西方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公共领域因其“非制度性”的安排及其带有的人民主权的理念,而产生如下的情况:
现代主权国家在其统治的疆域内,尝试整合各自分立与自主性的领域,包括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以及公共领域,而带出来政治权力与公共领域所形成的“督促政府”之舆论,两者彼此之间的摩擦与冲突。二十世纪出现的法西斯主义与极权主义政权其基本的性格乃是,凭借全面控制的政治权力压碎公共领域以及消除其它自主性之领域。
若以泰勒的阐释来说,公共领域预设多元的、区域性的“主题性之公共领域”,换句话说,公共领域内涵繁复多样的理念、意见。就此言之,公共领域的共同性如何可能?如上面所解释的,自十八世纪以来,传播媒体的扩展促使公共领域形成某种共同性,即任何区域性的议题可以成为广大之公众关注的议题。但是,依赖公众媒体以形成共同性,公共领域内部的共同性毋宁是碎弱的。大众媒体不可能成为某种具权威性的“集体机制”(collective agency),以调节公共领域内彼此分立的理念与意见,俾能形成某种同一性。相反地,大众媒体也可能响应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藉由炒作非关公共论述的课题(如揭露公共人物的隐私性)来提高其利润;或者,公共媒体也可能受政治党派与利益团体所操纵,而变成某种意识型态的传声筒。在这情况下,大众媒体沦落为偏私性的机制。
公共领域酝酿冷静的、理性与公正的舆论。它代表一种集体的省思与判断。然而,舆论也可能形成某种“道德多数之压迫”,倾轧人的个体性。特别在社群的集体生活与体制产生严重的危机时,这个由公共领域塑造出来的“道德多数”因心里的不安全感与焦虑,容易倾向寻找“替罪羔羊”(或公众敌人),藉此缓解他们因体制之危机所形成的焦虑。在现代社会的处境中,暴力也可能体现在公共领域内的“道德多数”。十九世纪的托克维尔与密尔在他们的政治论述中,已表达出这种忧虑。
公共领域的形成是跟随着人民主权的理念,这个鲁索式的理念,就其原来的论旨来说,乃试图跨越过去之契约论所设想的公利与私利相合的理论,进而塑造出真实的,具道德性的共同意志。这种共同意志被设想为优先于(不论是论述逻辑,抑或政治实践)既定的政府。人民主权,如是言之,蕴含颠覆既定权力的理念。积极来说,它足以唤醒被宰制、压迫之人民的解放;负面来说,它所蕴含的“真实之道德性”的观念,也孕育出善恶对立的“道德性政治”。自十八世纪末的革命以来,人民主权遂逐渐形成现代性之自由民主制的正当性原则。然而,人民主权之理念本身带来“何谓人民?”的争议;显现在公共领域的进展上,则是从“资产阶级/贵族阶级”以至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人民之界定、分化与抗争。时至今日,民族性、文化性、族裔性与性别…等等理念涉入了有关“人民”之范畴的界定。界定“人民”之范畴所运用的语言、论述的概念架构以及呈现的价值理念往往形成分立与“不可通约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而造成基本共识的难以确立以及公共领域的“零碎化”(fragementation)。无可讳言地,公共领域因人民主权之理念及其争议,而得以防范它自身的排他性。但是他内在所形成的“零碎化”若缺乏某种程度的“集体性的机制”以及共同的目标或价值,或者说,缺乏“政治的同一性”(political identity),公共领域甚至整个社会可能形成某种“无政府”的状态。
三、公共空间的伦理性格
本文在这里以这些问题为思考的取向,尝试对公共领域的活动意义作进一步的规范性之反思。这一方面的思辨牵涉人际之间的伦理以及政治权力之运作;探讨的主题包括公/私的区分、共同价值与意志以及国家主权与公共领域的关系。
在阐述公共领域的人际之间的伦理上,美国哲学家Thomas Nagel提出了如下的观点:
人既是复杂又个别分歧。一个人若要求他的感情、心思与要求悉数为公共空间所接纳,那么,势必带来人彼此相互侵犯与冲突。公共空间乃是复杂且彼此分歧的个体彼此交会互动的地方,它是单一的而且有其限度。每一个人的言行表达必须是公共空间里的人们可以面对处理的。若非如此,个人言行的表达必会带来人际的混乱与纷扰。诚然,是有不同的空间以及各种团体,它们各有其可容受冲突的限度。但是所有公共空间的运作均如同某种交通管制的形式,必要调适个别差异的人们,他们个个都复杂万端,而且潜在的冲突与斗争也是漫无止尽。同样地,我们为了彼此的调适,在处事处人方面,必须学习通融、谦恭、忍让,处处为人留余地,顾及他人的面子, 以及不计较他人无心的过失。这些态度不是虚伪,而是我们可以体会的人际交往的常规习尚。我们在公共交往的过程中,如果毫无节制地表现欲望、贪念、蛮横霸道、焦虑不安与妄自尊大,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公共生活可言。同样地,如果我们毫无顾忌地表达个人的心思、情感与隐私于公共空间,而成为公共舆论的焦点,以为如此才能造成坦荡荡的人格,那么,我们就毫无私人生活可言。17
Nagel在这段引言中,阐释公共领域是复杂且彼此分歧的个体彼此交合互动的地方,是一个言行之公开表达的空间。但既有彰显,就必要有遮掩,换句话说,必要有公/私的分际;这种公/私,彰显/遮掩的分际乃构成公共领域之伦理条件。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区分公共性与私人性的伦理宗旨在于保护私人性的事物(与事务)使它们免受政府或社会力的干扰与侵犯。但我们是否可能对公/私做一个明确的界说?对于这个问题,Raymond Geuss提供如下的观点:“(在思考公/私的区分上)我们并没有必要去发现何谓公与私的区分,然后决定我们应该以什么价值态度去面对。相反地,在我们既定的价值与知识下,决定何种事物为我们认为需要规约的或者必须关照的——然后在它们身上印上‘公共性’的标示。”18这种类似方法论的观点,其要义乃承认我们无法得到一种单一的区分公私的原则,因为公与私之别及其对立,其型态繁复多样,它们既非绝对性的;但是,也不是所有的这种分别与对立都不实在。重点在于,当我们在做这种区分时,有必要给予某种理由,但“给予理由”是有其特定具体的脉络与目的,并考虑得以实现此种区分的能力。19
姑且不论这种方法论在操作上是否流于一个个案接着一个个案的琐碎的概念与语意的分析,Guess的方法论提示了公共领域之规范性思辨必要阐释的问题,即:如果我们跟Guess一样承认公私的区分界线难明,彼此各自多元分歧,而且也可能重迭,那么,我们如何可能去处理公私分界的问题?从抽象的理论层次来看,公私分界既然难明,就没有一个人(包括国家之执政者与某些社会大众)可以正当性的宣称某种“正确”(或正统)的判准,而强加于其它人身上。这种所谓“正确”(或正统)的判准很容易带来集体性的权力藉由政治的压迫或社会的压力,来控制个人的生活(包括其内在心灵),“更糟的是,它会造成某种(社会的)氛围迫使每个人为证明自己是站在正确的一方,而言不由衷”,虚假、作伪便成为惯常之事。20
涉及公与私之分辨的议题,若我们避免使用任何势力去声张某种正确区分的原则,那么,另外的替代途径即是,透过公共的讨论去议决公与私的分际的诸种问题。以宪法所保障的“隐私权”为例,所谓的“隐私”的界定为何?公众人物的“公共”与“私密”的生活是否可以公开?又以“防范家庭暴力”为例,我们是否可以因为防制此暴力的发生,而可以立法让司法人员侦察每一个家庭的生活?再者,“言论自由”是否容许性别歧视、族裔偏见或种族仇恨的言论公开发表或出版?诸如种种的议题都不是一个人或任何团体可以独断下所谓“正确”的答案的,而必须被带到公共领域,透过公共性的讨论,形成公共的判断。
但是,个人的审议与判断在公共领域内必然会跟其它的产生摩擦与意见的相左(disagreement),而有可能带出激烈的冲突。如何可能协调这些冲突,以达成某种共识?再者,共识预设集体的决断。公共领域如果是与国家权力脱离的,不是国家体制内的一种制度安排,那么,公共领域是否有正当性做集体的决断?这问题牵涉了公共领域的运作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关于公共领域之冲突与共识的问题,不论自由主义或者激进民主的论述皆承认,当代民主社会既无法避免,也不可能根除它们内在的种种冲突。再者,所谓的“共识”都是相对性的。其理由在于,现代的“世俗性”的社会,如上所阐释的泰勒的观点,不再可能援引任何“超越性之原则”,以作为共识之正当性的根据。现代社会必然“自我寻究与创设自我的根基”,如人民的共同意志、民族主义、或者,如法西斯主义的“国族主义”、极权主义的种族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等原则。
就当代自由主义者与民主论者而言,任何共同性或集体性的理念,如果落实在一具体的目的(如阶级、民族、或种族)而且被安置在一套历史哲学的目的论的架构上,便容易形成极权主义式的意识型态。因此,任何共同性或集体性的原则或理念不能是“实质性的目的”,
而必须是“规约性之伦理”(若用欧可秀的语言),或者是无实质内容的“象征”,或者如泰勒所提示的的“政治的同一性”。这种自由民主的共同性以人们相互承认的自由、平等与自主性为基础,并以法治为机制、为经纬构成一个宽松、处处留有开放之空间,但不缺乏一种“集体之机制”之认同的社会。简言之,自由民主社会的“共同性”乃形之于自由、平等、个人之自主性与法治的实践当中。
在这样自由民主的架构下,公共领域内部的意见的冲突的化解一方面透过“制度化”的途径,使之成为“日常之例行事物”(routinized)。在这里,公共领域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如前所阐释的,乃与国家之主权脱离,它所形塑的舆论构成“政府之监督”。但是另一方面,公共领域的舆论并不具政治决断的正当性。政治之决断是操在国家之主权者及其制度(如国会或各级议会)。因此,公共领域之舆论欲合法性之施用,必须在主权国家内之制度架构中。无可讳言地,在民主国家当中,公共领域的舆论以及因此形成的各种“社会运动”经常跟国家主权的政策与理念发生冲突,但民主的这种冲突、抗争是行之于权力之外,而且有制度作为冲突的缓冲点,这避免了致命的社会冲突。
当代之政治自由主义者,如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Thomas Nagel与Earnest Gellner,在思辨民主之共识的可能性条时,基本上乃以维系民主之宪政的完整性为前提。以Gellner的观点而论,民主社会中的共识若要有可能,必要的条件之一在于,公共领域中的争议皆承认基本宪政结构的有效性(或正当性),因此争议的议题不会是有关诸如宪政与民族认同的问题,而只是日常生活有关各种民生的琐碎议题21又如,罗尔斯所揭之“交迭性共识的理想”,这个理想预设人的道德性与理性,而跟只讲求利益妥协的策略性共识,即modus vivendi,区然而别。在演绎“交迭性共识”的理想时,罗尔斯一方面确立交迭性共识所形成的界域乃构成“共同性”;另一方面提示“作为公平之正义”概念的“政治性”;依此推论,民主共识的形成必须依据自由民主之宪政及其基本之制度安排,在其中,多元分歧之“合理之整全性学说”透过公共理性寻找“交迭性共识”时,必须限定在公共讨论所能处理与解决的议题上,即使涉及宪政结构的问题时,合理性的公共讨论只审议“既定之宪政的根本”而不是其结构本身及其根源性之问题,以确保其政治的整合与连贯性。这种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理念在Nagel的近著中也有所发挥。他在思考“公/私”领域(或彰显/遮掩)分际时,特别提出“忍隐”(reticence)的道德与伦理性的原则,其论证的主题在于,在民主社会中,任何公民应当学习有哪些事物是可以带进公共领域的讨论,并且藉由此讨论,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共识,以及有哪些事物是必须隐匿于私人领域的。举最明显的例子,个人的性生活与个人的生活态度是无法经由公共讨论而有定论。因此,媒体揭露公共人物的隐私,对于公共议题的讨论而言,毫无关系,也了无意义。以Nagel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公共领域所能容受的争议与冲突有其限度,有些争议,如牵涉广泛但抽象的文化、民族的认同、或者宪政之根源的问题,不是经由公共的讨论而可以得到满意的结论;在某些时刻,公共讨论这些问题,反而造成极端的对立,带来无法化解的冲突,甚至暴力。
上面所阐释的政治自由主义的论点,在思辨公共领域的规范伦理上,大致都将公共领域的运作限制在一定的宪政法制的架构内,是故,不是任何议题都可以进入此领域,受公共的讨论。这种论点基本上是为保持公共领域的完整性与文明性。
结论
公共领域在当前已构成自由民主政治的一重要部分。从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来看,公共领域的形成是跟国家主权分离的,如泰勒所解释,公共领域是“外于权力”的。是故,它的运作可以被视为国家主权治理权的正当性来源,特别是从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当人民主权的理念与实践与公共领域的运作相结合,公共领域的舆论与人民主权(或人民自治)的理念,加上人权的原则,遂奠定自由民主的基础。然而,从现代主权国家的发展来看,主权国家的治理权力与统治权力亦构成另一种“公共性”与“政治性”的理念。同时,在现代主权国家的扩张过程中,本为“外于权力”的公共领域亦被纳入国家主权的统治范围。从是观之,国家主权与公共领域就形成既分离又整合的紧张,这也带出了“公/私”界域的争议。两者之间产生的这种紧张与争议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促使西方民主化的动力之一。以当前的处境来看,只要自由民主的社会存在,就不可能完全铲除国家主权与公共领域的紧张,同时,随着科技的进展与社会经济的复杂化,公/私之间的界定也更难以确定,其中的问题也更复杂万端。在这篇文章中,个人以当代自由主义的观点,对于如何可能建立公共领域本身的规范,提供某些看法。
政治自由主义者所论证的这些观点是否令人信服?从激进民主论者的批判来看,这些规范性的理念,不免自我设限过度。这种限制容易扼杀公共领域原本具有的多元倾向。就此而言,公/私的界域应是浮动或动态性的,它不断会受公民的挑战,因此它理应是开放的。当涉及言论彼此激烈的争议时,取得共识的途径不全然是如政治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那么冷静、温和,而有时是充满暴烈的情绪。集团的利益与意识型态,也时常左右公民的判断。公民不因道德的设限,而能在争议中达成共识。共识反而常常是各方利益妥协的结果,或者取决于集团势力的强弱。这种批判观点揭露部分的政治现实。但是我们是否因此全然否定政治自由主义的伦理约束?
自由民主社会本身即呈现不稳定的性格,民主的公共领域充满不断的争议与冲突。共识亦难以求得。这样的民主社会当然时遇险境,如自由民主社会的自我否定,但也不是它的弱点。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自由民主社会时,我们对于民主的公共领域的共识就不一定抱着:无共识,民主就解体的态度。政治自由主义的约束性的伦理诚然是达成民主共识的要件之一,但是伦理性之原则必须通过在现实中的学习,才能成为具体性的实践原则,在这个地方正视现实主义的批判是有其必要的。
① 2002 《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汉纳‧鄂兰的政治思想》,台北:联经。P80-94,235。
② Benhabib, Seyla:1992 Situating the Self: Gender, Community, and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 orary Ethics. Oxford: Polity Press.p89-120
③ 就如Jean L. Cohen与Andrew Arato的评论:“如我们所见,鄂兰的公共领域是建立在古希腊或雅典政治的理想概念之模式上。令人困思的事,这种公共领域的政治因现代社会、国家与经济体系的兴起而式微;尽管她认为这种政治在现代性兴起之前已经消失。再者,鄂兰本人不受她这种‘式微之理论’所限制,她认为在现代革命期间,公共(领域)之自由(实践)的实验重现,虽然为时极短。这种论点好似说,自由与不自由在不同的,以及偶然的相关连的时间中进行。换言之,只有当历史的辩证静止的时刻,它往往(以及才有)可能。”(Jean L. Cohen&Andrew Arato,1992:210-1)
④ Oakeshott, Michael:1975 On Human Conduc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⑤ Oakeshott, Michael:1975 On Human Conduc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p166.
⑥ Cohen, Lean L. & Arato, Andrew:1992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p211-215.
⑦ Taylor, Charles:2004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p86
⑧ Cohen, Lean L. & Arato, Andrew:1992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p85.
⑨ Taylor, Charles:2004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p92.
⑩ 在回答什么是“共同之空间”这个问题上,泰勒做了如下的阐释:“牵涉于‘共同之空间’之人们,假设性地来说,从未有机缘会面过。但是他们在一个透过媒体——在十八世纪,即印刷媒体——而形成的讨论的共同空间中被联系,彼此宛如可以相见。书籍、宣传册子、新闻在受教育的公众当中流动、传阅;互通信息的主题、分析、反论…等相互交涉、交锋与批驳。它们广泛地被阅读,而且常常在面对面的集会中、在社交界、在咖啡馆、沙龙以及在更具有权威性与公共性的地方,如议会当中,人们彼此讨论它们。进由这种过程得出来的普遍性的观点,若有的话,就可以被接受是为在这新的意义下的舆论。”(Taylor,2004:84)
11 Taylor, Charles:2004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p92.
12 Taylor, Charles:2004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p94.
13 Taylor, Charles:2004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p97.
14 Taylor, Charles:2004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p94.
15 Taylor, Charles:2004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p87-89.
16Taylor, Charles:2004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p166.
17 Nagel, Thomas
2002 Concealment and Exposure an Other Essays. Oxford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8-29.
18 Guess, Raymond:2001 Public Goods and Private Good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86.
19 Guess, Raymond:2001 Public Goods and Private Good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113.
20 Nagel, Thomas
2003 Concealment and Exposure an Other Essays. Oxford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1.
21 Gellner, Ernest
1967 “Democra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Archives Europennes de Sociologie 8(1):47-70.p60.
原载: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6辑《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