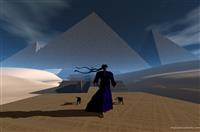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准确些说,是从1979年初到1990年夏,九号院的农村工作机构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迁。第一段即农委(国家农业委员会)时期,约两年,负责人先是王任重,后是万里,他们都是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本职来兼任;第二段为农研室(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时期,约七年,负责人为杜润生;第三段为清查和善后阶段,是属于九号院的尾声阶段,时间一年多。若论政策研究影响,尾声阶段可以说毫无建树,但对于这个院子里的人们来说,这段生活可谓刻骨铭心。在这短短一年里,这个院子里的人们,上至部长,下至普通办事员,几乎都经历了迷茫、纠结,甚至颇有些惊心动魄。若干人的际遇命运由此发生转折。谈到九号院,这段事情无法不说。这段时间的负责人,即清查清理和遣散分配的主持者,是王郁昭。
王郁昭是九号院的后来者。他调来的时候,我在秘书处工作,日常有所接触。后来,我做他的秘书四年,由此开始多有往还。在九号院的高级干部中,他是我最熟悉最了解的人。谈到九号院在中国农村改革中的兴衰过程,无法不谈王郁昭。谈王郁昭,也许则不应该只谈他在九号院的岁月。九号院是他本人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调来九号院之前,他长期在安徽工作。观照王郁昭跌宕起伏的职业轨迹,聚焦他在县里、地区、省里、九号院的从政经历,某种意义上也是管窥这个变革的时代。
初进九号院
九号院里的人们对于王郁昭并不陌生。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82年秋天,在年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当时他是安徽省委常委;1983年冬天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他又来了,这时候他是安徽省长。我在会议秘书组工作。会议报到时,我负责发放出席证。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召集座谈,或者会议分组讨论,我常常负责签到和记录。作为会务人员,当然见过王郁昭,但并没有什么交流。后来,他多次谈起这两次来京开会的情况,但对我则毫无印象。
更早进入九号院的同事,则与王郁昭有更多交往。1970年代末期,王郁昭是安徽滁县地委书记,他在万里支持下推行农业家庭承包,支持保护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那时,九号院就很关注王郁昭了。初期,九号院对于万里、王郁昭在安徽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中央高层否定家庭经营的政策意见,就是通过九号院发出;包括当时《人民日报》反对家庭承包的重要文章,也主要是九号院所出。那时候,九号院关注安徽,重点是关注安徽的滁县,王郁昭作为滁县地委书记,作为万里推进农村改革的急先锋,自然受到关注。1980年春天,万里调任北京,成为九号院农村工作机构的主要领导人。这时,高层政策意见纷争依然激烈,九号院曾数度召集内部座谈。王郁昭曾两次受邀与会,参加高层政策讨论,此外,他也曾安排地委秘书长或者县委书记来参加过会议。九号院也曾不止一次派员到他主政的滁县去实地调研。九号院的一些同事,对于王郁昭不仅有所知悉,有的还相当了解。
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存续七年,王郁昭是从外部调来的第二个副主任。第一个是陈俊生,原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当时,我们秘书处曾为他的到来做了不少具体工作,如准备办公室等。但是,任命后他一直没有来上班。大约两三个月后,又一个任命下来,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去了。再后来,他成为国务委员,曾分管农村工作。王郁昭任命后,也是迟迟没有上班,有两个来月未见其人。这在我们工作人员看来,似乎与陈俊生一样,有些不寻常。但是,到了秋天,也就是国庆节以后,王郁昭出现了。一般来说,人事变动都有突如其来的特点,包括突然宣布任免、要求马上交接到位。但是,陈俊生和王郁昭都不是这样,任命是“突然”的,但是并非“马上到位”。陈俊生任命后不上班,旋即又有新的提升,在九号院仅一掠而过,如神龙首尾不见,其发生原因和内部过程至今不得而知。王郁昭开始也没有上班,我们当时也有些议论猜测,但对真正原由不得而知。后来,他自己多次说到其中内情。
官员的调动,不论在京城还是在地方,历来是官场热点话题。官场中人关注议论此类事情,就如同乡下农民关注和议论田地里庄稼长势和收成一样。通常,人们议论的内容,首先是这个官员的基本情况,如何方人士,曾做过哪些职位之类;如果深入些,则会说到这个人的个性或者工作特点,有何业绩等;再深入一步,有知道更多情况者,则会议论这个人后面什么人在支持重用,甚至直接说是谁谁的人。在九号院的那些年,我常有机会随同一些部级干部出差开会,不同的人可能朋友圈子不同,但是聚会闲谈往往都有这方面内容。当时,对于王郁昭的到来,人们自然也免不了议论,但是没有人说得清楚是怎么回事。因为,官场消息的传播,往往是知情者不肯细说,肯说者又往往不知详情。也许正因为没有确切权威的消息,揣摩猜测才更加热烈。1987年夏天,王郁昭的任命对于九号院来说,显然是重要话题之一。这既是有关部门的工作议题,如准备办公室、配备车辆、安排住所等;也是工作人员茶余饭后的闲聊的话题。那时,我听到的一些议论说,其实九号院并不需要增加领导,王郁昭是上边“例外”调来的;还有的说,他是万里欣赏重用的人。
对于王郁昭本人来说,调来九号院是一个巨大意外。二十余年前,我刚给他当秘书的时候,他就多次说起过这次调动;现在,在他八十几岁的时候,仍然有时候会谈到当年调动的情况,若干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1987年6月,他率安徽省政府代表团赴欧洲考察,回国后在北京刚下飞机,省里来接的人就告诉他,中央组织部领导请他去谈话。第二天,他去见了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这位领导说:中央决定,他担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不再担任安徽省长。这位领导还说:“你对农村改革有贡献,熟悉农村工作,到北京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王郁昭表态:服从中央决定。同时,他对这种调动明显不解。在接下来的交谈中,他表示,现在更能理解鲁迅文章中关于“横站”的说法,因为需要随时准备转身应付来自背后的袭击。王郁昭借用鲁迅的话,表达了对调动的不满,意指有人中伤排挤。中组部部长显然无意与他讨论,更不回应他从鲁迅文章中引申的问题,而是说:“工作需要嘛”。晚年谈到这次与中组部长的谈话,王郁昭几次都提到了鲁迅“横站”的说法。后来,我在《鲁迅全集》中找到了原话。这段话出自鲁迅给杨霁云的信:“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3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王郁昭回到省里几天后,任免文件通知就到了,他马上与代理省长交待工作,并向中组部领导表示,在安徽工作四十年,对安徽有很深的感情,不想马上到北京上班,而是要在安徽再走走,去一些地方看看。大约三个月后,到了国庆节前夕,他到北京报到。中组部一位副部长和九号院一位副主任到机场迎接他。他到单位报到,并没有到九号院,而是去杜润生家里礼节性见面,算是上任。然后,他又回到安徽,过节后来到九号院上班。
王郁昭到九号院上班以后,开始几个月没有分工,如他在一本书中所说:“实际上是坐冷板凳”。这几月,他没有具体责任和实际职权,上班主要是看看文件材料,常规性地参加一些会议。当时,在九号院里没有分工的还有一个领导,是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职务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在九号院将近两年,一直没有工作分工,直至再度调走。大约是在1988年新年开始的时候,九号院的领导班子开会,让王郁昭分管九号院下属单位,主要是报社、出版社等。这些工作显然不是九号院的工作主流。不论分工前还是分工后的的情况都显现出,九号院对于他的到来,并没有需要,也没有准备。再联想到,他卸任省长并不马上到位,调令下来几个月后才进京报到。可见,中组部领导所谓农村政策研究的“工作需要”,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调动原因。或者说,让他到九号院,说是更好地发挥他在农村改革中作用,只是一种“说辞”而已。调动背后的真正原因殊为高深。
出任省长
如果说,王郁昭离任省长进入九号院是一个巨大意外,那么,把历史的镜头向后推拉得更长,王郁昭当初出任省长也是一种巨大意外。如果说得更远些,他的从政生涯本身就是一场意外。晚年,王郁昭谈起自己的经历,经常说自己本来是个教师,属于意外从政。
王郁昭是山东文登人,1941年,他15岁,在威海的一所教会学校读初中一年级。这年冬天,学校被日本军队占领,他辍学。家乡是抗日根据地,他回到家乡担任小学教师,后任校长。抗战胜利,他到威海市担任文教助理。内战爆发,威海解放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他参军。1947年冬天,随大军南下,进入安徽芜湖。渡江战役前,他被留下来,参加接管安徽大学,担任安徽大学军代表兼办公室主任。1954年,他就读中央马列学院,1956年毕业回到大学,先后担任政治教育系主任、教务长、副校长。“文革”中,大学停办,他被下放农村。1970年春,王郁昭被派担任县的领导,又五年,担任地区领导。农村改革破土之际,发生在安徽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在改革历史研究中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在这个过程中,万里作为省委主要领导,王郁昭作为地委主要领导,上下呼应,鼎力配合,推进了家庭承包的艰难突破。万里调离安徽以后,省委政策急剧逆转,一些地、县纷纷退缩。诸多地委书记中,唯独王郁昭不改初衷,艰难挺进。关于万里与王郁昭在安徽农村改革中的故事,本人在《农民的政治》一书中有专门介绍。
现在看来,1982年10月间胡耀邦视察安徽,也许对于王郁昭不久后出任省长有重要影响,但过程则难述其详。胡耀邦此行的重要目的,是考察安徽领导班子,因为来年春天,省委省政府将要换届。胡耀邦在合肥,先是与安徽省班子成员座谈了两天整,然后去滁县等地考察。在座谈会上,王郁昭第一次见到胡耀邦。会前,全体省委常委在会议室门口排好队,胡耀邦进来时一一握手见面,每个人自报姓名职务。当走到王郁昭面前时,未等他自我介绍,胡耀邦握住他的手说:“你就是王郁昭同志吧,你们推行联产承包是有功的。”王郁昭猜想,可能是有领导事先向胡耀邦介绍过他。王郁昭身材高大,在人群中易于辨认。座谈会后,胡耀邦视察滁县地区,王郁昭全程陪同并代表地委汇报工作。
在与省委班子谈话时,胡耀邦总书记提出了新班子的筹备原则。胡耀邦说:“第一条,能不能达成这么个协议,外面不进人来,你们退下去的也不调走。省委书记、省长外面不来人,要退下来的一个不调走,就在本省安排,可不可以办得通?第二条,怎么安排法?你们常委讨论酝酿成熟,然后走群众路线,中央审查决定。不是中央帮你们定,你们自己商量确定,上面派人帮助,你们自己定。文件讲了,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报中央批准”。(《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P286)。胡耀邦的这次谈话为安徽新班子奠定了基本格局,成为省委考虑换届的基础。可以设想,如果中央有意见从外边调进书记、省长,则省里的考虑就很不同了。关于工作程序,胡耀邦也讲得很清楚,就是省里自己商定,形成一致意见后报中央批准。有了总书记的这个谈话,省的领导班子筹备才正式展开。
胡耀邦从安徽走后,省里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班子来筹备换届工作。这是一个单独而特别的工作班子,由省委第一书记负责,封闭运行,直接与中央沟通。这个班子与省委常委会分立,讨论的事情不经过省委常委会。王郁昭本人是省委常委,但并不参与这个工作班子的筹备工作,也不知道新班子的筹备进展。后来,王郁昭是从非正式渠道得知,在关于新班子的方案中,他是常务副省长。在省内,关于新班子的传言猜测很多,新班子的构成很快就成为公开的秘密,人们基本上都知道在新一届班子中谁将是书记,谁将是省长,有人甚至传说新的书记、省长已经开始了工作。
1983年3月初,中央通知安徽省委常委全体到京,住进京西宾馆,等待中央领导集体谈话。王郁昭后来回忆说,刚到北京时,以为三两天之内就会公布班子并谈话。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在京西宾馆住了二十来天。期间别无它事,仅仅是等待。王郁昭在宾馆看看书,有时候出去看看朋友,或者逛逛书店。他们也猜想到似乎出现了新情况。3月26日,全体省委常委被接到中南海,参加中央领导的集体谈话。出席谈话的中央领导有万里、习仲勋、胡启立、宋任穷等,他们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其中宋任穷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万里主持了这次谈话。首先,宋任穷宣布新的安徽省班子。原方案发生颠覆性改变,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是新的人选。
省委书记黄璜是原方案中排名最后的省委常委;省长是王郁昭,在原方案中是常务副省长;其他职位也有很多变动。新班子与原方案变化如此之大,大大出乎意外。
新班子宣布后,万里、习仲勋、胡启立分别讲话。这些讲话的基本内容,一个是肯定现在这个班子是好班子,体现了“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一个是提出了对于新班子的要求,讲了新班子要注意的问题。万里首先讲话,也讲得最长。他说:“安徽的班子酝酿了很久,解决得最晚,为什么晚?慎重。”但是,万里并没有展开解释班子方案变化的过程,而是评点了新老班子里的部分成员,并特别对王郁昭的任用做了说明:“王郁昭同志,他文化水平高一些,研究了多次。因为也有人不大同意,理由是批邓当中有点问题。当时在那个条件下,不算什么问题。当时各省都发了通电,那是毛主席说要批邓的。中央认为,在那个历史条件下不算什么问题,不影响对他的信任和使用”。万里又说:“王郁昭同志有一个最大的贡献,在农村改革中带了头,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在凤阳县实行大包干到户,现在全国都搞开了,这一条是有很大贡献的。但是,不要骄傲,要闯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还要继续探索。搞社会主义,我们还在探索,我们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美国人韩丁最近到凤阳去看,回来写了一篇,说凤阳现在确实富了,但是一二年后可能就没有劲了,他还不大通。王郁昭同志有创见、有干劲,但不要满足。”接下来,习仲勋讲话:“首先声明,我对安徽的问题没有发言权。去年同万里同志一起研究安徽的班子,才了解一些。”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安徽带头搞农村改革,随后,也解释了批邓问题:“最近,邓小平同志在反映某一位同志问题的来信上做了批语:当时批邓,谁都得批。他的这个批语很重要。”习仲勋又说:“这个班子定了,但还会有各种议论,你们要有这个精神准备,我们还会接到许多来信,你们不要受外界干扰,首先你们班子要顶住。今后有这方面的材料,再来信,我们即一看了之,甚至看都不看。”王郁昭在若干年后谈到,他当时在会上听到中央领导人专门解释“批邓”的事情,非常感动,以至于当场流泪。后来,万里还对王郁昭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让他负起责任,奋力开拓安徽的工作。
为什么原定班子出现颠覆性改变?此中过程怎样?安徽的政坛,特别是王郁昭这些当事人,也都心存疑问。不少人在议论,提出推翻原方案的是万里和胡耀邦,并经邓小平的批准。这些仅仅是猜测。但不管内情怎样,这种结果本身外部冲击是很大的。其复杂深刻的影响既在当下,更在后来。对于王郁昭来说,文革中的“批邓”问题中央有了明确说法,心里无比欣慰。他觉得这个问题终于过去了。但是,后来正是这个问题的发酵和演绎,成为王郁昭从政生涯的“梦魇”。
在省长任上
从1983年3月到1987年7月,王郁昭担任安徽省长。
在省长任上,王郁昭先后与两位省委书记搭档。同时上任的省委书记黄璜,是新进的省委常委,也是班子中最年轻的成员。担任省委书记时四十六岁,比王郁昭年轻十岁。他原来是县委书记,提拔为地委副书记后即进中央党校学习,半年后学习尚未结束时即被任命为省委书记。在原来的班子方案中,他是排名最后的省委常委。这种不拘一格的官员任用,是八十年代的重要特点。那时,官员提拔的台阶尚未形成,越级提拔很常见。现在,这种提拔的台阶次序是很清晰的,比如不担任同级副职则一般不能担任正职;位置之间的移动轨迹也是基本清晰的,比如虽然是同级,一般先担任副省长才能担任副书记,或者先担任非省委常委的副省长再担任常委副省长。黄璜担任省委书记三年,因为受到省委秘书长案件的影响,被调任江西省副省长。随后,调来了新的省委书记李贵鲜。李书记原来是辽宁省委书记,也是一个年轻的省委领导。在谈到与两位省委书记的配合时,王郁昭说,不论是黄璜书记,还是李贵鲜书记,他们相处得都很好,个人间彼此尊重,工作上积极配合。
尽管王郁昭认为与省委书记合作很好,但是,在安徽省内省外,关于他和省委书记的关系,还是有不少议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王郁昭调任北京之前,我就听到过一些议论,说他在省里很强势。有一次,我随一位副部长到安徽调研,晚上一位农口负责人请吃饭,席间谈到了省长王郁昭。他说,在安徽,省委书记的批示往往被有关厅局长压住不办,要等省长王郁昭的批示来了以后再定怎么处理。现在,王郁昭聊天时,时常谈到二十几年前当省长时的陈年旧事,我曾问他是否知道这样的情况。他说:“不知道。即便有,也不说明我和书记关系不好。但是,这种情况在别的地方都可能发生,因为一个厅局长在接到省长或书记的批示时如何处理,要考虑很多因素。”王郁昭从来不认为自己与省委书记关系不好,不因为自己资历深、情况熟,就对省委书记不尊重。他说,那时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排位靠后,他的压力很大,工作特别努力。
关于王郁昭在省长任内的表现,社会评说自然不会一致。但总体上,他被认为是一个敢负责、有魄力的省长。特别是,在他离开安徽二十几年以后,省里上下议论到这些年的领导,不论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能做事的人”。常言说,做事和做官并不是一回事,善做官者未必能做事,能做事者未必善做官。在现代政治环境中,情况似乎更加复杂。党委和政府的混合领导是现在体制的重要特点,但是,不论从建政之初说起,还是从改革以来说起,党委和政府之间的领导功能界定,虽然原则上可以说明,实际上混沌不清。就运行机制来说,党委和政府的分工其实并不清晰,党政两个主要领导之间远未形成制度化职权配置格局。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如何做事和如何为官,其中是非成败,不论本人或外人都殊难分说。
在王郁昭担任省长后期,中纪委接到关于他的举报。举报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文革中间“批邓”的问题。八十年代中期,整党刚刚结束,文革中的表现仍然是领导干部考察的首要因素。举报中另外的问题,说他在用人上拉帮结派、工作上作风浮夸等。谈到用人问题,王郁昭说:“有人向上反映我的问题,说我在安徽势力太大,并说在地市、厅局的领导人中,我的学生就有八十四个。这个数字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我在大学教书十几年,学生非常多,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做什么领导。有人向中央反映:王郁昭在长江路上一呼百应。”长江路是省委省政府门前的一条马路,是省会的主要道路。王郁昭晚年曾多次感慨,对于此种非议,当事者本人是无法辩解的。
1987年5月,中纪委派出工作组到安徽。调查组到合肥后,先与王郁昭见面并说明来意,王郁昭表示积极配合,照常工作。文革中“批邓”问题说来话长,但并不复杂,且已经有过处理。1976年初,邓小平在短暂复出后再次被打倒,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王郁昭作为地区革委会主任,在省里一次会议上做了“批邓”发言。早在1978年,王郁昭就被告过,告状者曾是地委班子成员,说王郁昭“批邓”很积极,并且与“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有密切关系。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是万里,他看了信后曾派人查过,说没有问题。这个人就又告万里,把大字报贴到了省委大院。在这种情况下,万里决定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由省纪检委副书记做组长,省委副秘书长、公安厅副厅长做副组长。调查组调查两个月后,省委常委会听工作组汇报,王郁昭也被通知参加这次会。万里在会上说:“调查证明,这是诬告,诬告必须反坐,要承担责任”,会议决定把这个人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在滁县开了群众公开审判大会。王郁昭当省长后,告状在继续,其中既有原来的告状者,也增加了新的告状者,但大致上都属于过去地委的班子成员。这正是中纪委派出工作组调查王郁昭的由头。
但是,为什么这样旧事重提的举报能够再起波澜,而且构成巨大杀伤,似乎很难理解。小举报终成大气候,是需要条件的,问题的背后想象空间很大。一般来说,此类事情的背后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过往的官场积怨、当下的权力纷争、上层背景的嬗变等等因素共同作用,终于使过去的小事演绎为现在的大事。
王郁昭回忆说:“为了查我的‘反邓’问题,中纪委工作组约谈了很多人,去了几个地方,还查了当初的档案。我当时在省里的‘批邓’发言材料,大部分内容是从南京军区的一个批判材料上抄来的。后来,我就出访欧洲了,一回到北京,就被通知调离安徽。决定调离我的时候,调查还在进行,调查并没有发现问题。我走了以后,工作组就撤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外出调研的旅途中,王郁昭遇到一位当年的调查组成员。他对王郁昭说:“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调查组正在查,还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就突然把你调走了。我们觉得,总应该把调查搞完,有问题或没问题有个说法,然后再调人好说些。这样做事很是莫名其妙,搞得我们很不好下台。”
王郁昭对于这次调查和调动的不满是显然的,但是甚少表达。我还在给他当秘书的时候,有一次上班路上,我们在车里,不知道怎么聊到这次中纪委调查。他感叹到:“想想彭德怀,也就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了。功劳再大,也大不过彭德怀;案件再冤,也不能冤过彭德怀。我这点委屈,实在不算什么。党内斗争就是这样。”关于这次调查的结论,中纪委在两年多以后才正式告知他本人。
中纪委谈话
王郁昭离任省长后,中纪委调查组即风流云散。调查结果如何,查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结论,既无任何说法,也无人提及,更没有人找王郁昭谈话。从所谓组织原则来说,应该与被调查者见面沟通。王郁昭当然很关心这件事,但中纪委不找他,他也不便找中纪委,照常工作而已。
1989年秋的一天,也就是调查结束两年多以后,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不久,中纪委约请王郁昭谈话。与王郁昭谈话的是当年中纪委调查组负责人,已经是中纪委副书记。谈话就在中纪委所在地官园的一个会客室里,内容很简单。这位副书记说:“关于当年有人举报你的问题,我们早就查清楚了。但是,拖到现在才谈话,很是对不起。我们调查的结果,你没有问题,不需要做任何组织处理。谈话拖了两年,很对不起,向你表示道歉。”这位副书记又说:“调查的结果,你没有问题。你看是否需要个文字材料?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出一个文字材料。”王郁昭考虑了一下,说:“既然工作组已经查清了问题,还了我的清白,文字材料也没有什么必要了。我作为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接受群众监督,既然有人告状,那么就应该调查。”中纪委谈话后不久,国务院一位领导也找王郁昭谈话,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撤销九号院机构,让王郁昭负责清查处理和遣散分配工作。
发生在1987年夏的中纪委调查,到1989年秋才谈话,期间为什么要拖延两年多,王郁昭并不很清楚。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作霖曾对他说过一些情况。陈作霖是王郁昭的老同事、老朋友。1970年代中期,他们都在滁县地委工作,陈作霖是地委书记,王郁昭是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到北京后,两人同住在一个部长大院,时有见面。调查组回来后,中纪委内部曾考虑让陈作霖找王郁昭谈话。但是,陈作霖没有同意,说:“当初派工作组去查,我就不同意,因为告状信说的主要问题,我是清楚的,万里在安徽的时候就查清楚了。现在让我去谈话,不合适。”后来,中纪委内部又有人提议让另一个副书记与王郁昭谈,这位副书记也不肯谈。这样,就拖下来了。到了1989年秋天,再不谈话就要直接影响王郁昭的工作变动,所以,就安排了当初的调查组负责人出面。王郁昭认为,如果没有九号院里的机构撤销,不是让他来负责清查和善后,也许这件事就不再提及,当年那次长达两个月的中纪委调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中纪委调查可以说无功而返,但是,问题依然不好解释,当初为什么要派出调查组,调查组与王郁昭的调离有什么关系,似乎扑朔迷离。在一般人看来,也许可以说,是因为有人告状到中央,中纪委派了专门的工作组到安徽调查,然后,王郁昭被调到北京。那么,通常就会认为这与告状有关,或者与中纪委调查有关。但是,这种判断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告状已经持续数年,为什么前几年了无声响,这次却能兴师动众?更重要的是,调查没有发现问题,就决定调离了。可见,调动与中纪委调查关系不大。也许,这种调动背后有更深厚的意蕴,调动与调查并无内在的逻辑关联,甚至是一种虚假相关。
关于王郁昭调离安徽的原因,在后来若干年中,一些有关或无关的官员,在不同场合有所议论。因为工作环境的关系,我也听到不少说法,但对此事有较多了解,则是源于1991年秋天的一次出差。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带领一队人马在南方考察农业工作,
随行的有五六位副部长,还有几个省的副省长,王郁昭也参加这次了考察。五六天的行程中,有在农村的实地考察,也有座谈会,晚上则往往是休闲放松的安排,如酒吧闲聊、打牌或者打球等。我从一些茶余饭后的议论中有所领悟,1987年王郁昭的调离并非个别,而是涉及十几个人的系列调动,既包括一些省的领导人,也包括一些中央部委的领导人。一位来自东部的副省长的经历更堪玩味。当时,他是中部某省的省委副书记,四十五六岁,可谓意气风发。中组部领导突然找他谈话,说中央决定调他到东部某省一个地级市担任市长。这已经不是平级调动,而是直接降级降职。他问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回答说不是犯了错误,他问那为什么这样调动他,中组部领导的回答是:这是工作需要,你年纪轻,要能上能下,多多磨练。就这样他就当地级市长去了,当了两年市长,他又当市委书记,当了一年市委书记,他又当回了副省长。他是王郁昭的好朋友,考察期间常有聚谈。这些调动的当事人,或者其他一些相当层次的官员,在议论这波官员调整时,往往要说到当年那场中国政界的大地震。年初,胡耀邦总书记突然去职。随着总书记和总理的变动,万里的位势也有变化。高层政坛的剧变也直接影响到部门和地方。个中情势可谓玄机深重,不仅外界人士难以明察,即便这些被调动的当事人,虽然身为高级官员,也往往不明就里,甚或一知半解。至于笔者本人,因为经验和视野的局限,更不敢妄作解人。官员谱系的演变机制或者说运作逻辑,也许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隐秘的部分。因为公开透明的竞争性选举无足轻重,封闭的内部博弈则显得纷纭复杂和迷糊朦胧。要窥探和展示其中机理,委实困难重重。这也正是中国政治研究的艰辛所在。
谈到当年的调离,虽然与中纪委调查有关,但是,王郁昭从未抱怨纪检部门。后来,我若有所悟。纪检行动根本上是政治过程,而非法律过程。作为政界要员,被举报或者告状总是会有的。但是举报本身并不重要,或者说,举报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举报经常发生,重要的是查或不查;问题经常发现,重要的是处理或者不处理。若翻转角度看,则有另一种运作轨迹,不是因为有问题而决定处置,而是因为要处置而寻找问题,问题本身并非决定性力量。这其中不同因素互为变量、互为因果,演变机制和配置艺术可谓出神入化。在西方,这种出神入化的决定性力量首先是选举;在中国,这种决定性的力量是什么,或者说各种力量的逻辑关系如何展开,于探究者而言是莫大挑战。
王郁昭的遭际常常使我陷入迷惑。在中国,政治与法治的关系何其复杂,“法治”往往成为政治之一部分。一方面,官员被处理是因为违纪违法,违法和被处理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另一方面,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现实生活中违法违纪者甚众,且官员变质并非一日之功,有关部门也非完全闭目塞听,但是,是否查办、如何惩处,则取决于政治的考量,而非法律的严格沿用。法治承认的是法律的权威,而法律本身是确定的,文本清晰、程序明确、标准统一,司法过程不过是技术性过程。但是,政治过程则是不确定的,区敌划友,形格势禁,较量博弈几无定则。用卡尔•施米特的话来说,政治无非就是处理极端的冲突以确立秩序,但是如果任何冲突都需要纳入政治过程,那么政治也就被湮灭在无尽的琐碎之中,而无法真正去面对根本性问题;所以,人们需要不断地将已经在政治中成熟的规则通过法律、规范的方式确定下来,以后再有类似的问题就直接依照现有的法律或者行政规范加以处理。但是,如果法律成为政治的武器,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使用或者不使用,那么法律自身的权威将无法自立。在一些现实的案例中,被惩处者往往忏悔“跟错了人”,而不是“做错了事”,似乎暗示了政治与法治之间的微妙关系。(上)
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本文是作者为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