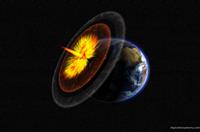内容摘要: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附。我们需要对“谁来启蒙”、“启蒙谁”、“拿什么启蒙”、“怎样启蒙”以及“启蒙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进行反思。传统中国对“启蒙”的固有理解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了三种路径的“启蒙”:“权势型”、“知识型”和“救亡-革命型”。这实际上意味着国人把太多的任务加诸在“启蒙”这根“树枝”上,使得它有无法承受之重,以至于远离了“启蒙”自身的逻辑。基于此,为使“启蒙”持续“运动”下去,首要之举就在于剥离附加在“启蒙”之上的东西,把属于“启蒙”的还给“启蒙”,使它真正拥有理性的翅膀。
近代中国启蒙问题是一个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沉重的话题。它之所以成为问题,大概有两个因素:一是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强烈刺激,一是西方思潮纷至沓来促成的觉醒。这样背景下的近代中国启蒙问题,注定会背上双重的包袱:一方面要求洞察近代中国社会所谓的启蒙问题到底蕴涵了什么?另一方面,借助西方思潮来拯救近代中国的启蒙问题,到底意味着或者将引发什么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很难给出最后的答案。但是,带着这些令人忧思的问题,我们可以去反思关于启蒙问题的更为广泛的问题。
谁来启蒙?
近代中国启蒙问题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启蒙主体是谁?如果启蒙主体明确的话,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谁赋予他们启蒙的权利以及权力?
关于启蒙主体,有一种不证自明的意见,那就是:谁掌握了知识,谁就是启蒙的主体[①]。顺着这种流行的意见来看,近代中国所谓的知识阶层,无疑是首当其冲。就发生的事实来说,他们中确实有不少的人,比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胡适,陈独秀,鲁迅……,担当了这样的角色。但是,启蒙主体的具体行动并不能代替或取消启蒙主体的行动合法性。因此,追问启蒙主体的动机是首要的任务。
启蒙主体的动机大概有两面:一面是内在的伦理动机,一面是外在的功用动机。如果借用“三不朽”即立德、立言与立功[②]来考察的话,他们的伦理动机就体现为“立德”,功用动机就体现为“立言”与“立功”。就“立德”而论,近代中国的知识阶层,很难抽象地奉为“道德”的楷模。这并不是说,他们自身的“道德”不足为鉴,而是说,近代中国社会本身还面临着一个“重塑道德”的问题。梁启超关于公德与私德的讨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由此来看,启蒙主体的主导性动机就是功用动机即“立言”、“立功”。正因为这样,他们才频频地创办刊物,发表文章,建立机构,从事教育,四处演说。我们可以说,是他们自己赋予了自己启蒙的权利。
不过,自己赋予自己启蒙的权利,并不能取代另一个关键性问题:启蒙的权力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可拿社会时势、国民的呼唤或者“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来随意搪塞。就近代中国的泛泛之众而言,长期的难题不是要启蒙而是要摆脱困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暗含的问题首先是“兴亡”而不是“启蒙”。“困穷”与“兴亡”问题,实质是社会发展与秩序问题。社会发展与秩序问题是知识阶层要回应的问题而不是他们所能够解决的问题。谁有可能和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权势阶层。由知识阶层赋予自己启蒙的权利,一定意义上已经表明他们力图超脱于权势阶层的控制。或者说,知识阶层在履行启蒙的权利时,他们必须要应付权势阶层对启蒙的干预。在这些凭借“知识”敲开了权力之门的权势阶层看来,知识是被权力操纵的奴隶。因此,他们不会容忍知识阶层自由地传播知识。知识阶层要么向权势阶层屈服,传播后者所谓的“知识”;要么同权势阶层抗争,独立地宣扬自己所谓的“知识”。就事实而论,近代中国独立的、公共性的知识分子并不存在。他们不是超然于权力,而是在权力的影响下,制造与传播知识。这里实际告诉我们,知识阶层行使启蒙的权利是在权势阶层的权力庇护下进行的。知识并不高于权力,权力是宰制知识的。启蒙的权力实质上是属于权势阶层而不是知识阶层。启蒙的权利与启蒙的权力,并不是在一个平等的、开放的、自由的平台上对话。
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不论从“知识”本身还是从扮演的角色而论,近代中国社会的知识阶层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都是“在一个共同体内执行相似角色的……都被要求或相信具备同等的知识。也并不认为他们在角色所需要的其他个人特征方面完全一样。对个体间不平等的承认,导致了执行某一类角色的人之间出现社会地位的初步分化。于是,那些在知识上处于劣势的人,像那些在技能、健康、创造性或毅力方面处于劣势的人一样,不会像那些具有卓越才能的人那样被委以重任。”[③]这就是说,近代中国的知识阶层还面临着社会组织化或社会分化的问题。
启蒙谁?
近代中国知识阶层在“知识”的逻辑上,承担着启蒙的权利。而权势阶层在“权力”的逻辑上,决定着启蒙的权力。这种不对等的地位,自然影响了彼此所认定的启蒙对象。
依据“知识”的逻辑,决定一个社会中被启蒙的对象应是“知识”。因此,“有知”启蒙“无知”和知识不足的人。我们姑且回避“知识多少”如何衡量的问题。只需追问这样两个问题:“无知”和知识不足者作为启蒙对象,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还是单方面意志的决定?社会上哪些人是“无知”和知识不足者?就第一个问题来说,很难说是经过自由讨论的结果。这就造成了启蒙主体与启蒙对象之间的疏离与隔膜。很多时候情形是这样:启蒙主体所认定的启蒙对象对启蒙无动于衷,他们关注的不是启蒙而是如何成家安身。启蒙成了启蒙主体的一种“自言自语”。用通俗的话说,近代中国所谓的“启蒙”,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所谓的知识精英自我的文化表演而已。在启蒙主体接收了外来思想的时候,他们作为启蒙主体的优越感将会剧增。结果是,他们无限扩大启蒙对象,权势阶层或多或少进入了他们启蒙的视野,尤其是他们认定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在于政治革新之时。
然而,从“权力”的逻辑看,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举动已经“出轨”了。他们试图以“知识”去启蒙“权力”。一个根本的要害在于,权势阶层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知识,一种垄断的、具有暴虐倾向的知识。因此,权势阶层自己需要的不是启蒙而是如何控制启蒙。在他们看来,除了他们自己,其他所有的人都需要启蒙。以“权力”为诱饵的科举制度,实质上就是权势阶层用以启蒙民众的工具。
显然,在谁需要启蒙的问题上,近代中国知识阶层与权势阶层存在着冲突和一致。在冲突可以容忍的限度内,他们会把启蒙的目光一起瞄准社会的下层。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社会的下层被知识阶层与权势阶层毫不商量地、毋庸置疑地塞进了启蒙的“囚车”。他们都把自己从“启蒙对象”中优先地提取出来,放置在他们选定的“启蒙对象”之上,以“知识”的优越与“权力”的威严成了启蒙的“训导员”和“判官”。不过很多时候,知识阶层“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鲁迅笔下麻木的看客和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④]即是证明,而这恰恰又是权势阶层所希望的。
拿什么启蒙?
在启蒙的主体和启蒙的对象上,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的普通民众是完全“失语”了。这事实上,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启蒙的内容上有什么发言权。
我们如果不严格区分的话,近代中国知识阶层与权势阶层都将把“知识”作为启蒙的内容。不过,在对“知识”的理解上,他们遵从不同的逻辑,因而给“知识”规定了不同的内容。不管是“什么”知识,启蒙对象都是不能决定的。也就是说,前者很少根据实地的调查来决定“知识”的内容。
从知识阶层来说,他们把自己所掌握的、知道的和读到的知识,一古脑儿兜售给了被启蒙者。他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这些知识是否符合启蒙对象的需要、兴趣、利益和价值。毋宁说,他们是在把自己的爱好、价值、理想强行输入这些“干涸”的头脑。比如说,他们认为,近代中国变革的出路在于塑造“新民”,他们就大量地输入新思想。这些不被理解和吸纳的新思想,不但无法让被启蒙者如沐春风,反倒引起了权势阶层的恐慌。知识阶层为了切实使普通民众明白知识,他们有时还需要不断地庸俗化知识,他们必须要顾及中国社会的“乡土性”。从权势阶层的逻辑来看,他们也掌握了一套知识,一套训练权力之奴仆的知识。他们需要的不是独立自主的民众,而是乖巧顺从的奴仆走卒。他们灌输的不是自治意识,而是权威意识。但是,从知识的逻辑来看,启蒙不是愚民而是使民觉悟和得以解放。这些明显冲突的结果,一方面损害了启蒙本身,另一方面践踏了知识。
权势阶层要求知识阶层按照他们的逻辑来传播知识,启蒙民众。崇尚平等、自由、民主的知识阶层,如果不向权力低头的话,就必须把自己封闭在书斋或者被关押进大牢。如果向权力投诚,知识阶层就要从权力的角度来过滤知识。普通民众在生存的压力下,他们不仅不理睬甚至会抵制这些所谓的“知识”。这就是说,尽管他们没有决定启蒙内容的权力,但是他们可以采取不接受、漠视或反对知识的立场。既然这样,陈独秀等人对清朝帝制推翻后无数民众满脑子还是皇帝意识的现象感到奇怪,就不足为怪了。可以说,无数普通民众不只是处于启蒙的边缘,实在是在启蒙之外。
怎样启蒙?
如同普通民众无法决定启蒙的内容一样,他们也无法决定启蒙的手段。近代中国社会所能运用的启蒙手段到底有哪些呢?
就权势阶层而言,依靠帝国体制,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一套灌输、传达、送呈、宣讲体系。这套体系主要是输送诏令、政府文件等。除此而外,还有一套由帝国控制的教化体系,主要载体就是官方教育机构。从正统的观点来看,这两套体系是互相支援的,是正式的知识(信息)传播体系。这种传播体系不存在开放性、平等性。它是权力的注脚。
近代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一个知识(信息)泛滥的社会。由权势阶层所控制的正统的传播体系无法完全左右知识。处于变革之中的知识阶层,大量利用新兴的传播载体进行启蒙。报刊、学堂、学会,是他们经常利用的工具。其中,报刊是最为显眼的。近代中国社会层出不穷的报刊,多数出自他们之手。最著名的代表大概要数梁启超、严复、胡适了。报刊成为近代中国最富活力的舆论阵地。但是,铺天盖地的报刊并不能掩盖它给启蒙带来的问题。办刊的宗旨与定位,报刊的撰稿人与编辑,报刊的运作机制,报刊的读者群,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反省的。报刊的宗旨与定位,必须要处理与正式传播体系的关系。近代中国为什么有不少的报刊忽兴忽灭,为什么会出现数量众多的报刊,就在于这种关系的处理。撰稿人与编辑,决定或选择了启蒙的内容。报刊的运作机制关系它的发展,一定程度限制了启蒙的深度。报刊的读者群,影响了报刊的走向,制约着启蒙的广度。
在权力主宰下的正式传播体系,权势阶层能够将他们自己的意图贯彻到穷乡僻壤。由知识阶层主导的报刊,知识往往局限在城市,而且还多是城市中年轻的求学者。当这些拥有知识的人返回乡村时,他们带去的往往是几个新鲜的名词。于是,“咸与维新”也从赵太爷口中传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一样在胡适的家乡流行。乡下人接受的不是什么自由,
而是玩起了城里人早就流行的麻雀纸牌。对于依附性极强的村民来说,他们要的不是知识阶层所谓的启蒙而是生存、生活。这是否意味着通过报刊等进行启蒙的知识阶层,他们不熟悉普通人的生活,不熟悉民情民俗,他们只是在理想的感召下进行一种无法回应的梦呓?当另一个担当启蒙任务的革命阶层出现时,他们发现鼓动普通民众去革命争自由,根本行不通。当他们说发财,普通民众却非常欢迎。[⑤]这实际上,预示着知识阶层所进行的启蒙将是一场悲剧。
启蒙是反光镜,还是探照灯?
当启蒙问题被北京大学的一大批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教授注意时,胡适认为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⑥],是一场“新运动”。“该运动有三个突出特征,使人想起欧洲的文艺复兴。首先,它是一场自觉的、提倡用民众使用的活的语言创作的新文学取代旧语言创作的古文学的运动。其次,它是一场自觉地反对传统文化中诸多观念、制度的运动,是一场自觉地把个人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是一场理性对传统,自由对权威,张扬生命和人的价值对压制生命和人的价值的运动。最后,很奇怪,这场运动是由既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又力图用现代新的、历史地批判与探索方法去研究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人领导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一场人文主义的运动。”[⑦]反观西方,它以文艺复兴为导火线,演化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它是“遍及欧洲各国(和美国)的一场思想变革运动。其根本目的是把人们的理性从偏见和迷信(特别是从被确立了的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将之用于社会和政治改革事业。所有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坚定地信奉进步。”[⑧]
如果不严格区分的话,近代西方启蒙运动与近代中国“启蒙问题”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就是都要以公认的传统为批判对象,都将运用“启蒙”这面“反光镜”来反思自我、反思过去。不过,西方的这面“反光镜”是由“机械哲学、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⑨]三种材料铸造成的。反观近代中国,我们无法寻找到这样的哲学基石。但是,我们除了拥有“中国的传统”这面镜子外,还有“外国文化”这面镜子和“一面更大的镜子,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⑩]
尽管它们都把“反光镜”聚焦在“传统”之上,但是,显著的差异在于前者的“传统观念中有一种主导性的启蒙运动模式,那就是使启蒙时代成为坚信理性、进步、个人主义、普遍友爱和人道主义价值观的时代的模式。”[11]传统中国的观念系统中没有这样的“启蒙运动模式”。然而,它却拥有一种生生不息的王权主义观念。
知识分子都是二者的主体。但是,西方知识分子“分析政治传统、社会和经济结构、看待过去的态度、人性思想、知识、科学、哲学、美学和道德理论,以及最重要的基督教的教义和机构”[12]。“最重要的是,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相信并试图实践这样一种思想:知识应该为人类服务。他们希望知识产生实际的结果:新的机构、新的实践、新的技术,所有这些都应促进普遍的人类进步。”[13]近代中国知识阶层双手拿着“中国的传统”与“外国文化”两面镜子,面对的是“沉默的大多数”这面大镜子。他们最主要的任务不是像西方那样“推翻旧有结构,重建人类社会、机构和知识”[14],而是“唤醒”[15]这“沉默的大多数”。虽然他们对“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16]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但是“并不真正尊重民众改善自己的能力,以及民众应对由教育和文化提供的机遇、挑战的能力,他们倾向于把民众当作潜在的病人,而不是思想的听众”[17]。之所以这样,除了他们以“先知先觉者”自居外,根本的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填鸭式文化”,而他们又不同程度鼓励“填鸭式文化”[18]。由此我们发现,西方的启蒙还在于它是一盏投向现实社会与人类未来的“探照灯”。它使“知识服务于人类进步”这种价值观“在欧洲各地推动了社会、政治、教育、经济和思想的改革”,“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引发了现实的改革”,“将欧洲世界带入了现代”。它用“光明”即智慧“引导人类更趋智慧和完美”。[19]
按照胡适的说法,中国的这场运动“被看成是预示着并指向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新生的运动”[20],也就是说,它也被视为照亮中国社会前进的“探照灯”。但是,当他说“中国文艺复兴的使命”在于其“领袖”知道“需要新语言、新文学、新的生活观和社会观,以及新的学术”时[21],实际上这盏灯就被牢牢地擎在他们自己手中,作为“唤醒”普通民众的工具,以至于它并没有沿着民族性、群众性、持久性的要求“运动”下去。
基于以上的差异,西方社会已在启蒙运动留给他们的遗产的范畴中继续他们现代的讨论,研究“如此众多富有启发性和迷人的资料”[22],而中国社会还在争论到底要不要启蒙、如何启蒙、启蒙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
传统中国对“启蒙”的固有理解[23]以及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困境与压力,注定了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会表现出自己的特点。
近代中国社会除了存在前面所说的“权势型”和“知识型”启蒙外,还有第三种即“救亡-革命型”启蒙[24]。三种启蒙的中心目标是不一样的:“权势型”启蒙解决的是利益保障,“知识型”启蒙解决的是国民觉悟,“救亡-革命型”解决的是阶级翻身或身份解放。它们彼此之间有着程度不同的冲突。但是,它们又存在程度不同的关联性、依赖性与妥协性。这充分表明近代中国启蒙问题的复杂性。更有意义的是,表明我们把太多的任务都加诸于“启蒙”这根“树枝”上,认为可以“毕”近代中国社会问题解决之“功”于“启蒙”之“一役”。
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启蒙“争论的焦点是富强、民族振兴或民族尊严的重建的条件”,成为“各种各样的救世方案或使中国摆脱可悲困境的药方的支配权的争夺”[25]战场。它当然就“不是纯粹的思想运动学术运动,而是把理论、行动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运动”[26]。总之,中西方“启蒙”遵循完全不同的发展逻辑:“在西方,启蒙主义是要解决个人的解放或个人的自由问题,在中国,启蒙主义要解决富强的问题;在西方,启蒙主义是个人主义的,而在中国,启蒙主义从其最根本的追求上,就是集体主义的。在西方,民主与自由被视为最后的价值,理性王国的根本的特征;在中国,民主与自由被视为实现富强的条件或工具。”[27]
遗憾的是,承载了如此多使命的近代中国启蒙这根“树枝”最后被“压弯”了,以至于每一种启蒙都远离了它本身的逻辑,我们无法辨清启蒙的本来面目。这大概就是国人们围绕着启蒙争论了若干年的根本原因。今天我们再来反思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之所以看得比较清楚,是由于我们抽身事外。今天我们面对的启蒙问题不再是启蒙应该如何,而是如何深化启蒙。如何深化启蒙,与其引入或创造新思想,不如花大力气去解除旧思想的束缚,或者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各种事物。当前,首要之举就如同“把灯熄掉,以便看清灯泡”一样,把那些附加在“启蒙”身上的东西一一剥离,然后把属于“启蒙”的还给“启蒙”,使“启蒙”真正拥有理性的翅膀,在属于自己的天空振翅飞翔。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①]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基认为:“事实上,每一位执行某项社会角色的个体,都被他的社会圈子认为具有或者他自信具有正常的角色执行所必不可少的知识。如果缺乏这些知识,就认为他在心理上不适合于担任这一角色。获得这种必要的知识是通常被称作‘教育过程’的准备阶段中的一部分,并且是最重要的部分;直到认为他已经获得这些知识(也包括角色所需要的其他个人特征),他才成为他正在为之做准备的角色候选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郏斌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8页。
[②]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原文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关于“立德”,唐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关于“立言”,据《旧唐传一六〇·韩愈传》:“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而“立功”古时主要指的是战功、军功,后引为事功。
[③] 弗·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第18页。
[④]王小波这样写道:“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17页。
[⑤] 原文是这样的:“中国人听到说发财就很欢迎的缘故,因为中国现在到了民穷财尽的时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贫穷;因为发财是救穷独一无二的方法,所以大家听到了这个名词便很欢迎。发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发财便可救穷,救了穷便不受苦,所谓救苦救难。人民正是受贫穷的痛苦的时候,忽有人对他们说发财把他们的痛苦可以解除,他们自然要跟从,自然拼命去奋斗。”《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3-714页。
[⑥] 认为中国存在与欧洲类似的文艺复兴的说法,大概始自梁启超。在20世纪初,他认为清朝“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新民丛报》(1902年)。后来,他又说:“前清一代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相类甚多。……清代何故与欧洲之‘文艺复兴’异其方向耶?所谓‘文艺复兴’者,一言以蔽之,曰返于希腊。……我国……所谓复古者,使古代平原文明之精神复活,其美术的要素极贫乏,则亦宜也。”《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92-93页。学界一般认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是开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比如何干之先生认为:“‘五四’启蒙运动,可以说是始于《新青年》的初刊,而终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但是,胡适却认为肇始于1917年,标志性事件是北大学生创办《新潮》杂志。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欧阳哲生、刘红中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⑦]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81页。
[⑧][英]戴维·米勒等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页。有的学者指出,“启蒙运动是用来描述18世纪的一场重大思想、文化运动的术语,这场运动的特征是深信人类知识能够解决现存的基本问题”。[美]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刘北成、王皖强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康德对“启蒙运动”有一个经典的界定:“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第22页。有的学者认为欧洲历史上存在过两种启蒙运动:一种是特指18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另一种是新指19世纪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的无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高放:《启蒙运动的回顾和重新启蒙的省视》,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2期,第4页。这种说法并不为学界普遍接受。但是,它说明启蒙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带有普遍性。
[⑨]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机械哲学、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三股思潮奠定了启蒙运动思想结构的基础。”[美]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第12页。
[⑩]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第18页。
[11][美]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第13页。
[12][美]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第11页。
[13][美]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第13页。
[14][美]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第11页。
[15] 孙中山在“遗嘱”中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选集》,第994页。
[16]《<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王栻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页。严复在《<原强>原稿》这样写道:“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三民”有时指的是“民智”、“民德”和“民气”。如:“所可悲者,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虽有圣人用事,非数十百年薄海知亡,上下同德,痛刮除而鼓舞之,终不足以有立。”《严复集》第1册,第9、14页。
[17][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18]弗兰克·富里迪认为:“鼓励填鸭式文化的并不是真正的民主精神。包容和肯定政策很少转化为对聪明公众所具有的智慧的真正尊重”。《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第130页。
[19][美]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第13页。
[20]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81页。
[21]具体来说就是:“他们需要新语言,不只是把它当作大众教育的有效工具,更把它看作是发展新中国之文学的有效媒介。他们需要新文学,它应使用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使用的活的语言,应能表现一个成长中的民族的真实的感情、思想、灵感和渴望。他们需要向人民灌输一种新的生活观,它应能把人民从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能使人民在一个新世界及其新的文明中感到自在。他们需要新学术,它应不仅能使我们理智地理解过去的文化遗产,而且也能使我们为积极参与现代科学研究工作做好准备。依我的理解,这些就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使命。”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82-183页。
[22][美]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第13页。
[23]在中国,“启蒙”的固有含义是“使初学的人得到基本的、入门的知识”。著名学者高放教授认为,启蒙的“本意是启发愚蒙,打破欺蒙,揭除蒙蔽,开导蒙昧,使人茅塞顿开,幡然醒悟,通晓事理,自觉行动。”见《启蒙运动的回顾和重新启蒙的省视》,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2期,第4页。传统中国重视启蒙的直接表现就是编辑蒙学教材、建立蒙学馆。在西方,“启蒙”是法语lumières的英文翻译,意思是“光明”。Lumières在18世纪的讨论中经常出现,它既指一种思想主张,又指那些正在阐发这一思想的人。[美]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第11页。有的学者认为,启蒙“无论从这个词的中文意义还是西文意义上,都有教化、教育的意思。通过教化、教育,使人达到一种自立、自主并意识到平等的状态。这就是启蒙的原本意义。因此,启蒙概念的原始的含义是教育方面的”。胡传胜:《观念的力量——与伯林对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24]一般认为,启蒙是知识阶层的责任。基于传统中国社会对“启蒙”的教化式理解,权势阶层为了统治的需要,自然非常倚重这种启蒙。在美国学者舒衡哲、中国学者李泽厚等“救亡压倒启蒙”认识下,救亡、革命与启蒙是大有分殊的。有学者认为,救亡促启蒙,实际上把救亡作为启蒙的途径。见金冲及:《救亡唤起启蒙——对戊戌维新运动的一点思考》,《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392页。孙中山认为,要传播欧美民权思想,建立共和国的基石即教育事业、兴办实业和地方自治,其手段都是革命。他说:“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4-315页)“以上三种(教育事业、兴办实业、地方自治),固是改造中国的要件,但还不能认为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是什么呢?在兄弟的意思,只有革命。”(《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5页)。由此看来,在“知识型”和“权势型”启蒙外,还存在一种“救亡-革命型”启蒙。“救亡-革命型”启蒙与“知识型”启蒙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再加上学界已经对“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所以前面并未论述。比如,张光芒:《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高放教授以下的话,可以说印证了作者关于启蒙路径的划分:“事实上从‘五四’时期开始至1949年,我国的启蒙运动一直是兵分两路,沿着两个轨道并行发展:一路是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直在进行西方那种民主、自由、人权、个性解放等等的启蒙;另一路则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直在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工农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的启蒙。这两路兵马在救亡、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有过联合与合作。”《启蒙运动的回顾和重新启蒙的省视》,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2期,第6页。
[25]胡传胜:《观念的力量——与伯林对话》,第133页。
[26]胡传胜:《观念的力量——与伯林对话》,第106页。
[27]胡传胜:《观念的力量——与伯林对话》,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