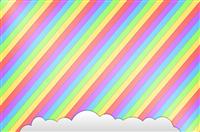
论文摘要 民众对辛亥革命的正面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认为清朝的气数已尽,而作为气数已尽的表征之一,则为新政在下层社会引起的混乱。人们对于清廷现代化改革的不满,有时竟然化为对革命的同情,下层社会其实并不明白,革命和新政在变革的大方向上其实是一致的,民众对于新政的不满,实际上预示了他们对革命后新政权的态度。但是,民众对于清朝即将垮台的普遍认同,不仅导致了社会异己力量的空前活跃,更重要的是销蚀了中上层社会甚至统治者的信心。下层社会基本上将革命视作“反清复明”和改朝换代,虽然他们也体味出革命党行为中具有某些新气象,但还是期望“新朝”能带给他们某些惠政,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争取减租减税,某些地区的农民甚至乞灵于革命党的“新名词”。然而,革命党人在减轻民众负担这个要害问题上无所作为,而在某些表面的社会改革方面却颇为热衷。强行剪辫的普遍推行,几乎引起了下层社会一致的反感,轻易地将民众推到了地方实力派一边。民众的不满和背离,在革命后袁世凯举起屠刀时,放大了地方实力派对革命党的背弃效应,造成了表面上看起来还具有相当实力的革命党雪崩式的瓦解。
无论从那个角度说,辛亥革命都是一个分界线:作为正统史学界的公议,辛亥革命划开了帝制和共和两个时代;而在有些人的眼里,它却标志着无序和动荡的开始。中国近代历史上这非同小可的一笔,虽然在当时看来似乎纯粹是由革命党的精英们涂抹出来的,但于被视为“后知后觉者”的普通百姓其实同样有着很大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老百姓的态度事实上影响了这场革命形状,甚至决定了它为什么日后会有那么多的不尽人意之处。也可以说,这场某种意义上算是精英革命的革命,其意义越是深远和重大,那么就越是有必要讨论一下当时民众对它的反应。
一、“气数说”与变革的悖论
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告诉我们,辛亥革命得到了劳动群众的普遍而热烈的拥护。除了一点必要的夸张之外,应该说这种说法并无大错,尽管我们可以在当时的史料中找到热烈拥护的场面,也可以发现冷漠旁观的人群,但下层老百姓对革命表示强烈反感的确实也非常少见,应该说,这对于一场以西化取向为目标的变革来说,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在这场革命爆发前十几年,康梁变法失败的时候,老百姓还普遍地将这些改革志士视为汉奸。到目前为止,我翻遍了所能看到的史料,也仅有一条说在江苏靖江的小县城里,一位卖五香豆的老太婆,对这场革命发出了一声“皇帝江山从此送掉”的叹息,还因此被警察拘押了半晌。[1]虽然沿海和城市的平民百姓对革命反应热烈,内陆和农村要相对漠然一点,但很少有人对那个统治了中国260年之久的王朝的垮台表示惋惜。
20世纪最初的十年,是清王朝统治威信大面积坠落的十年,对于那些对政治并不敏感,甚至对革命党人卖力地宣传不甚了了的下层百姓来说,如果说他们也有一些改朝换代的预感的话,那么恐怕更多的来源于历史习惯。在多少懂得一点历史知识的老百姓眼里,一个统治了260年的王朝,无论如何也是该寿终正寝了。一时间,有关清朝气数已尽的民谣,盛传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隐晦一点的有:“爷爷落,鬼出窝,赶上小儿跑不脱。”《成安县志》为此加注说,此歌谣意为“朝廷微弱,列强肆横,清代不久将丧失主权,清祀一二传亦将斩也。”[2]比较明白的则有“辽阳今何在,二四旗不古,天下谁是谁,一省各有主。”[3]“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4]“头戴小馍盘,身穿一裹园,宣统作了帝,不过二三年。”[5]辛亥革命前夕,在西安的大街上,引车卖浆者流居然敢公开说:“大清家快完了!”因为“明朝不过二百几十年,清朝也差不多二百多年了,还不亡么?”[6]这些民谣和传言,有些固然有革命党人的因素,但能够迅速地流传开来,毕竟说明它们契合了老百姓的某种心理。反过来说,革命党人其实也受到了气数说的影响,我们在许多起义后建立的军政府的文告上,都能看到诸如“上征天意,下见人心”以及“胡运告终”之类的说法。[7]
“气数说”是一种中国固有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政治理念,蕴涵了五德循环的古老观念,而且为王朝兴衰的周期律所证实,受历史感颇强的民间戏曲小说的熏染以及《推背图》、《烧饼歌》之类的谶书的影响,民间自然不难接受这种观念,但是这种说法成为针对“本朝”的普遍流行意识,毕竟要有严重的政治腐败,普遍的社会动荡的背景衬托。气数已尽的民间说法,往往意味着民不聊生和民怨沸腾,统治者不仅失政而且失德。在南通,由于清政府苛捐杂税繁重,经办官吏又层层勒索,“工商业者怨恨极了,大骂亡国政府,且有附会《推背图》、《黄蘖诗》各种谶言,以决定清朝必然覆灭。”[8]自然,一个气数已尽的王朝,在百姓眼里继续维持下去的合法性依据也就没有多少了。比较耐人寻味的是,民众对于清朝政府的怨恨,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新政的实施。
自1903-1905年开始推行的清廷新政,是清朝最后一次,也堪称是最认真的一次西方式的改革,但是这场改革却只能依靠行政手段来推行,本来就已经陷入腐败和失效的行政网络,正好借助新政施展其最后的疯狂,“借新政之名,其实金钱主义。”[9]几乎所有的新政名目,从办学堂、办警务、到兴办地方自治,清查户口、丈量土地,都成了官吏们借机敛财的机会,各种田赋附加和捐税,直接冠以各项新政的名义。地方自治实际上成了行政触角的延伸,自太平天国以来已经逐步劣化的乡绅,名正言顺地把持了具有政府职能的各级自治机构,成为农民的直接统治者,丧失了原来处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调处者身份。先前受人尊重的乡绅,变成了农民切齿的对头,各地时常发生自治局的绅董受到农民的围攻甚至被杀的事件。进而,新政以来的民变,有相当大的部分与新政有关,农民由反对摊派和勒捐,到反对新政举措的本身,各地的征收机构、警察局甚至新学堂都成了被围攻的对象。辛亥前夕,各地农民和市民打闹自治局、征收和清丈机关的事情层出不穷,比较极端的事例象山西的干草会骚动,不仅主张“进城先抄洋学堂,以后再杀巡警兵,”而且发生了多起杀害学堂教员事件。[10]
应该说,新政的实施,虽然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别,但在大方向上与辛亥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均属于西式的向着现代化的改革。然而,对于这种改革的怨恨,却成了同一目标的更大变革的起点,这对于清廷和民众来说,都是难以想像的。庚子以后,巨大的赔款和外债压力,已使民众对于经济负担的承受力非常脆弱,而日益臃肿和失效的官僚体系更是难以承担改革重负。不幸的是,清朝政府将自身拖到了病入膏肓的关头才进行改革,社会根本无力承受越来越大的改革成本,分崩离析再所难免。而死到临头尚不自知的满清王朝,却又在最后关头自不量力地企图将久已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中央,甚至利用假责任内阁一举改变自太平天国以来满轻汉重的局面,结果是得罪了所有的人,为自己墓穴挖好了最后一锹土。新政或多或少被人们视为清朝政府气数已尽倒行逆施表现,而对新政的仇视,则成为一般民众乐意看到清朝垮台的心理基础,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场革命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尽管革命党人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但是影响所及,基本上限于知识阶层。下层民众对于革命的理解,极易误会为反清复明。同时,革命党也难以跟会党划清界限,我们知道,同盟会最乐意联系的下层社会中人就是会党。“反清复明”虽然只是会党的一个与自身的现实目标关系模糊的口号,但毕竟他们没有将它全然忘掉。在清朝呈现出明显的末世迹象的时候,他们自然乐意重提往昔的宗旨,也好从“第三社会”冲杀出来,温习称王称帝的好梦。革命党人在与会党合作的时候,一般都迁就会党的固有主张,虽然有所修正,但微乎其微,多数革命党人其实自己也往往更在乎排满,而对共和理想不甚了了,甚至有人在进行革命鼓动时,居然操着跟会党差不多的话语。鲁迅的好友,属于光复会的孙德卿,曾经很热心地拿从画像上翻拍下来的明朝皇帝的照片分送给农民,并宣传说,“清朝的政府是外面侵入的人组成的,我们应当把他们打出去。”[11]在革命前夕,凡是感觉到革命暴动迹象的人们,很容易将革命联想成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杀鞑子”,陕西起义前夕,八月十五杀鞑子之说,真的“又复充盈街巷”。[12]不仅如此,在革命中,会党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天地会、哥老会、清帮、洪门、汉留与袍哥,在各地的民军中占据了相当的份额,有的地方如西北甚至举足轻重。在独立各省,他们自称“兵马大元帅,见官大一级”,穿戏衣,蹬皂靴,两鬓结绒球,招摇过市,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革命后的中国已经是洪家的天下了。所以,老百姓以对会党的固有印象来看革命党,将革命视为反清复明的暴动,也的确顺理成章。
从另一个方面说,革命党人在革命中的行为也加强人们的这种印象。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反映辛亥革命时乡下人传说革命党人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而革命党人在各地起义时,大多数都真的张白帜、袖白臂章、甚至有的还扎白腰带,以至于有些冒充的革命党,比如一度进据扬州的流民孙天生,则“一身缠白色洋绸(由足胫至头顶)”,白了个彻头彻尾。[13]不管革命党人“尚白”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但老百姓和孙天生之辈,确实将之理解为反清复明的一种表示,革命党的行为实际上印证了老百姓的想法。
但是,反清复明的口号与逝去的明朝一样,即使对于会党也过于遥远了。帮会虽然一直属于一种令政府头痛的社会异己力量,但他们并不真的非要贯彻他们的这个宗旨不可,之所以长时间的不放弃这个口号,更多的是出于某种历史的惯性,也许革命党与会党之间更多的是相互利用,但彼此更在乎的都是排满。在革命中,几乎所有投入起义的会党中人都不再打朱家的名号,过去会党起事中常见的“朱三太子”之类的名目,此次悄然地销声匿迹。所以,对于会党自己和旁观的老百姓来说,革命对他们更多的意味着一次成功的改朝换代,一次汉人取代满人的朝代更迭。对此,革命党人在革命中的表现依然以予支持,各地党人在起义时,往往更强调“光复汉族”,对“建立民国”则较少提及,在他们在高举的白色旗帜上,往往写上一个大大的“汉”字,告示上一般都用“黄帝纪元”,所以,一般老百姓很难不将之想像为汉人取代满人的“鼎革”之举。经过辛亥革命的一位四川老人回忆说,革命中,一些地方猛然间冒出了不少头戴方巾,身穿白色圆领,宽袍大袖衣服的人,四川军政府成立,人们问一个从成都回来的人,军政府都督蒲殿俊是怎样穿戴的,那人回答说,“他头戴金冠,插野鸡翎子,身穿大红袍,腰围玉带,足穿粉底朝靴!”而听者却都信以为真。[14]显然,在相当多的老百姓心目中,通过革命上台的新统治者,理所应当就该有这样一种戏台上的汉官威仪。甚至明明白白的共和制度摆在面前了,下层民众还是将新的当成旧的来看。据当时在南京的英国领事跟他的公使汇报说,南京的下层人士“通常谈到孙文博士是新皇帝,他们不了解总统这个专门名词,认为它不过是更高头衔的一个委婉的说法。”[15]事实上,几乎所有革命后冒出来的新头衔,无论是总统还是县里的民政长,在老百姓眼里,与过去的皇帝与县太爷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于有的老百姓来说,甚至革命是什么意思都不太清楚。扬州的市民以为“革命党就是大家合(扬州方言读合如革)一条命的党。”[16]
虽然老百姓对革命党该是什么样子,脑袋里是一盆糨糊,糊里糊涂,但却往往将他们传得神乎其神。扬州的市民就传说革命党的厉害——“能把炸弹吞入腹中,遇到敌人时,将身一跃,人弹齐炸。”[17]而革命党人的兵器更是神得不得了,说是革命党人有一种“无烟炮”,“只要二指头挨到机器一搬,对面的人立刻一排一排地倒地而死。”[18]革命党的这种神奇,似乎与洋人有点关系,老百姓往往将革命党人与之联系起来,当然,这与革命党人的领袖多为来自海外的留学生不无关系。由于这层因素,以至于革命期间一有外国军队的动静,民间便传说是来帮助革命党人革命的。[19]这种神化革命党的传说,对革命党无疑是有利的,也是民众希望革命成功心愿的一种曲折的反映。
将革命视为改朝换代,将革命党视为会党甚至是戏台上的英雄,属于民众心目中旧的影象的再现,而传革命党人洋派和神奇,则又掺入了“新”的感觉,但都是希望革命党的事业有成。只要朝代能够改换成功,那么至于这个新朝是什么样子他们并不太在乎,只要能比旧的强就行。
三、新名词的浸润与老百姓的期待
虽然对于革命并不真的理解,但是相对于其他几次现代化的变革,辛亥革命对一般老百姓的震动是比较大的。戊戌维新的时候,绝大多数乡下人根本不清楚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辛亥年间皇帝的江山从此送掉,却是大部分农民都知道的事。同样,与前几次变革不同,老百姓对于辛亥革命也有某种希冀。一位留日的湖北籍学生在北京听闻武昌起义的消息,决定前去参加,“他看见沿途小贩,只顾宣传革命,不暇照顾买卖,有人问他们为何不注意自己做生意,他们一致答称:‘只要革命成功,不愁没有饭吃’。”[20]说小贩“宣传革命”多少有点夸张,但是幻想革命成功有饭吃却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希冀。还在1911年的5月,连任长沙税务司洋人司伟克都已经看出,“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21]换个政府会怎么样?并没有太多的人会去想,只知道清朝太糟糕,改换天地之后,无论如何都应该会有所改变。
打算乘乱捞一把的是不安分之徒,而大多数老百姓对政府的指望,一是维持社会安定,二是减轻一点租税和负担。辛亥革命期间,各地农村纷纷出现抗租抗税的骚动,有的还具有相当的规模,近乎于农民暴动。这些骚动显然不同于那些乘革命之机起事抢劫发财的暴乱,参加者既不是绿林好汉也非帮会人物和散兵游勇,他们都是在乡种地为生的农民,他们的要求也带有很强的合理性。对于一个前现代国度,既要发展现代工商业,又要进行现代化的体制改革,同时还要承担巨额的赔款和外债负担,几乎所有的成本都要由农民来支付,在这种情景下的农民实在是不堪重负。改朝换代对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种机会,在一些农民看来,“皇帝已经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租米不仅指地主的租,还包括官府的捐税)。”[22]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指望着新的政府尤其是直接管他们的地方政府能有所行动,改善他们的境遇,而其中性急的,就自己干了起来。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某些农民抗租骚动,居然打出了他们所不懂的新名词和新头衔,用来号召人众。湖北黄梅县张天霸组织“政党”,取名为“农林党”,并“粘贴告示,开堂散票”,宣称“农人得入党籍,将来佃人可以不交纳租课。”[23]江苏无锡常熟地区农村的“千人会”组织,在辛亥革命期间发起抗租抗税活动,成立“司令部”,推举农民孙二孙三为“都督”,树起的大旗上写着“千人大会”、“仁义农局”字样。[24]而南通丝鱼巷农民抗捐起事,首领则是“总司令”、“军政长”、“财政长”。最出奇的是他们的口号,居然是什么“自由择善”、“自由择君”。[25]其余像打出革命军、民军、独立、共和招牌的还有很多。很明显,这些起事的农民对于他们拿来的新名词和新头衔并不理解,但却没有因此而减少他们拿来的热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在辛亥前是非常少见的,那时的农民和流民的起事,往往还袭用过去的名号,诸如皇帝、王、将军和军师等等,应该说是辛亥革命的成功才点燃了农民们模仿和拿来的热情之火。
国门打开70余年以后,经过长期中西间的碰撞和西学特别是西方事物的浸润,特别是庚子义和团事件的大刺激,即使是农民,不仅知道洋枪洋炮厉害,甚至也有一部分知道了西方非物质层面的东西也同样具有威力。辛亥革命那些顶着新头衔,喊着新名词的革命党人推翻清朝政府的活生生的现实,无疑强化了这些名词和头衔在他们心目中的魅力。那些不伦不类地拿来新名词、冠以新头衔的农民们,肯定以为这些东西具有某种说不清的力量。虽然他们弄不清“革命”、“政党”、“共和”以及“自由”这些名词的真实含义,但既然强大的洋人喜欢这些东西,而学习这些东西的新派人物居然推翻了皇帝,那么这些东西肯定是有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期间人们存在着的“制度迷信”,多少已经影响到了下层社会,尽管下层社会的人们可能只是出于某种近乎巫术的心态,经过农民固有的实用理性的中介作用,才会迷信新名词会给他们带来好运。
然而,这些看起来似乎有点可笑的现象,实际上却蕴涵着悲苦的无奈。农民煞费苦心地打出“新”的旗号,其实不过是为了减轻一点租税。借新名词为自己的抗租抗税之举批上一件“合法”的外衣,用他们以为是革命党人的“道理”来为自己壮胆。这里,既有对革命和革命后建立的政府的迎合,更有迫不及待的期待。可是,刚刚尝到政权滋味的革命党人,却只将这些现象当成笑话,将农民的抗租抗税视为作乱,毫不犹豫地采取了镇压手段,他们的行动甚至比那些保留下来的旧政权还要果决。攻克南京之后,江浙革命党人最忙的事情不是北伐,而是镇压抗租抗税的农民,在革命党人的都督和军政长的命令下,刚刚与清军作完战的民军,一次又一次地开进了农村,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农民的都督和军政长们剿灭,非但不准阿Q式的农民革命,连农民合理的要求也置之不理。在革命进行过程中,一位英国外交官通过观察感觉到,“实际情况是:改变统治者对大多数人是毫无意义的,而从君主制变为共和制,对大多数人来说只不过是改变统治者而已。关于皇帝和议会,除了作为名称之外,老百姓是一无所知的。他们所熟悉的政府机构中的那部分主要是衙门差役,而已经发生的事情并未包含对该部门进行根本改革达到希望”。[26]一位美国学者的看法似乎更苛刻一点,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他认为,同盟会在革命后,是“按照传统的方式,作为军队和征税者进入农村的,”这样一来,“那些新贵们及其政策,就和他们的军事和财政基地一样,很难与既得利益的旧秩序区别开来”。[27]在农民眼里,新政权在征税催捐方面似乎与清政府并没有多少区别,县政府的衙门,除了插了一面白旗而外,一切照旧。满清还没最后推翻,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谈判尚在进行,而各地的民政与军政长官则均忙于催租、征税和“拿办乱民”,不旋踵则布袍子就换成了皮袍子,可是南京临时政府却连一分钱上缴经费也拿不到。时人讽刺到:“新朝气象百弊无,惟有租赋难蠲除。大府火急筹军需,哓哓抗诉胡为乎?多言尔且罹罪辜,即不笞杖亦孪拘。小民畏法长叹呼,痛深不觉涕泪濡。”[28]
四、留住辫子
当然,我们说革命后的新政府与清朝政府没有区别也是有点冤枉。新政府至少有一件事是与旧政府根本相异的,那就是为男人剪辫。当年满清入关,剃发留辫是作为顺从统治的标志而强行推行的。为了头上的头发和脑后的辫子,汉族老百姓很是死了不少。然而,两百多年过去了,汉族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习惯了脑后的辫子,虽然晚清以来某些知识人在西风熏染之下,受不了洋人讥辫子为pig tail (猪尾巴)而愤然剪辫,但绝大多数老百姓还是将辫子看得相当重,决不肯轻易地让它损伤分毫。
然而,革命的到来使辫子的命运再一次发生了重大转折。在人称革命政府最忙的三件事,剪辫、放足和打菩萨中,他们最最热心、执行最力的就是剪去男人的辫子。凡独立各省,尤其是那些靠革命党人拼杀而独立的地方,几乎一进城就会有剪辫的文告出台,武装的剪辫队上街强行为人剪辫。有的地方剪辫队甚至有好几拨,有来自民军的,也有来自警察的和学生的。其中学生和民军的积极性最高,而警察则往往是因为有政府的命令而例行公事。当然,强行剪辫的“武行”出台之前往往有属于“文行”的宣传,在街头为老百姓宣讲剪辫的好处和必要性,但是由于往往文的没有演完武的就开锣,所以老百姓只要一听到有人宣传剪辫,马上望风而逃,结果最后只剩下“武行”了——就是突然袭击,抓住按头便剪,或者守在城门口,所有进出人等,有辫子的就是一剪。有的地方,革命党人对于辫子不仅强按头采取断然措施,而且通过法律手段硬性推行。比如浙江宁波军政府就贴出告示,宣称凡不服从剪辫令的,“剥夺其公权及诉讼权”。[29]为了抗拒剪辫而吃官司的也不乏其人。[30]
如果说,对于革命党推翻清朝的行动老百姓还能算是拥护的话,那么对于掌握权力的革命党人的强行剪辫之举,他们可是非常的不情愿。被抓住剪辫的人,哭闹喊叫甚至与剪辫队发生扭打的都有,农民则干脆不进城了,集市为之一空。某些聪明人为了逃避剪辫,将辫子盘起,再戴上头巾,以遮人耳目,还有将辫子散开,扎成抓髻装道士的,道士服装一时也值钱起来。某些地方甚至开始流行一种尖顶帽,“帽的款式,尖顶耸起,帽的容量,由于高高耸起,足可以容辫子有余,一时皆大欢喜,中少年人纷纷购置,贫穷人情愿衣不蔽体,食不裹腹,也须购买一顶,以为藏辫之需。”[31]
这种大规模的剪辫,有时居然会惹到洋人头上。当一些为西方人做事的买办和仆役难逃劫运丢掉自己的辫子的时候,他们的主人往往会出面交涉,英国驻长沙领事就曾经为太古洋行的一位买办的遭遇提出过“强烈的抗议”。[32]谙熟西方政治的外国人,从共和政体的规范出发,质疑革命党人的这种有碍自由和人权之举,往往令革命党人有些难堪,但也只做到了涉及到洋人时才有所收殓。[33]
有时,强行剪辫也会酿成风波,1911年11月,苏州新军的某排长等率领士兵在城里强剪路人辫子,结果“被众不服,围住痛殴”,将该排长打伤。[34]而安徽事情闹得就更大,独立后,拥护前清巡抚朱家宝的旧势力,恰是煽动一些对剪辫不满的安庆市民,围攻革命党的都督王天培,以反对剪辫为名,压迫王走人,“遇有西装无辫之人,遂任意殴毁。旋经绅商学界仍公举朱家宝为临时都督,并沿街劝导,其事始寝”。[35]
当然,革命党人如此急切地要人们去掉脑后的辫子也是有他们的道理的。首先,他们是将辫子看成满清留在汉族人身上耻辱标记,所以必须去之而后快。我们知道,即使是同盟会中人,大多也将“驱逐鞑虏”看得远重于“建立民国”,经过同盟会长期的宣传,像与辫子有关的“嘉定三屠”之类的满清血案,已经深深地印在所有投身革命的新军和学生脑海中,一旦革命成功,他们很自然地要尽快地刷洗这种长达260年的耻辱,其次,革命党人也将辫子视为奴隶的标志,他们要给人们以自由。以先知先觉者自居的党人,既然革命当然要用他们的手来解放老百姓,而不愿意剪辫则视为“奴隶根性”顽固不化,所以非得以外力打破不可。其实最刺激革命党人,使他们不仅要去掉自己的辫子,而且还要去掉别人的辫子的动机,原为西方人的嘲笑。晚清时节,西方人一直将中国人视为不开化的“土人”和“野蛮人”,而其标志就是缠足和辫子。他们讥中国男人脑后的辫子为pig tail ,而且上海租界的外国巡捕抓中国人以及八国联军搜捕义和团,往往揪住辫子,一抓一串。我们在许多革命者的记叙中,都能发现这种讥讽和场景的刺激而留下的强烈印象。实际上,正是要尽快地消除这种奇耻大辱的印象,他们才会不惜放下手中的要务,先来对付辫子。我们看到,潮州的剪辫文告中就有这样的文字:“蓄发垂辫,满清陋制,豚尾悬肩,供人戏弄;民族光复,理应毁弃,若不自动,军民代剃。”[36]显然,从这个角度讲,剪辫实际上是在向西俗看齐,并非恢复清以前的传统,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做“假洋鬼子”,所以,老百姓接受的难度就更大一点。
在华的英国外交官看到中国老百姓为了躲避剪辫而戴上头巾和帽子,而革命政府的警察居然还要检查时,不无揶揄地写到:“警察对自由的热忱,常常促使他们去攫取那些没有恶意的过路人的帽子,以便查明在这个自由的领域内,这些过路人是否在内心仍然是满清的奴隶。”[37]也许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的作法实际多少堕入了传统征服者强迫归顺的老套,而这正是他们所憎恨的满清统治者当年做过的事情。人们内心是否归顺,实际上是不容易测出的,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留着辫子,并不就意味心向满清。我们知道,剪掉辫子在清朝意味着反叛(晚清虽然有松动,但在老百姓眼里,依然是了不得的事情,具有生命的危险),而在革命党则意味着投向革命,双方未卜胜负的时候,让信息闭塞的老百姓做出甘冒在他们看来有性命之忧的抉择,委实是强人所难。我在前面说过,其实老百姓对清朝并无留恋,于革命党的革命也基本上持欢迎态度,但同情革命是一回事,而投身革命又是一回事,在老百姓心目中,剪掉辫子就意味着投身反叛,自己就成了叛党,而这恰是株连九族的事情。所以让农民将辫子如阿Q式地盘起容易,但让他们将辫子剪掉却难,剪掉了辫子,一时半会儿长不起来,如果皇帝再坐龙廷怎么办呢?虽然辛亥年底,迫于革命的压力,清廷颁布了允许自由剪辫的诏令,但是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知道。
更往深里说,对于那些风气未开的农民和市民而言,辫子还有另一重的意义。读过孔飞力《叫魂》的读者想必会知道,人们对乾隆年间剪辫风波的恐慌,主要是巫术性质的,人们害怕辫子被剪,主要是担心剪下来的辫子会被用来行巫,
从而危害被剪人的生命,这也正是为什么辛亥期间被强行剪了辫子的农民非要苦苦哀求讨还被剪掉的辫子的原因。基于这个道理,即使被剪的老百姓大部分要回了自己的辫子,但被剪毕竟蕴涵了丢失辫子很大的可能,所以,恐慌很快就会弥漫起来。显然,这种恐慌对革命政权并不利。如果说,照样催粮纳赋不过是袭承前朝,农民虽然失望,但还说得过去,而剪辫政策,在老百姓眼里,不啻是一种添加出来的暴政。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成为革命政府失掉民心的开始。
五、结语
从表面上看,下层民众对于革命的态度,与这场革命能否成功并无多大的关系,起义和战争,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直接的军事力量的对比,以及双方战略战术的选择和武器与其他与军事有关的条件,但是,即使是最为唯武器论的军事家,恐怕也难以否认士气这一类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中,恰恰是这种类似精神性的因素帮了革命的忙。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未必强于清军,其指挥也不见得高明,清朝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自身的统治信心已经瓦解,这种瓦解近乎某种普遍的崩溃,几颗炸弹就能让满朝文武作鸟兽散,有的地方,革命党人还没有露面,仅仅十几个根本没有来头的乌合之众,就能让拥有兵马的清朝地方官交印投降。这种统治信心的瓦解,无疑与“民心已失”的普遍认同有着关联。当社会上布满了敌意,反叛行为得到普遍的同情,社会秩序陷入紊乱的时候,不仅绅士阶层对王朝的信心会受到影响,连带着各级官吏也会心存另谋出路的贰心,老百姓的态度实际上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刺激着官吏和乡绅,日积月累地销蚀和瓦解着上流社会对王朝的信心和忠诚。几个、几百个甚至几万个老百姓对政府不满、希望政府垮台当然并没有多少效用,但是如果这种情绪成为一种普遍而持久的心态,就可能从根本上瓦解统治,这个时候,只要遇到外力或者内乱的刺激,而且这种刺激又具有一定强度的话,就可能导致全面崩溃。
孙中山曾经说过,庚子以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庚子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前后相较,差若天渊”。[38]虽然孙中山将这种“差若天渊”的变化半归之于其党人郑士良惠州起义的“唤醒”,未免有革命党人的自负,但他对民心变化的感觉却是相当准确的。
只是,民心的变化并不是因为革命党人那一次次小打小闹的起义,跟他们声势不小的宣传也没有太多的关系。庚子义和团运动无疑是与下层民众关联最为密切的历史事件,清廷的表现有目共睹,令下层百姓寒心也是理所当然。接下来奉旨(洋人之旨)变法的新政,又火上浇油,使这个王朝丧失了在老百姓眼里的最后一点合法性依据,辛亥革命的成功,有着十分复杂原因,但与民众的普遍反感和期望“变天”不无关系。
然而,成功了的革命党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革命后袁世凯的北洋系、各省乡绅和前立宪派混合的地方实力派以及革命党人的力量对比中,革命党人虽然看起来人多势众,其实革命中扩张起来的势力中,农民和流民远没有与革命党人达成起码的亲和,很多地方的民军,其实更象是各行其是的乌合之众。地方实力派出于对清廷收回散在地方的权力的不满,顺从了革命,但是他们对革命党人的敌意却并未消失,情愿拥护似乎更讲究规矩的袁世凯。革命党虽然与地方实力派在革命过程中结成了事实上的联盟,但并不在意维护,同时却在与地方实力派“咸与维新”的种种努力中,抛弃了下层民众,甚至为了维护乡绅的利益,不惜镇压农民,而大力推行的强迫剪辫的举措,更是无端制造下层社会的恐慌,失掉了本来可以获得的民心,某种程度上将民众推到了地方实力派的那里,革命后真正革命的革命党人屡屡在地方政府失掉权力,老百姓宁愿拥护前立宪派的官僚和绅士上台,江苏甚至传出了歌颂某些前清开明官僚的民歌(苏州有儿歌云:“苏城光复苏人福,全靠程都督。”[39]),实际上,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还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在南京英国外交官发现,强迫征税和强迫剪辫已经在南京城内引起普遍的厌恶情绪,“广大群众开始认识到,豁免一切捐税以及关于新太平盛世将带来繁荣昌盛的其他一些普遍幻想的前景,事实上是没有根据的。在许多场合下,他们开始对他们所给予革命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感到后悔”。[40]当然,这种后悔还不至于导致针对革命政权的骚乱和反抗,但足以销蚀这个政权的基础,遇有外力压迫,就难以支持。
革命后,由于革命自身的声势,革命党人依然在政坛上十分活跃,但实际上已经成了空架子,地方基层政权不是偷天换日,就是改头换面。中国不是西方国家,第一次国会大选的胜利其实并能不说明革命党的实力(农民根本就没有投票),拥护它的多是浮在面上的“洋”学生,而这些人远没有他们作为绅商的父兄有根底,革命政权虽然时日不多,但已经在老百姓中留下了毛糙浮躁的印象(农民对此特别反感),他们对这样不稳的统治自然不无担心。虽然革命后革命党人拥有的军队数量大为减少,但在革命党、袁世凯和地方实力派的三方实力对比中,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依然有相当规模,然而在还谈不上精锐的袁军打击下,居然雪崩似的瓦解,确实是件令人费解的事情。革命党的组织涣散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民众对他们丧失信任和失去亲和力确也是个不小因素,不是说老百姓的倾向直接促使了革命党人的惨败,而是地方实力派在民心求稳的情况下得分过多,无形中强化了反对势力。甚至民心的归附与否,也影响到了革命党人军队的士气和人心,从而大大削弱了民军的战斗力。外力的压迫激活了民众的反感,而这种反感则放大了外力的效应。
如果说,在一般的历史条件下,下层民众的意向是通过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释放能量的话,那么,当袁世凯挥起屠刀砍向革命党的时候,在突然到来的军事压力面前,民众的反感和冷漠终于转化成了某种情景,促进了革命党雪崩式的瓦解。在革命党和袁世凯的较量中,地方实力派毫不犹豫地成了帮凶,而老百姓则变成了麻木的旁观者,甚至宁愿跟在实力派的后面看热闹,对革命党人的遭遇,他们甚至连一点起码的同情和留恋都没有,在某些党人看来,民众对他们似乎比对满清还要冷酷无情。二次革命后,革命党人颓废的多、出家的多、自杀的多,或多或少跟吾国吾民这种“麻木”有些关系。
“得民心者得天下”倒不见得是个始终能被历史所印证的命题,但失民心者却是有可能失去已得的天下,尤其是在刚得天下,而又有外力的压迫的时候。在北洋和地方势力的双重压迫下,革命党人要想保全革命果实固然很不容易,但象后来那样被迅速扫地出门却也出人意料。我们当然不能期望当年的同盟会中人,象后来的共产党人那样进行民众动员,但在当时的情景下,做到将老百姓的感受当回事似乎也并不难。
--------------------------------------------------------------------------------
[1]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18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
[2] 《成安县志》,民二十年刊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451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3] 《中国民间文学史》下册,第2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4] 同上,第276页,亦见景梅九《罪案》。
[5] 董继广等:《柘城农民起义纪略》,《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386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6] 景梅九:《罪案》,《近代史资料专刊: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75页。1981年12月。
[7]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第46、2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9] 胡恭先:《西昌辛亥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236页。
[10] 《上党干草会运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194—195页。
[11]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253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
[12] 郭孝成:《陕西光复记》,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六)第38页。
[15]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50页,中华书局,1984。
[17] 同上
[18] 陈日刚:《大足同志军》,《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267页。
[19] 参见日本驻汉口领事馆情报第58号,《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辛亥革命资料”第600页。
[20] 贺觉非:《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人物传》(上),第1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21]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23] 1912年11月7日《时报》。
[26]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231页。
[27] 【美】爱德华·弗里曼:《革命运动还是流血事件?》,《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第191页。
[28] 汪曾阳:《辛亥纪事诗》,《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216页。
[29] 林端辅:《宁波光复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180页。
[30] 参见江天蔚:《辛亥革命后松阳的一次剪辫斗争》,《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203—204页。
[31] 陈逸芗:《故乡兴化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八)第112页。
[32]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390页。
[33]英国驻腾越领事的仆人被抓住,但是在说明他的身份后,没有丢辫子就得到了释放。参见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320页。
[34] 郭孝成:《江苏光复纪事》,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七)第9页。
[35] 郭孝成:《安徽光复记》,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七)第175页。
[36] 翁辉东:《潮汕光复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七),第259页。
[37]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320—321页。
[38]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