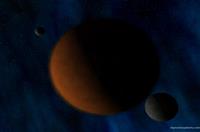
我们学校的文艺刊物《摇篮》,从上世纪的1981年至今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一个《摇篮》一摇就摇了三十年,这真是个值得好好庆贺的日子。新任《摇篮》文学社社长田伊琳,昨天给我写了一封让我激动了一夜晚的信,她在信上“歌颂”我说:“您的真诚,您的洒脱,您敏锐的洞察力和您直指人心的言语……使您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心目中的‘麻辣老师’。”“歌颂”完了以后接着就给我提要求:“给《摇篮》写一千字左右的寄语”。
听别人唱颂歌当然很高兴,听说要写寄语可就有点发怵。30岁,要是个大姑娘早该结婚了,要是小伙子早已谈过好几轮女朋友——总之,它要是个“人”我就知道该怎样恭维它,什么“前程似锦”,什么“早生贵子”,恭维辞前人早就准备好了,可这个年满30岁的《摇篮》偏偏是个刊物,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对它开口。
但听了赞歌,就得写寄语。
任何人在婴儿时期都离不开摇篮,任何立志创作的青年同样也有自己的“文学摇篮”。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可能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运,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刊物,可能是影响自己一生的“恩人”。
于是,我想到我自己的“文学摇篮”。
那是在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中学一次“批林批孔”的墙报上,贴出了我自己半是抄袭半是拼凑的两首“诗歌”,一位同学不知道此诗基本是抄来的,称赞这两首诗“写”得如何如何好。我一听到恭维就头脑发昏,当天就把这两首诗寄给了一家报纸,没有想到那家报纸的编辑比我头脑还昏,竟然把这两首诗给发表了,我在自己那个乡村中学一夜成名,人们开始叫我“诗人”,时间一长我自己也俨然像个“诗人”,学校很多墙报和宣传稿都由我执笔,上大学前我还发表了几篇散文,一个短篇小说,一个独幕剧。我尝到了写诗作文的“好处”,这才爱上了写诗作文,其实原来我最喜欢的是数学,成绩最好的也是数学,但那时我觉得写诗最有前途,1977年高考时文理科考一样的试卷,我数学考得还好一些,但我第一志愿就填了华师中文系,因为我的班主任是华中师大校友。来华师后发现写诗并没有那么“光荣”,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写诗的才能,虽然在校报和外面的小报上发过一些诗歌,但对写诗作文的兴致骤减。上大学两个月以后,我要求转到数学系,可那时转系比现在移民还难,转系不成,又向我当时的班主任、语言学家刘兴策教授要求“退学”,幸好刘老师不像我那像发昏,他拒绝了我的退学要求,并鼓励我好好学习,还表扬我“学得不错”。这样我才坚持下来学习中文,才坚持学习英语,最后坚持学习搞文学研究和教学。
不知道这是人生的喜剧还是人生的悲剧,我首次发表的那两首歪诗,影响了我的学习兴趣,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首次发表我“诗歌”的那张报纸,事实上就成了我文学创作的“摇篮”。可见,小时候的“摇篮”比成人的“床”重要得多。
今天的教育环境与三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今天青年朋友的人生也不会像我们当年那样盲目,他们现在学习文学创作,学习文学研究,是一种个人兴趣,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将来他们的创作和学术成就肯定比我们更高,将来他们的人生肯定比我们更加美好。
我希望,也相信,从我们学校的《摇篮》中,将走出了更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学者,走出了更多杰出的大学教授、中学老师……
2011年10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