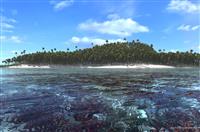摘 要: 本文继续作者以往的文化研究课题,把女权/女性主义批评在西方的兴起以及最近的发展走向纳入文化研究的语境之下进行重新考察。作者认为,女权主义早已从早期仅仅对妇女社会地位和权益的追求发展到对女性与男性之差异的认同以及对女性自身独特身份的建构。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的迁徙和文化身份的模糊更加为性别研究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条件,当代性别研究的前沿课题就在于对女性同性恋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怪异现象的研究。这两个理论课题的研究目前已经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并有可能结合国内的现状而开展相应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文化研究;性别研究;女权/女性主义;怪异研究;女性同性恋研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 西方文化界和文论界就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浪潮,这股浪潮很快便将各种与后现代、后殖民有关的边缘话语研究纳入其不断扩大的研究领地,对传统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在这股文化研究大潮面前,一些原先从事精英文学研究的学者感到手足无措,他们惊呼,面对文学以外的各种文化理论思潮的冲击,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边界向何处扩展?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 而另一些观念较为开放并致力于扩大研究领域开阔视野的学者则对之持宽容的态度,并主张将基于传统观念之上的狭窄的文学研究的课题置于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之下,尤其是要注重那些历来不为精英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边缘”课题,例如种族或族裔研究(ethnic study)、性别研究(gender study)、区域研究(area study)、传媒研究(media study)等。毫无疑问,对性别和身份问题的考察是文化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课题,因而将性别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同性恋(gay and lesbian)现象和怪异现象研究(queer study)纳入广义的文化研究语境之下来考察是完全可行的。尽管国内学者对女权/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和女性文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当前西方性别研究的前沿理论课题却知之甚少,更谈不上将其纳入到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来考察了。因此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及其发展方向
文化研究崛起于上世纪40年代的英国学术界以来,至今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它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声势浩大,但正如有些学者所始终认为的那样,“它并非一门学科,而且它本身并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方法论,也没有一个界线清晰的研究领地。文化研究自然是对文化的研究,或者说更为具体地说是对当代文化的研究。”[1](p1) 显然,这既是文化研究的不成熟的地方,同时也是它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长处。它的不成熟之处在于其研究方法的不确定,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视角,因而很容易把一些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但确有着自己一孔之见的“业余学者”和文化人引入自己的领地。但也许正是这一“不成熟”之处才使得文化研究在近二十年内有了迅速的发展。[1]毫无疑问,本文所要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已经与其本来的宽泛含义上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有了根本的差别,在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中,“‘文化’并不是那种被认为具有着超越时空界线的永恒价值的‘高雅文化’的缩略词”,[1](p2)而是那些在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占统治地位时被当作“不登大雅之堂”(unpresentable)的通俗文化或亚文学文类或甚至大众传播媒介。它并不是写在书页里的经过历史积淀下来的精英文学文化,而是现在仍在进行着的、并有着相当活力的当代流行文化。当然,文化研究也是从早先的文学研究发展而来的,它在早期的形态有着这样两个特征:其一是强调“主体性”(subjectivity),也即研究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之模式;其二则是一种“介入性的分析形式”(engaged form of analysis),其特征是致力于对当下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细致的分析并提供理论的阐释。这两个特征毫无疑问都为文化研究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尽管文化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标榜自己的反理论、反体制等倾向,但它的理论来源的多元化却是十分明显的。关于文化研究所受到的理论启迪和所拥有的理论资源,一般认为主要有这几个方面:早期的英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F.R.利维斯的精英主义文学观和注重文学经典研究的倾向毫无疑问成了后来的文化研究者所要超越和批判的对象;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A. Gramsci)的霸权概念无疑也对文化研究的鲜明的批判性特征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更是使得文化研究得以直接地针对当代社会现实问题提出批判性的分析和阐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使文化研究者得以从语言的层面切入探讨文学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习俗;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史学理论使论者们得以剖析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权力的主导作用以及话语的中介作用;拉康的注重语言结构的新精神分析学也为文化研究关注性别问题提供了理论资源;巴赫金对民间文学的探讨也给了文化研究者新的理论资源和启示;文学人类学对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书写使得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建构成为可能;而文化人类学理论则使研究者得以探讨艺术的起源等问题。可以说,在经过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冲击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了,探讨的问题也从地方社区的生活到整个大众文化艺术市场的运作,从解构主义的先锋性语言文化批评到当代大众传播媒介甚至消费文化的研究,从争取妇女权益和社会地位的女权主义发展到关注女性身体和性别特征的性别研究和怪异研究,从特定的民族身份研究发展到种族问题和少数族裔文化及其身份的研究,等等。原先戒备森严的等级制度被打破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人为界线被消除了,殖民主义宗主国和后殖民地的文学和理论批评都被纳入同一(文化)语境之下来探讨分析。这样,“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文化研究最有兴趣探讨的莫过于那些最没有权力的社群实际上是如何发展其阅读和使用文化产品的,不管是出于娱乐、抵制还是明确表明自己的认同”,[1](p7)而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论争而来的全球化大趋势更是使得“亚文化和工人阶级在早先的文化研究中所担当的角色逐步为西方世界以外的社群或其内部(或流散的)移民社群所取代并转变了”。[1](p17)这一点正符合后现代主义大潮衰落之后西方理论界的“非边缘化” 和“消解中心”之趋势,从而使得文化研究也能在一些亚洲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得到回应。[2]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文化研究也有了快速发展的土壤。它迅速地占据了当代学术的主导性地位,越来越具有当下的现实性和包容性,并且和人们的文化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当代文化研究的特征在于,它不断地改变研究的兴趣,使之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文化情势,它不屈从于权威的意志,不崇尚等级制度,甚至对权力构成了有力的解构和削弱作用, 它可以为不同层次的文化欣赏者、消费者和研究者提供知识和活动空间,使上述各社群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活动空间。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研究已经逐步发展为一种打破了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跨越东西方文化传统的跨学科的学术研究领域和批评话语。在文化研究这一广阔的语境之下我们完全可以将长期被压抑在边缘处的性别问题和性别政治提到文化研究的议程上来。而全球化的进程则使得对性别问题和性别政治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西方的发达国家,并逐渐成为一些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从事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女权和女性研究到性别研究
早在后现代主义大潮在西方学术界衰落之后刚刚形成的多元文化格局之下,女权主义作为一种边缘话语力量在西方文化理论界扮演的角色就开始显得愈来愈不可替代。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传统的注重女性权益和社会地位的女权主义理论思潮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如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怪异研究(queer study)、妇女研究(women study)、同性恋研究(lesbian studies) 等,颇为引人注目。在汉语中,女权主义又可以译成“女性主义”,但在使用中却旨在说明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表明的侧重点的不同:早期的女权主义之所以称为“女权”主义是因为它所争取的主要是妇女的社会权益和地位,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所要达到的是男人已经拥有的东西;而当今的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时常混用则显示出一部分已经享有与男性同等权利的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所要追求的恰恰是女性在生理上与男性存在的天然的差别。她们并不满足于与男性的认同,而恰恰要追求不同于男性的“女性特征”和女性身份。对于这一本质上的差别表面上看来在这个英文词中并无体现,但人们却能从“feminism”这个术语逐渐为上述诸概念所依次取代而看出其中的转向。这自然也体现出女权/女性主义研究内部的一种转向。但尽管如此,女权/女性主义的边缘性仍是存在的,而且是双重的:在一个“男性中心”社会中的边缘地位和在学术话语圈内所发出的微弱声音,这两点倒使得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性文学始终具有强烈的论战性和挑战性,并一直在进行着向中心运动的尝试。早在80年代初,女权主义就曾经和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共同形成过某种“三足鼎立”之态势,后来,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后结构主义在美国理论界的失势和新历史主义的崛起,女权主义在经过一度的分化之后又和马克思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共同形成过一种新的“三足鼎立”之态势。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女权主义的多向度发展,它又被纳入一种新的“后现代”文化研究语境之下得到观照,在这一大背景之下,由传统的女权主义理论研究演变而来的妇女研究、女性批评、性别政治、女性同性恋研究、怪异研究等均成了文化研究中与女性相关的课题。总之,时至今日,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女权/女性主义和作为一种批评理论的女权/女性主义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显示出其不断拓展和更新的包容性特征。
女权主义曾经有过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始自19世纪末延至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争取妇女的权利和参政意识,所强调的重点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改革,这在某种程度上与6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女权主义运动有着明显的差别。而且这时的女权主义批评家所关心的问题主要局限于其自身所面临的诸如生存和社会地位等问题,并未介入理论界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因而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则使得女权主义运动本身及其论争的中心从欧洲逐渐转向了北美,其特征也逐渐带有了当代批评理论的意识形态性、代码性、文化性、学科性和话语性特征,并被置于广义的后现代主义的保护伞之下。这一时期所关注的有五个重要的论争焦点:生物学上的差异,经历上的差异,话语上的差异,无意识的差异以及社会经济条件上的差异。论者们讨论的主题包括父系权力制度的无所不在,现存的政治机构对于妇女的不适应性和排斥性以及作为妇女解放之中心课题的女性的差异等。应该承认,这一时期的批评家和女性学者所关注的是女性的独特性和与男性的差异。经过70、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再度勃兴,后现代主义辩论的白热化和后结构主义的解构策略的冲击,女权/女性主义本身已变得愈来愈“包容”,因此它的第三次浪潮便显得愈来愈倾向于与其他理论的共融和共存,形成了多元走向的新格局: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黑人和亚裔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女性文学,有色人种女性文学,第三世界/第三次浪潮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性别政治,怪异理论等等。这种多元性和包容性一方面表明了女权主义运动的驳杂,另一方面则预示了女权主义运动的日趋成形和内在活力。
在文化研究的广阔语境下,以女性为主要对象的性别研究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女性性别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反女性的女性主义,女性写作和女性批评,法国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理论,女性诗学的建构,女性身份研究,女性同性恋研究,怪异研究。从上述这些倾向或研究课题来看,一种从争取社会权益向性别差异和性别政治的转向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也就是说,所谓女性的性别政治已经从其社会性逐步转向性别独特性。这一点恰恰是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性别研究的主要特征。本文将在下面两节中分别予以评介和讨论。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女性同性恋批评和研究
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考察性别和身份问题,我们自然不可回避这两个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女性同性恋和怪异现象。在这一节里,我们主要讨论女性同性恋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女性同性恋批评和研究。
众所周知,50、60年代在一些欧美国家曾经兴起过性开放的浪潮,大批青年男女试图尝试着婚前无拘无束的性生活,致使传统的婚姻和家庭观念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之后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尤其是对女性怀孕后人工流产的限制,这种性开放的浪潮逐渐有所降温。带来的后果则是三种倾向:其一是传统的婚姻和家庭观念的逐渐淡薄,青年人虽然对结婚和生育持审慎的态度,但对婚前的同居生活则更加习以为常,这一点和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其二则是呼唤一种新的和谐的家庭和婚姻观,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家庭和婚姻观念的继承;其三则是在经历了性开放浪潮的冲击之后,一些知识女性也模仿早已在男性中流行的同性恋倾向,彼此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久而久之便发展为对异型恋的厌恶和拒斥和对同性的依恋。人们对这些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社会地位的知识女性的所作所为感到极为不解,甚至认为她们十分“怪异”。起源于70年代、兴盛于80、90年代的所谓“女性同性恋研究”(lesbian studies)以及兴起于90年代的“怪异研究”(queer studies)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目前对这两种现象的研究已经被纳入广义的文化研究的性别研究范畴下,并逐步成为其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学科领域。
早期的女性同性恋现象及其批评(lesbian criticism)的出现与先前已经风行的男性同性恋(gay)现象及其批评(gay criticism)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同时也与早先的女权主义运动有着某种内在的继承和反拨关系。作为女权主义批评的一个分支,“女性同性恋批评尤其起源于有着女性同性恋倾向的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和运动,因为它本身就是由妇女解放和男性同性恋解放运动发展而来的”。[2](p329)一些知识女性,主要是白人知识女性,既不满于妇女本身的异性恋,也不满于男性同性恋者的那种肆无忌惮的性行为,因而她们自发成立起自己的新组织,并称其为“激进女性同性恋者”(radicalesbians)或把自己的事业当作一种类似“女性同性恋解放”(lesbian liberation)的运动。她们认为女性同性恋主义使妇女摆脱了父权制的束缚和压迫,可以成为所有妇女效仿的榜样,因此女性同性恋主义是解决女权主义的没完没了的抱怨之最佳方式。[2](p329)还有一些更为极端的女性则公然号召妇女与男性“分居”,同时也与异性恋妇女“分离”,她们认为这不仅仅是性行为上的分离,而且更是政见上与前者的分道扬镳。毫无疑问,早期的这些极端行为为女性同性恋批评及其研究在80年代的逐步成型、90年代的蔚为大观奠定了基础,应该说当代女性同性恋文学理论正是从这种女性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语境中发展而来的。
女性同性恋批评的发展同时也有着一定的机构性支持。例如早期的“女性分离主义”学派(feminist-separatist school)从一开始就注重建构自己的文化,她们通过创办自己的刊物和出版社、出版自己同仁的作品来扩大影响,后来她们甚至在有着数万名会员和广泛影响的现代语言学会(MLA)的年会上组织专题研讨会,以吸引更多的知识女性加入其中。当然,女性同性恋运动一出现就遭到了相当的反对,主要是来自女性内部的反对,一些传统的女性甚至认为这些“无性的”女人本身“有毛病”或“反常”,如同“魔鬼一般”,实际上是生理上可悲的“牺牲品”。另一些人则对之持理解的态度。比较持中的观点以利莲·费德曼(Lillian Faderman)为代表,她在《超越男人的爱》(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1979)一书中号召妇女建立起一种类似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存在于美、英、法作家的作品中的“浪漫的友谊”,但她并没有对有性的和无性的亲密关系作出明确的区分,这实际上也是当代女性同性恋没有朝着畸形方向发展的一个健康的先声。
尽管迄今女性同性恋文学批评家和学者大多为白人知识女性,而且阅读和研究的对象大多为经典的女性作品,但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女性也开始了自己的批评和研究,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早期著述为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的论文《走向一种黑人女权主义批评》(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1977),其中花了不少篇幅从女性同性恋的理论视角来解读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苏拉》。在这之后研究非裔美国同性恋女性主义的著述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显然与美国这个多元文化社会的混杂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有关。而相比之下,在欧洲的批评界和学术界女性同性恋批评的声音就要小得多。如果说“古典的”女性同性恋理论还有着不少令人可以分享的概念的话,那么经过解构主义训练、崛起于80年代的新一代批评家则把这些东西抛在了脑后,再加之有色人种妇女的参与以及男性同性恋理论的吸引,女性同性恋理论愈益显得驳杂,它与其说与异性妇女围绕性别的轴心有着关联倒不如说更与男性同性恋理论相关联。这些深受解构主义影响的批评家将一切“统一的”、“本真的”、“本质的”东西统统予以解构,从而使得“lesbian”这一术语成了父权话语体系内的分裂的空间或主体的表征。这些观点大多体现在卡拉·杰(Karla Jay)和琼娜·格拉斯哥(Joanne Glasgow)合编的论文集《女性同性恋文本和语境:激进的修正》(Lesbian Texts and Contexts: Radical Revisions, 1990)中的一些具有原创性的论文中。显然,进入90年代以来直到本世纪初叶,女性同性恋理论依然方兴未艾,批评家们围绕自我的本质、社群问题、性别和性等问题而展开异常活跃的讨论,此外,学界也越来越尊重传统的女性同性恋女性主义(lesbian feminism)的不少观念。这一切均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稳步拓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在文化研究的大视野中,性别研究和性别政治成了其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甚至包括男性同性恋研究在内的这方面的研究机构也在一些大学建立了起来。但相比之下,对女性同性恋的研究更加引人瞩目。这可能与90年代崛起的“怪异理论”或“怪异研究”不无关系。
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怪异研究及理论思考
尽管人们难以接受女性同性恋现象,甚至对研究这种现象的女性学者也抱有一些偏见,但对其反抗男权话语的激进批判精神还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于怪异及其怪异理论,人们则有着某种天然的敌意,这主要是出于对怪异现象本身的误解所导致。实际上,怪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男性同性恋和女性同性恋发展演变而来的,或者说是这二者平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必然产物。由于男性同性恋者的不懈努力,男性同性恋运动在相当一部分国家已经成为合法化,因而对男性同性恋的研究也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对于女性同性恋行为,不少人,尤其是女性内部的一些坚持传统者,则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由于被认为“怪异者”的人都是女性,而且大多是由女性同性恋发展而来,与前两种同性恋既有着一定的联系又不无差别,因此研究者往往对之的研究也自然会将其与前二者相关联。
“怪异”(queer)根据其英文发音又可译为“酷儿”或“奎尔”,意为“不同于正常人”(non-normative)的人,而用于性别特征的描述而言则显然有别于“单一性别者”。也即如果作为一个男人的话,他也许身上更带有女性特征,而作为一个女人,她又有别于一般的女性,他/她也许不满足甚至讨厌异性恋,更倾向于同性之间的恋情,等等。因而在不少人看来,这样的人与正常的有着鲜明性别特征的人不可同日而语,属于“怪异的”一族。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怪异”,人们至今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定义。1991年,当女权主义理论家特里莎·德·劳瑞提斯(Teresa de Lauretis)最初使用这个术语时,她试图赋予其一种反对男性的偏见的责任,在她看来,这种偏见就隐藏在被归划了的并且似乎具有性别感的术语“女性同性恋和男性同性恋”(lesbian and gay)之中,而将这二者混为一谈实际上也就混淆了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差异。[4](pvi-vii)这一点一般被认为是“怪异”的一个显著特征。[3](p116)正如怪异研究者安娜玛丽·雅戈斯( Annamarie Jagose)所不无遗憾地总结的,“显然,迄今仍没有一般可为人们接受的关于怪异的定义,而且,确实对这一术语的许多理解都是彼此矛盾的,根本无济于事。但是怪异这个术语被认为是对人们所习惯于理解的身份、社群以及政治的最为混乱的曲折变异恰在于,它使得性、性别和性欲这三者的正常的统一变得具有或然性了,因此,造成的后果便是,对所有那些不同版本的身份、社群和政治都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尽管这些不同的版本被认为是从各自的统一体那里演变而来的。” [3](p99)这实际上也就道出了怪异这一产生于西方后现代社会的现象所具有的各种后现代和解构特征:在怪异那里,一切“整一的”、“确定的”、“本真的”东西都变得模棱两可甚至支离破碎了,因此怪异在这里所显示出的解构力量便十分明显了。
从当代美国怪异研究的主要学者的思想倾向来看,她们大都受到拉康和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前者赋予她们对弗洛伊德的“利比多”机制的解构,而后者则赋予她们以消解所谓“本真性”(authenticity)和“身份认同”(identity)的力量。身份认同问题是近十多年来文化研究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课题。在传统的女权主义者那里,女性与男性天生就有着某种区别,因而要通过争得男人所拥有的权利来抹平这种差别。但女性同性恋者或怪异者则在承认男女性别差异的同时试图发现一个介于这二者的“中间地带”。比如说,传统的女权主义者仍相信异性恋,并不抛弃生儿育女的“女性的责任”,而怪异女性则试图用“性别”(gender)这一更多地带有生物色彩的术语来取代“性”(sex)这一更带有对异性的欲望色彩的术语。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们的身份也发生了裂变,也即身份认同问题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和具有可讨论性:从某种单一的身份逐步发展为多重身份。这一点对怪异理论也有着影响,因此怪异女性也试图对身份认同这个被认为是确定的概念进行解构,也即对身份的本真性这一人为的观念进行解构。传统的观念认为,一个人的身份是天生固定的,而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身份即使天生形成的,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建构的范畴。对于怪异者而言,即使生来是一个女性,也可以通过后来的建构使其与异性恋相对抗,因而成为一个更具有男子气质的人。对男性也是如此,并非所有的人都必须满足于异性恋的,有的男人即使结了婚,有了孩子,照样可以通过后来的同性恋实践使自己摆脱传统男人的异性恋和对女性的性欲要求。因此怪异与其说是诉求身份不如说更注重对身份的批判。[3](p131)
美国怪异研究的主要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反身份的本真性恰恰是怪异所具有的潜在的民主化的力量:“正如身份认同这些术语经常为人们所使用一样,同时也正如‘外在性’经常为人们所使用一样,这些相同的概念必定会屈从于对这些专一地操作它们自己的生产的行为的批判:对何人而言外在性是一种历史上所拥有的和可提供的选择?…谁是由这一术语的何种用法所代表的,而又是谁被排斥在外?究竟对谁而言这一术语体现了种族的、族裔的或宗教的依附以及性的政治之间的一种不可能的冲突呢?”[5](p19)这些看来都是当代怪异理论家和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在目前的文化研究语境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性别研究和身份政治,而处于这二者之焦点的怪异无疑是他/她们最为感兴趣的一个课题。
怪异现象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出于对怪异理论的科学性的怀疑以及其研究方法的主观性的怀疑,一些学者还试图从遗传基因的角度甚至人的大脑的结构等角度来对这一现象进行科学的研究。
于是“怪异学”(queer science)也就应运而生了。在一本以《怪异学》为名的学术专著中,作者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来探讨这样两个问题:究竟什么原因使一个男人变成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的?以及谁又在乎这些呢?[6](p1)由于这样的探讨已经大大地超越了文化研究的领域和范围,我将另文予以评介。我这里只想指出,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大大加速,一些大城市已经率先进入了后工业或后现代社会,繁重的工作和学术研究压力以及自身的超前意识致使一些知识女性对异性恋冷漠甚至厌恶,因而女性同性恋的征兆也开始出现在一些知识女性中。因此对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也将成为中国的文化研究语境下的一个令人瞩目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Simon During.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2]Bonnie Zimmerman. Lesbian (A),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C). Michael Grodon and Martin Kreiswirth.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Annamarie Jagose. 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4]Teresa de Lauretis. Queer Theory: Lesbian and Gay Sexuality (A), Difference: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J). 3,2, ppiii-xviii.
[5]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r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6] Simon Le Vay. Queer Science (M).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6.
Gender Study and Queer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Studies
WANG Ning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Continuing its author’s previous work on cultural studies, the present essay offers a theoretic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feminism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studies. To the author, contemporary feminism has long shifted its emphasis from pursuing women’s social right and position onto the level of identifying themselves as female and constructing their own unique identity different from male. In the current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large-scale immigration and the obscurity of nati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enable gender study to develop in a pluralistic orientation. The main focus of contemporary gender studies is put on lesbian and queer studies, which have alread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domestic scholars and which will be further carried ou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urrent Chinese practice.
Key Words: Cultural Studies; gender studies; feminism; queer studies; lesbian studies
--------------------------------------------------------------------------------
[1] 针对文化研究的不成熟和“非科学性”特征,一些欧洲学者主张用“文化学”(cultural science)来重新定位文化研究。参阅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2005年6月10日在清华大学所作的演讲《文化研究和文化学》(“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Sciences”)。
[2] 我们完全可以从文化研究近十多年来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发展见出这一研究的不同区域特色。经过上述地区的学者与其他亚洲国家学者的通力合作,文化研究在亚太地区已经形成了一种“亚洲国家之间”的(Interasian)研究特色,完全可以和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进行平等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