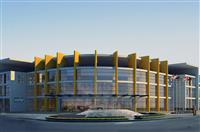
内容摘要:文学语言不仅塑造生动的文学形象来感染人,而且,其自身也成为对读者富有巨大感染力的、韵味深长的艺术形象。汉语形象则是指,建立在汉语基础上的语言形象。一方面,文学形象是建立在语言形象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语言形象具有自身的意义,可以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形成有趣味的对话关系。
把语言作为一个审美形象来理解和把握,也就是相信文学语言本身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不是像传统的文学理论所认为的,文学语言仅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和手段。在这里,我们讲语言的形象,指的是文学语言不仅塑造生动的文学形象来感染人,而且,其自身也成为对读者富有巨大感染力的、韵味深长的艺术形象。汉语形象则是指,建立在汉语基础上的语言形象。
1
与一般的文学形象相比,语言形象有着自身独特的存在形态和审美特征;与此同时,它也是文学形象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文学形象是建立在语言形象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首先要接触和理解的就是语言的形象,并通过对这个形象的感受和领悟,最终达到对文学作品中各种形象及其意义的想象和领会。另一方面,语言形象具有自身的意义,可以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形成有趣味的对话关系。
美国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的学者麦克列林(Thomas McLaughlin)对英国诗人布莱克的《羔羊》一诗进行了有趣的语言分析[1],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说明语言形象和文学形象关系的例子。在这首诗中,布莱克这样写道:
小羔羊,谁创造了你?/你知道吗,谁创造了你?/给你生命,叫你去寻找/河边和草地的食料/谁给你可爱的衣裳/柔软,毛茸茸又亮堂堂/谁给你这般柔软的声音/使满山满谷欢欣?/小羔羊,谁创造了你?/你知道吗?谁创造了你?
小羔羊,我来告诉你/小羔羊,我来告诉你/他的名字跟你一样/他管自己叫羔羊/他又温柔,又和蔼/他变成一个小孩/我是小孩,你是羔羊/咱们的名字跟他一样/小羔羊,上帝保佑你!/小羔羊,上帝保佑你![2]
按照麦克列林的分析,这首诗的语言表面看起来是那样的简单纯朴,是所谓的“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具有童真清澈的语言形象:“诗的说话者是个小孩,他正在与一只小羔羊娓娓细语,对它进行宗教启蒙。[3]”于是,童真语言的这个形象和诗歌中小孩儿、羔羊的文学形象相互钩连在一起,生成一种“天真无邪”的意义。这首先表明,这首诗歌中的语言形象和人物形象结合在了一起,人物形象的形态和意义离不开语言形象的形态和意义。
与此同时,麦克列林提到,这首诗“语言”和“形象”存在着一种不协调:一方面,小孩子的童真语言表明他和羔羊的天真纯朴,另一方面,这些“童真语言”竟然同时塑造了一个“仁慈但非常强大的上帝形象”,这是一个孩子的纯真无法把握的形象,从而和这个孩子使用的语言之间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违背”和“对立”的现象。换句话说,这首诗的语言形象和这首诗里面的人物形象之间存在一个叙事的张力,他们互相对立矛盾,使得这首诗的意义暗中发生着转向和变异:那种孩子的童真和纯朴,伴随了“上帝”这个形象的庞大和威严,从而显示出一种反讽的意味。孩子的童真和热情,也就变成了对权威的服从和认同的纯朴形式。用“纯朴”的形式而不是用思辨的形式表达对上帝权威的服从,从而强调了“上帝”的“仁慈”和“和蔼”,也就使得“上帝”变得更加容易接受和认同。
在这里,语言形象和人物形象都共同构成了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成为一个文本承载意义的两个重要层面。事实上,语言形象地分析,往往可以让我们进入到文本意义的那些复杂幽微的方面,得到比一般的印象阅读更多的感受。比如,在对这首诗的读解中,麦克列林就进而发现了“隐藏”在语言中更加复杂的意味。他认为,每个词除了自身的含义之外,都还包含着形成这个词的“有趣的历史”。从语言的审美形象这个角度来看,语词的语法含义虽然是相对固定的,但是,它在不同的历史语境的各种修辞用法所造就的意义,依旧沉淀在语词当中,构成了语言形象的微妙含义。这些语词中的各种微妙含义,也就会在作品中产生作用,影响到文本意义的表达。因此,在这首诗的结尾,麦克列林发现了这样两句话:
我是小孩,你是羔羊
咱们的名字跟他一样
小羔羊,上帝保佑你!
小羔羊,上帝保佑你![4]
其英文的原文是:
We are called by his name.
Little Lamb, God bless thee!
Little Lamb, God bless thee!
麦克列林指出:“最令人惊异的例子是bless(血)。‘保佑’即是以洒血的宗教仪式清洗某物。现在当我们使用‘保佑’时,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一意义层面,但事实却不可抹煞:这是一种修辞手段,其中blood一词的某些意义被转移到了施洗的行为之中。这与诗非常吻合,因为羔羊基督之间的主要联系之一是,二者都是血祭的祭品。”[5] 由此,这首诗变得具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危险和惊悚的意味,孩子充满热情和向往地向羔羊赞美的东西——上帝,正是以他们的血来祭祀的对象。这首诗的意味令我们始料不及:语言形象和人物形象之间的对立如此尖锐——而在最初的阅读印象中,语言形象正是为了“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
显然,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文学作品的语言形象,作为整体的艺术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具有独特的艺术美的价值,而且,它还和文本中的人物、场景形象一起,或者相互对话,或者相互对立、或者相互维系,共同参与到文学文本本意义的多元合唱之中来,造就丰富多样的文学审美景象。
基于此,文学语言的探讨,就不能能仅仅停留在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媒介和手段,还应该把它视为一种艺术形象,并细致探求这个形象的各个内涵层面。
在汉语文学的研究中,我们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汉语形象”方面。对于汉语而言,汉语形象可以分成汉语的基本形象和审美形象。在这里主要探讨的是从汉语的审美形象来进行探讨。
2
任何语言都必然以可见的实体呈现出来,因此,也就必然都涉及到形象问题。语言的字符形体、声音韵调等等,也就都构成了语言的基本形象。
针对汉语形象而言,这个特点更为明确。
首先,汉语作为一种确立在象形字基础上的文字系统,其形体形象是比较鲜明而有特色的。
有这样一个类似谜语的对子:
二人土上坐
一月日边明
“坐”这个字,其形体包含了“两个人坐在土上”这样一个想象性的场景;而“日”和“月”则似乎相互辉映,激发着“明”的感受。由此来看,这个对子显示了汉语语言的基本形象:汉语系统建立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汉字的形体本身就有“象”,可以激发人们的想象,带来趣味化的、甚至是美的的感受。
对于汉语的形体形象,古人也有过自己的认识。清代人刘熙载在《艺概》一书中,就曾经这样论及写字时的形体追求:
昔人言为书之体,须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状之,取不齐也。然不齐之中,流通照应,必有大齐者存。故辨草者,尤以书脉为要焉。
事实上,中国的书法作品就是以一种艺术的形式展现了汉语的这种来自形体的美。刘熙载所谓的“入其形”,就是指,书法的要义在于,写字时必须要揣摩透汉字的形体形象,令这种形体形象变化多端,各具风采。而“书脉”,则是指在这种形体形象的变化中,生成一种连绵不绝、回环往复的气韵。显然,刘熙载的这个说法,充分肯定了汉字基本形象对于书法艺术的重要意义,这表明,汉字的形体形象可以成为一种审美形象,产生生动的气韵。
其次,声韵,也是语言的一种基本形象。声音的变化往往蕴含着情感的波动,从而造就不同的汉语语音形象。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瞧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上,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6]
在这里,汉语的声音形象既包括汉字本身的读音,也包括对这个读音的具体读法。这就有了汉语声音的不同口吻、语气、节奏、韵律等等。相应地,这些声音就带上了语言使用者的情感,往往可以唤起听的人的形象化想象。比如我们常用的问候语“你好”:
北京人说“你好!你好!”时,“你”(nǐ)字还得加上一个-n尾,念作“您”(nín),“您好!您好!”就表示更加客气些,或者更加尊重些。人与人之间见面,已经完全废弃了旧时代许多虚伪的客套话,也不再是漠然不相闻问的漠不关心的状态……[7]
这里声音的改变,包含了一种人们生活状态的变化。而“你”和“您”,则蕴含不同的“人”的气息:“你”字指向普通的人,“您”字唤起“值得尊重的人”这个形象。
语言的声音形象是在语言的具体使用中呈现出来的,由此,“口音”(accent)就成了一种极其有意味的现象。而不同的口音则构成不同的语音形象,从而具有不同的意义。“以英国英语为例,其国内口音差异就形成了一整套谱系,从地域鲜明的乡村与城市口音,进而到那种被视为标准发音的典范口音,这种口音在BBC的‘世界报道’、司法系统、公学以及诸如此类的地方可以经常听到。从这个意义讲,每个讲话的人都有一个口音,包括习惯使用标准发言者。尽管标准口音现在基本上属于一种基于阶级地位的口音,但历史上它却一度与中古时期英格兰中部方言区的东南一带具有很强的地域关联,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对它的专门提倡,比如16世纪的英语公学以及BBC早期电台广播,有助于解释标准口音在今日联合王国的支配性社会地位,在那里它似乎成为中立的和通行的英语口音,甚至达到这种程度,即它已被当作讲英语的‘自然’与‘正确’的方式。”[8] 简言之,语言的标准音,本来只是一种便于通行的说话方式,但是,由于这种声音总是通过电台、电视进行传播,也就总是和“客观”、“公正”、“理性”、“权威”等等语言色彩联系在一起,从而逐渐成为一种具有社会和阶层内涵的文化形象:标准口音似乎意味着良好教育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为白领化阶层的象征。
显然,汉语的形象是伴随着汉语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渐确立起来的汉语本身的形象。当这种汉语的形象被审美使用时候,就有了汉语的审美形象,简称之为汉语形象。
3 事实上,语言的基本形象不等于语言形象。作为一种审美形象,语言形象呈现在文学作品之中,是文学语言的一种特殊形象。因此,我们讲“语言形象”、“汉语形象”,是要强调其审美形象。
也就是说,所谓语言形象,是在不同的使用方式中才能获得的;而语言的审美使用,则相应生成了一种极其具有魅力的审美形象。
因此,作为一种审美形象,语言形象是文学语言和普通语言区分开来的重要方面。按照这个理解,所谓语言形象,其实就是指呈现在文学文本中的汉语的审美面貌;它往往可以激发读者把语言本身当作审美对象,流连忘返,玩味蕴含在语言形象中的丰富内涵。
在这里,普通语言和文学语言呈现出不同的功能。普通语言往往注重于传递信息的功能,并不要求阅读者过多地注意所使用的语言本身;文学语言则恰恰相反,其功能不仅仅是要传递信息、生成意义,它还“努力”显现自身的魅力,让读者沉浸在语言本身的形象之美中。
美国诗人威廉斯的《便条》诗这样写道:
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们/大概是你/留着/早餐吃的/请原谅/它们/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凉
作为一首诗,这里的语言似乎和普通的生活语言并没有太大不同,无论是用词还是语气,都像是随随便便地说出的话。不妨把这一段话再使用普通语言的排列方式看看:
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们大概是你留着早餐吃的。请原谅,它们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凉。
表面看来,这两段话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的语言排列方式不同,这就造成这样一种感觉:按照文体识别的习惯,分行排列的是诗歌,其语言是诗歌语言;而不分行则有可能只是一张真正的“便条”。这似乎可以表明,语言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自身的形象,就无意中规定着语言本身的使用形态。
但是,是否分行并不能最终决定一堆语言材料是否就是文学语言或者普通语言。事实上,“分行”属于语言的一种“使用方式”问题,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使用语言,才能最终将普通语言和文学语言区分开来。
就生活中的真实的便条而言,这一组语言材料读起来有一点儿显得累赘,因为,写一张便条,只需要把这件事情交待清楚就行了:
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们大概是你留着早餐吃的。请原谅。
对于“事件”的交待,和“抱歉心情”的表达,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请原谅,它们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凉”,这一段话相应就成为真实的便条中可有可无的语言。甚至可以说,这一段话的增加不仅不会取得人家的原谅,反而会适得其反:我吃了你的梅子,要知道,它们太好吃了!这不是“斗气”吗?——好吃却被你吃了!故意的?
有意思的是,《便条》成为一首诗,就不能不“依赖”这一段似乎在斗气的话。或者说,失去了这一段话语,《便条》的审美意义就会消除殆尽。在这里,“它们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凉”,一方面表达的是“吃梅子”这个事件中的自我感受;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感受的表达,把“甜”和“凉”当成了违背契约和规范的“借口”。这首诗的意义就因此被凸现了出来:1,我知道吃别人的东西是错误的;2,可是我吃东西时的美好的生命体验也是合理的,为了这种生命体验的获得,我就可以违背我所了解的规范。
由此可以知道,这首简短的诗歌里面隐藏了一种矛盾:生命体验的合理性与尊重他人财产的合法性之间的矛盾。与这种矛盾相应和,这首诗显示了两种语言之间的对话,也就同时表现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形象:1,“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们大概是你留着早餐吃的。请原谅……”这是一组显现着“规范性力量”的语言,主要是对事件的叙述,具有逻辑语言的形象;2,“请原谅,它们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凉”,这是一组显现着“颠覆性力量”的语言,主要是一种情感体验的表达,具有感兴语言的形象。在这里,“甜”、“凉”两个字,构造了一个极其丰富的瞬间:那种任性的姿态与享受的感觉,一时间驻留我们心中。第1组语言的迟疑、惭愧,与第2组语言的流畅与情不自禁形成了极其有趣的对话。两种语言各自试图占到上风,但是,终于美好的体验性语言征服了我们,使得这首诗成为一种感性击退理性的象征。
显然,两种语言各自以自身的形象在积极地对话、交谈和渗透,成为这首诗的有意味的阅读现象。
由此可知,和普通语言不同,这首诗的语言中,不传达实际意义的语言更富有审美价值。这表明,文学语言不是以信息的传达为重要目标,而是要显现自身的形象,以这种自身形象的感染力来激动读者。
事实上,将自身显示为一种审美形象,这正是文学语言的独特意义。伊格尔顿曾经这样总结雅各布森的理论要义:
他认为“诗”首先在于语言被置入某种与本身的自觉的关系。诗的语言作用“增进符号的具体可知性”,引起对它们的物质性的注意而不是仅仅把它们用作交流中的筹码。在“诗”里,符号与它的对象脱节: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通常的关系打乱了,因而使符号作为一种价值对象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立性。[9]
所谓文学符号的“独立性”,事实上也就是文学语言涉及其自身的形象及其意义,超过了对文学语言所指称的对象的涉及。“当诗人告诉我们他的爱人像一朵红玫瑰时,我们知道事实上他是把这种说法纳入格律,我们不应该去问他是否真的有一个爱人,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他觉得像一玫瑰。”这表明,文学语言的理解在于对语言特殊的“谈话方式”的理解:“这种对谈话方式而不是所谈事实的集中注意,有时用来表示我们认为文学是一种‘自我相关’的语言,一种谈论它本身的语言”。[10]
简言之,文学语言总是使得语言独立地成为一种审美形象,就汉语而言,就是成为让读者玩味不已的汉语景观。
--------------------------------------------------------------------------------
[1] 周志强,1969年生人,山东滨州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
[1] 【美】麦克列林(Thomas McLaughlin):《修辞语言》(Figurative Language),载Frank Centricchia、Thomas McLaughlin编:《文学批评术语》(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中文本,张京媛等人译,108-203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2] 【英】布莱克:《布莱克诗选》,袁可嘉译,42-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3] 【美】麦克列林(Thomas McLaughlin):《修辞语言》(Figurative Language),载Frank Centricchia 、Thomas McLaughlin编:《文学批评术语》(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中文本,张京媛等人译,109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4] 诗中着重号为编者所加——编者注。
[5] 【美】麦克列林(Thomas McLaughlin):《修辞语言》(Figurative Language),载Frank Centricchia、Thomas McLaughlin编:《文学批评术语》(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中文本,张京媛等人译,115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6] 《乐记》。
[7] 周有光:《语言与社会生活》,2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
[8] 【美】约翰·菲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第二版),李彬译注,2—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9] 【英】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1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0] 【英】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