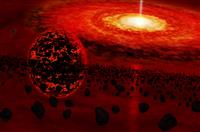(编者按)8月2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了纽约大学比较文学及东亚系教授张旭东的新书研讨会,与会的陈平原、崔之元、陈晓明、吴增定、张辉等学者就张旭东教授的《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一书展开了讨论。《21世纪经济报道》在会后对张旭东教授就全球化、文化认同以及中国发展等问题进行了采访。(特约记者刘晗)
全球化的普遍主义辩证法
全球化将几乎所有的封闭空间都打开,各国都没有什么大的回旋余地,使得各种文明之间直接面对的程度加深。
《21世纪》:你对全球化如何理解?
张旭东:在我看来,全球化不仅仅是指全球市场的开放和经济的交融。全球化的最根本的特征是一种空间意识的转变,也就是说,全球化将几乎所有的封闭空间都打开,各国都没有什么大的回旋余地,并且这种开放是对内在性的一种破解,是时空秩序和时空经验的一种全面的、根本性的改变。在文化-政治冲突的意义上,这里不再有“内”与“外”、“外围”与“核心”、“里屋”和“外屋”的区别,原先通过各种屏障予以隔离、遮蔽和缓冲的东西都直接地、赤裸裸地显现在彼此的面前。
一个直观的例子是如今各方争议的Google Earth电子地图。用这个软件甚至可以看到纽约或北京的任何一个街道、任何一个屋顶,这里就没有什么国界和围墙的限制。各个国家直接呈现在人们的目光之下。这种视觉和知识上的可能性可以为“文化比较”提供新视野,但也可以为巡航导弹提供精确打击的坐标。这就使得各种文明之间直接面对的程度加深。我想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维度。
《21世纪》:那么你是否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呢?
张旭东:当然可以从这么一个角度进行理解,并且实际上很多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是被动的,也就是说,被美国拖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但这么理解全球化容易陷入一个简单化的路径之中,不能揭示实际问题的要害所在。在我看来,这里涉及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问题。这也是黑格尔集中探讨过的问题。
黑格尔认为,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但任何特殊都不可能穷尽普遍的含义。换句话说,没有一种抽象的、实体性的、超越于各个文明和国家的一种普遍性,普遍性只能寄身于某个特殊的文明或者国家之上,任何普遍性其实都是某种特殊性的一种自我张扬和自我确证的结果。普遍主义是一种话语,而非实体。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未与他种文明碰撞的文明在根子上都是普遍主义的,比如中国的儒家文明,就有极强的“天下”观念,这就是一种普遍性。但西方的普遍主义的要害在于,它通过各种手段极深广的、深刻的挖掘出了自身特殊性中的普遍性,并且在将他人列为特殊性或者定性为“非文明”的过程中再次强烈的对自己的普遍性进行了确认。我认为全球化与美国化的问题必须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更好的理解。
中国认同
文化认同不是一个单单的文化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一个文化政治的问题,涉及到一个民族在世界对抗中的生存问题。
《21世纪》:那么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文化认同是否会受到冲击?
张旭东:这是显然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是被动的,是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内部分工之中的,同时也是在前面说到的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的支配之下的。对于中国的认同,显然会随着这种进程受到很大的影响。至少现在我们无法获得完全自主的一种价值认同,我们还在到别人的解释框架里寻找资源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和日常现象,并且这种状况随着全球化的“无可遮蔽”的特征而更为明显。说到底,文化认同不是一个单单的文化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一个文化政治的问题,涉及到一个民族在世界对抗中的生存问题。
《21世纪》: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文化认同之间是什么关系?有学者认为中国在21世纪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那么这是否有助于中国的文化认同?
张旭东:现在中国人谈文化认同问题都要谈到经济增长的问题,这涉及到一个民族自信的问题,也是一个实力的问题,比如在谈论大学改革的时候就涉及到经费的问题,涉及到新经济精英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互动关系,这些不可能离开经济增长。从正面关系来讲,是中国人比以前自信了,说话腰杆儿硬了,但从反面来讲,我们现在说的中国文化-政治的各种危机跟经济增长也有关系。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果可能是被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格局之中,沿海的经济精英越来越会跟世界经济有体制性的接轨,知识精英和专家型官员会跟全球的体制性的市场有一种联盟、一种认同感。这种世界市场接轨式的认同感跟我们所说的文化认同是有内在的紧张、冲突和矛盾的。中国的文化世界或者生活世界于是随着经济的崛起而处在一种内部扯裂的状态。因此经济增长本身就从正反两个方面把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的危机推到了前台。
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中国经济总量上的增长,在客观上使中国在各个向度上扩张,其含义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不仅仅是人文知识分子,专家型官员也在考虑这样问题,比如能源配置、市场开拓;普通的中国人也在日常经验的层面上不断地在修正自己对作为时空存在和价值存在的中国的理解。作为一个崛起的经济实体,中国必然要考虑地缘政治上的重新安排,比如跟东南亚的关系怎么摆、跟中东的关系怎么摆、跟南美的关系怎么摆。这种地缘政治和国家影响力的改变肯定会反映到文化人的认同意识里面来。
但如果我们看人均意义上的财富增长的话,中国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只是处于集体脱贫状态,这就会造成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各自对于中国的表述不一样。这样在中国这个巨大的符号下面,实际上你的认同不一定是我的认同,虽然都是中国,但你的中国和我的中国完全是两回事,社会分层十分严重,是韦伯意义上的“社会领域的分化”(differentiationofsocialsphere)。
对此我有一个个人感受。这次在北京我和一个朋友去京郊潭柘寺游览。这是一个很美丽、很有古典气息的地方。但一路下来,感觉很复杂。我当时就想,要是能从长安街直接空投到那里,大概是最好的,这样既能享受全球化、又能享受传统美。但我们是开车去的,经过石景山垃圾处理场附近的一片民房,我们感觉到从城东出去一点、开车不到二三十公里就会看到那种城乡结合部的破落,那里烟尘弥漫、房屋破败得也许还不如内地的乡村,完全是一种人在灰堆里打滚的感觉,十分难受。在三年前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跟学生座谈的时候,有学生就说,你替中国操心,但这个中国不是我们的中国,什么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等等,跟我们这种从底层出来的人没关系,我们是从农村来的,而你谈的是精英们的中国;你们去跟美国争好了,跟我们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没有关系。
“中国”概念的面孔
我们没有一个静态的五十年,我们不能在一心发展经济的同时,把自己的存在设定在一个价值的真空当中。
《21世纪》:你的意思是说大家现在对于“中国”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产生了分歧?
张旭东:这是最有意思的。北京郊区或许很像印度,好像过去25年的现代化完全没有触及的。但我转念一想,或许最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在于此,如果这些京郊的人都活得像中产阶级一样,中国经济也就没什么潜力了。底层人们有一种为了生活什么活都可以去干的劲头,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内部分工意义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还可以提供50年,50年不计成本的发展。但在这50年中世界会发生很多我们今天难以逆料的变化。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我们没有一个静态的50年,我们不能在一心发展经济的同时,把自己的存在设定在一个价值的真空当中,价值的连续性和国家政治的连续性一样,都是一刻也不能中断的东西。这就当代中国文化政治问题的急迫性。
中国的有趣之处在于,“中国”这个词之下包含了好多层的意思。打个比方,过去讲权利都是说一个权利什么的,但崔之元他们说这是一种“权利束”,是公民权、私有财产权等等的一捆。“中国”现在也是这么一捆,有的人认同这一束,有的人认同那一束,好的理论应该能够容纳中国这个语词之下的杂多的可能性。即使你没有办法满足他们,也要为他们留出空间来。
21世纪》:是不是像你这样海外归来的学者从理论层面对于中国的把握和内地的有部分经验的学者对于中国的理解有一定的偏差?
张旭东:我觉得海外回来的学者与北京、上海知识界在对中国的认识上有差别,北京、上海知识界和内地知识界对中国的理解也有差别,我认为这是一样的。中国的内与外不能以民族国家的边界来衡量这种差异,中国的真正的内与外的差别可能不是在国界上,而是在中国内部。中国真正的边界可能不是在你从美国进入香港的时候,而是在于你从深圳到广东其他区域的时候,或者从北京市区到北京郊区的时候,这内部一层一层的边界都是很实实在在的。在这个意义上,从美国回来可能并不是跨越了什么边界,好像与北京、上海的知识界就有那么大的差别,难道北京、上海知识界到沂蒙山老区就不存在内与外的问题了?
《21世纪》:有人说你的新书虽然对西方的普遍主义进行了历史批判,但只是在讲西方,没有谈中国,比如就没有谈中国儒家的普遍主义的传统以及其在当代的作用,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旭东:我想这种批评的前提是只有儒学才是中国,只有这个帝国文明传统才是中国。但如果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那么这种问题就是伪问题。就算我们暂且接受这个前提,我们也不妨想想,近代中国是如何一步步从儒家天下观点走到了今天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究竟是较晚近的传统主义思想更“中国”,还是较早的东西,比如乾嘉学派的东西更中国。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在“回归传统”或“做中国人自己的学问”方向上能够做什么,不在于多大程度上同早先的国学形态相媲美,而在于我们如何在我们自己的历史性中回答了前人没有能够回答的问题,做出了前人没有能够做出的选择和判断。老祖宗并不需要我们去重复他们早已说过的东西,更不需要我们去重复他们经历过的失败,而是期待我们做出他们没有能够做出、也不可能做出的事情来。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可能性并不是因为我们比老祖宗聪明,或在国学上达到了超越前人的修养,而是因为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境遇做出自己的回应。我们必须问的一个问题是,建国后的革命传统以及社会主义是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传统是不是中国的?如果这些都是中国的,是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那么就必须追寻它们背后的理论逻辑,就必然进入西方的现代性经典,所以我才去探讨康德、黑格尔、尼采、韦伯等等。这里面都有一种中国的关怀,而不仅仅是在厘清西方的逻辑。
《21世纪》:甘阳先生在最近的演讲中谈到了三种传统的融合问题,你怎么看?
张旭东:首先我认为,中国的传统确实是断裂的,1990年代跟1980年代断裂,1980年代跟“文革”断裂,“文革”跟十七年断裂,新中国跟旧中国断裂,旧中国里面1940年代跟1930年代、1930年代跟1920年代都是断裂的,再往前还有晚清跟民国的断裂,没完没了的断裂。因此,我觉得甘阳的说法是很强硬的,他把建国以来的传统、改革开放的传统和帝国传统通通勾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在大的立场上,我完全赞同,但问题在于操作性的细节上,具体到处理自己的社会历史经验的时候,更具体到文学史、思想史上,如何在具体的层面上把这些断裂进行勾连,这十分困难。
中国文化认同的指向
我们的大国传统,包括以语言、习俗和伦理关系为依托的生活世界的延续,悠久的历史。
《21世纪》:在21世纪做中国人,我们的认同资源的可能性有哪些?做中国人到底认同什么?
张旭东:这个问题当然需要大家来说。但我觉得可能还要回到中国革命。我觉得中国革命可能是世界近代史上唯一的一个例子。你去读日本学者的著作,比如竹内好,他们就觉得日本的现代化并非一个重建文明的主体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真正优秀的日本知识人士都有这样一种自我批评。中国的革命是通过一种非常本土、非常民间、非常有传统意味的一次变革,西方现代性内部对此只能按部就班来完成一个转变,但中国用另外的方式一下子做到了,这属于那种千年一次、有创世纪意味的一个事件。
我这里并不想把中国革命神化,但是它确实有其不可思议的一面。如何把这种资源一点一点的重新领会过来,对于我们父辈和祖辈来说这些不言而喻的,而对于我们而言又是些陌生的东西,需要重新把它“读”出来,这个可能是中国人当代自信的一个最为直接的源泉。
说白了我们都是新中国的产物,一出去你就会发现我们待人接物的方式、思维方式、语言的模式(包括身体语言),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文化上的一个独特现象来看的时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中国大陆出去的中国人跟海外的华人群落是完全不一样的,唯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就是美国人。我们所称之为“美国佬”的美国人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一群外国人之间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个是美国人,他的走路的样子、说话的语调、思维方式、感情方式等等十分独特。中国人也有这种独特性。这表现为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对自己的尊严不容侵犯的感觉。中国人一方面很谦卑,并没有说我一年挣一百万就觉得我这条命比一般的人值钱,另一方面,在骨子里时时刻刻能够看出来一种平等的激情,很多世界其他的民族所不具备的一种特征。其他民族很抽象的东西在中国人这里非常非常具体。
另外,中国人对未来非常乐观。你找不到一个其他的民族对自己民族的前途如此乐观,一个泰国人来中国就会纳闷,你们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这么一大堆问题还怎么活下去,但中国人却总觉得明天总会更好,五年以后十年之后定然烟消云散,这种乐观的态度不能不说跟50多年来的历史进程有关。中国人办很多事情,有一种只能成不能败的气势,后来就成了。你看其他的地方的,比如东欧、阿拉伯等等,特别是印度,它们对西方只有失败的经验,它们的独立是一个偶然的妥协,而中国是一路杀出来的,我们可以认同的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争取到的,没有任何东西是别人施舍的,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从理论上讲很成问题,推到抽象的哲学意义上就是唯意志论(voluntarism),是“人定胜天”、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气势。这个东西是没法讲理的,这是种自我肯定。别人可以问,你凭什么这样?但中国人可以回答说,我就这样。
最后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的大国传统,包括以语言、习俗和伦理关系为依托的生活世界的延续,悠久的历史。可以说,只要中国的国家形态尚能维持,文化中国就仍然有回旋的余地。有时候这只是一种幻觉。但这种幻觉是必要的,不能把它随便消解掉。没有的话我们还必须把它再造出来。西方人也有这种尼采说的“必要的幻觉”。近代西方不但靠这种必要的幻觉支撑了好几百年,而且还从中生成了一些实体性的东西。我们也同样需要这种精神力量。中国古人认为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代中国人一方面固然应该重新去领会那些“经”和“义”的普遍内涵,但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在偶然性、主体性的内在空间里把价值的世界理解为意志的行动。在最后一层意义上,我们比古人多了一种自由,但也多了一份意识的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