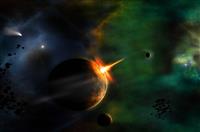
写下这样的文章名字,肯定要冒风险,这就应了人们对玩弄词藻的指责。很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于避免使用这种修辞,可是面对严歌苓的小说,我还是禁不住地破了自己的戒律,没别的,就是因为这是一种感受,一种阅读时无法割舍的感受。写作书评和阅读已经带有职业的麻木,通常情况下很难被感动,很难被文字之力所击倒。我所说的感动当然不是什么情感之类的东西,那种感动已经很难伤害我,或者稍纵即逝,或者很快便看穿作者的技俩。我说的是一种文字之力,那种书写怎么就那么强劲?那么不留余地?就象舞蹈,你看不到舞者,也看不到舞的破绽,这就使职业看客受到了伤害。
很显然,《花儿与少年》(昆仑出版社,2004)看上去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简朴得有些粗糙的装帧,总共12万字,定价也不过15元。它的规模与份量在这个宏大著作铺天盖地的年代,无足轻重。要作为一部轰动一时的作品,或要“划”一下时代都没有任何可能。可是这部小说却让我感动,我说过是那种文字之力击中了我。
实际上,很久以来就想写写严歌苓,但看着她那一大摞的书我就知难而退,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找不到要领。数年前,在一次作品讨论会上第一次遭遇她,隔着会议桌,很难看清她的面目,给我的感觉,就象在北京看着多伦多或洛杉机一样。我真不知道我何以有这种感觉,她那么抽象,如同历史或未来,就是不在此在之中。很可能是她长期旅居海外,她始终是与另一个时空场域相关,这使职业阅读者对她的把握茫然而缺乏直接性。
然而,书写会唤起一种东西,那是最直接的文字之力,文字所练就的舞,真是如羚羊挂角,却又有迹可求。书写有一种踪迹,一种力的踪迹。文学书写变成文字的书写,我想这就到了一种写的境界。
当然,这是小说,不是诗,它是叙事文体,而且是相当典型和标准的叙事文体,问题就在这里,它是叙事文体却能写出一种文字之力。这本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也不奇特。它讲述一个曾经是某芭蕾舞剧团主角的华人女子嫁给一个大她三十岁的美国退休律师的故事。这个女子到了美国已有十年,她的女儿四岁就跟她远嫁重洋,现在也长到十四岁了。儿子十四岁到美国却怎么也融不进这个中产阶级家庭,到了十七八岁终于离家出去打工,成为一个送外卖的小苦力。小说写的是新一代移民的生活辛酸,这个辛酸不再是肉体上的和经济上的,而是精神和内心的困境。小说同时描写了美国富裕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要融入这样的家庭,是所有中国移民的梦想,然而,这样的富裕中产阶级家庭却也是问题重重,在这里,小说就不单是写所谓的移民生活,而是人性,文学永远不能摆脱的写作深渊。
当然,小说的主角是那个叫做晚江的女子,年轻时可是芭蕾舞主角,多少人在台下看得眼都直了,没想到她就嫁给一个极平庸的伴舞者洪敏。他们在筒子楼的五层拉上一个花哨的窗帘,他们的婚姻就在一个窗帘背后展开。这原本是花儿与少年的一对,却经不住生活磨损。那个洪敏永远是生活中的倒霉蛋,他们成为这个剧团最后要不到房子的一对夫妻。生活可以击跨任何曾经美妙的事物,这一对舞伴夫妻,女的去开了一家餐馆,男的也被分流去干杂物。男的还是失败,女子却练就了一手厨艺。但落魄的生活并没有影响他们相濡以沫的感情。一个偶然的机遇一个刘姓的华侨相中了她,男的居然大义凛然劝女子嫁给刘姓的退休律师。这样,女子便可以享受荣华富贵。这个叫晚江的女子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听从了丈夫的建议不得而知,而丈夫又是如何能够割舍夫妻情分也不得而知。总之,这个女子就这样远嫁美国,嫁给一个已经七十岁的退休律师。每天早晨,晚江起床跑步,那是她偷着与不成器的送外卖的儿子相会的时刻,儿子九华会带来一罐豆浆给母亲喝。后来故事中出现了另一个人,洪敏,二年前他通过一个旅行社来到美国,十年夫妻没有见面,他们每周偷着通电话,真是情真意笃。洪敏还在想着发财,他以买房子的名义不断从晚江那里要钱或借钱,买一幢房子,安一个大浴缸给晚江。可想而知,他遭遇彻底失败。平心而论,小说中的那个瀚夫瑞是个好人,极富有中产阶级修养。在这部小说的封面所做的内容提示中,他成为这部书的主角:“十年前,他把晚江娶过太平洋,娶进他那所大屋,他与她便从此形影不离,他在迎娶她之前办妥退休手续就为了一步不离地与她厮守……,有时她半夜让台灯的光亮弄醒,见老瀚夫瑞正多愁善感地端详她,如同不时点数钞票的守财奴,他得一再证实自己的幸运。”这段话看上去象是在讴歌一对老夫少妻的美妙婚姻,就其表面现象而言,这段话的概括是恰切的。就对老瀚夫瑞的心理品性的描述而言,也很到位。瀚夫瑞对宽容而有修养,就是他发现了晚江与儿子九华偷偷相见,也宽谅了晚江的所做作为。问题在于,这里面每个人都按照他的情理生活,甚至都没有恶意,但这个家庭的建构,这个生活场所却是包含着深刻的伤害。
伤害并不是严歌苓在这本书中要描写的主题,实际上,它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副本产品,不经意给予的连带责任。 这本小说也许就是看一下表面平静幸福的生活背后藏的故事。晚江被描写成一个绝对善良,忠贞的女人。她显然是被放置到一个生活困境,她的忠贞与背叛被紧紧栓在一起,成为一对生死相依的孪生姐妹。她对洪敏的忠贞,就意味着对瀚夫瑞的背叛;她对瀚夫瑞的忠贞就意味着地过去的背叛。她已经剧成祥林嫂式的二段。这个女人依然旧情难忘,这倒不是出于什么深情或道义,而只是生活是如此坚韧地延续,她本来就没有从过去的生活延续中离开。这种书写是令人惊异的,她从中国到美国,换了一个丈夫,就象出去郊游一样,或者说就象一个出租的物品,她知道她终究是要归还的。她依然在情感上没有任何变化,那么自然地延续着过去的婚姻史,她与洪敏每周的通电话,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的情感和关切,他们见面时的那种情感心理,一如既往,生活如此大的变故,美国的生活场景,都没有影响她对前夫的感情和态度。她真正就象一个典当出去的妻子,她的心自然地属于她过去的历史。她对瀚夫瑞的不忠,决不是有意背叛或伤害,没有,对于她来说,这一切是天经地义的,是自然而然的。她的灵魂,她的心灵,她的精神,还是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中。现在不过是外形,不过是表象,生活的本质,内涵没有变化。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源于爱,因为爱才产生忠诚与背叛。一个如此为爱所注满的女人,却如此深地陷入忠与不忠的困局,小说对人物存在命运的把握无疑是相当巧妙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小说的故事或内容,都是叙事方面的东西。我写作此文的初衷是为那种叙述,为那种文字所感动。但直到现在,我也无法进入到文字层面谈论——这一层面的谈论几乎是不可能的,文字,文学的书写本身只能感受、体验。说到文字,我们以为那是小说的语言之类东西,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那是由小说叙述与文字形成的一种力道。除了文字之力,我无法找到其他的字词来表达它。阅读严歌苓的这本书,始终感觉到文字有一种舞的动能。当然,这种表达都是比喻性的,相对于其他的比喻来说,对它的表达,又都是比喻的比喻。
事实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形容词,例如,饱满、韧性、张力、韵律……等等,这只是一些关于文字之舞的外在比喻。当然,文字并不是单纯的符号,它的能量总是受到它所包含的意义的内驱作用。就这一点而言,德里达的寻求的纯粹的文字的延异性也必然要在一个时间之点上停留下来,当然没有无意义的文字。我们只能理解为文字与叙述同谋,叙述在文字的背后起支配作用。那些生活的伤痛和伤害都被当作副产品来处理时,文字本身就获得了一种力,它可以如此不顾及它所划过的生活创伤,还是一如既往地向前推进。严歌苓是真的那么铁石心肠,还是刻意如此?不管如何,它笔下的文字就以自然而天真的形态展开,它的叙述还是那样舒畅地展开,那里藏了那么多东西,它/她从来不露声色。这真正令人惊异。看看她的叙述,怎么一个人一个人是那样出场的,那个故事是怎么毫不在意就抖出了那么些生活中的死结。每个人的出场对于晚江来说,都是困局。她跑步跑得好好的,怎么就出现了九华,她的不成器的同样也是绝望的儿子。她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富婆的悠闲自在的且有点奢侈的晨炼,怎么就变成钻进那辆破车与木纳的儿子相会呢?她喝下那又香又甜的豆漿,这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场面:“然后她站在那儿,看九华的卡车开下坡去。她一直站到卡车开没了,才觉出海风很冷。回程她跑得疲惫沓沓,动力全没了。”(参见《花儿少年》,第15页)这一切都是客观冷静的描写,严歌苓从来都未置一词,由它们去吧——这就是存在之本来事相。小说几乎已经写到快三分之一的地方,那个前夫洪敏才真正出现,一出现就拖出了巨大的尾巴。藏着这么大的事,严歌苓也能谈笑自如,正如晚江的生活也并没有因此有多大变化——她本来,她一直就是这样生活。她的生活一直就藏着狐狸的尾巴。严歌苓的叙述就这样一点一点往外透,把里面的东西象挤牙膏一样不动声色往外挤,但生活不可克服的崩溃就这样不知不觉造就了。这样的文笔无疑是惊人的。晚江是这样凭着惯性往前走,就象走向雷区,她就此引爆了一个又一个地雷,但她没有停止,甚至没有回过头来看看,那就是她的生活本身,她本来就是走在这样的道路上,这就是她的命运之路。
她的叙述就象狐狸在玩的把戏,藏得神不知鬼不觉,一点征兆都没有,一点酝酿也不需要,就那么不经意地透露出来。严歌苓真能说故事,那么松驰却又富有紧张的韵律。她知道她有的是货色。那里面藏着晚江的全部生活史,只要出现一个人物,就带出了她的一段暧昧或诡秘的历史,晚江从来没有觉得她的生活有什么绝望之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以本来的方式存在。而生活的演变却使得原来的单纯性事件,变得阴暗而不可理喻。晚江与洪敏整整保持了十年的通话,就好象晚江是在老瀚夫瑞家里打工或做佣人一样,而洪敏还是她真正的丈夫。这就使前夫让她嫁给“老人家”象是一个阴谋,最后冷不丁冒出那句“再等十年”“最多二十年”的话?歉霰?扯?呱械脑都拗匮螅?拖笫且桓鲆跄绷耍???吹纳?孓限我部赡鼙涑苫拿?囊跄绷恕U庹媸鞘剂喜患暗模?饩褪茄细柢咝鹗碌谋玖欤??诓恢?痪踔邪巡啬涞哪侵缓?攴帕顺隼础K?故且涣车恼娉希?涣车奈薰肌U飧鲂鹗霰纠淳褪浅雇烦刮驳暮?晖娴陌严罚??允?愕男鹗觥?br> 由此就不难理解这个平常故事的魅力,就只是一些家庭琐事,一些老夫少妻之间的忠与不忠的日常生活,甚至无聊的吃饭还占据了那么多的篇幅,但小说就是吸引人,就是有一种磁性。它在平静的外表下,让人性每时每刻都经受考验,让心灵时刻都处在裂开的状况。仁仁和路易,这也是“花儿”与“少年”吗?再看看那个苏,瀚夫瑞前妻的女儿,一个失败的酒鬼,她独处地下室,喝光了养父珍藏的所有的名贵的酒,醉眼朦却看到这些体面生活的真相:这些人生活得真累,满心地狱,却整天在无动于衷地微笑。在这个完整近乎和谐的家的生活场域中,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那样正常又那样残缺,那样平静又那样随时面临崩溃。我要说的依然是,严歌苓轻而易举的叙述,她使这一切象水流一样无目的又执拗地向前流失。
评论家李敬泽在为本书作序时写道,严歌苓写作这本书,一定想到曹禺的《雷雨》,他是敏锐的。这个文本确实存在与《雷雨》的某种相似之处,这可能出于偶然,关于家,关于家内部的伦理冲突,这是无数的经典文本反复在演绎的故事。后来的文本永远无法摆脱经典文本的阴影。但是,我也在想,严歌苓的写作融进了非常充足的个人体验。数月前,在一次偶然观看电视节目时,我看到香港凤凰卫视做的一个访谈节目,可惜只看了临近结束的一小片断。我得庆幸偶然看到这个场景,这使我在理解严歌苓的写作时,多了一层参照。那是座落在河边的一幢漂亮房子,严歌苓在家门外的路上奔跑,据说她天天坚持长跑,她的年长些的外交官丈夫正慈爱地看着奔跑的背影。这些场景在这本小说中也不断出现,而且严歌苓早年也是一名出色的芭蕾舞主角。很可能是她玩的诡计,她会躲在晚江的身后看看人们作何联想。幸福得一塌糊涂的她也可能是出于游戏精神。没有人会把她与晚江混同起来,但她并不害怕这种混淆。她为什么要以如此贴近的方式写作?这也不只是好玩,我更愿意认为,她是个用心在写作的人,她要用她最熟悉的经验作为原料,她在把自己的心打碎,再安到晚江的身上。她可以与她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这就可以理解,那些文字是如何自然而执拗地向前伸展,就象她在家门前的路上奔跑。
200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