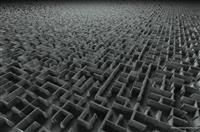故事:1983年8月12日,我第一次在《解放军报》“外军了望”栏目发表了一篇《海因里齐的防御战术》,随后多次在这个栏目和学军事专栏发表译稿。我至今还能记得军报的老编辑曾光军鼓励我说:“你写的东西我们很欢迎,栏目现在就缺这样的稿子。”这时,我的兴趣已经转移到了理论研究上去了。
观察:在不很壮大的国内新闻学术界,80%以上的学人关注的是国内问题,看的是中文出版物,而这个学科80%以上的资源不在中国。这种人力资源的严重不合理配置势必妨碍我们这个本应“得风气之先”专业的健康发展。
建言:媒体的首要功能是进行环境监测,并把观测到的东西告诉公众。监测是不是及时很重要,当今社会科技发达,人类文明发展很快,但任何社会都不能避免天灾人祸,如果一味排斥负面的东西,媒体就是失职。
论点:坚持媒体的社会公器论,构筑公众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制定和恪守严格的新闻专业标准,反对媒体公司论和集团工具论,抵御不良政治和经济势力的对媒体的腐蚀。
展江:励学敦新行
初识展江,可能会对他的面无表情产生误解,似乎他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然而交往开去,渐渐感觉:他很坦率,不会掩饰自己的好恶喜怒;他亦很严厉,甚至有些苛刻、不近人情,对学生的错误、同事的失误都会有错必纠,绝不姑息;同时他也很热忱,对求教于他的学生,哪怕是校外只有一面之缘的小字辈都会不遗余力地指教,尽可能地提供便利条件。这正像孔子所说的:“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在为人和治学上,他都显低调,不喜张扬,在派别林立的学术界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清醒的头脑、独立的精神……军旅生涯使他的腰受伤,上课时间长了,他经常会停下来,用手捶捶腰。当有人夸他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术上的砥柱,他会说:“我的腰不好,不能抵什么东西”。
“作为新闻传播学最高学位获得者理应抛却浮名,多做实事”
王永亮:古人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对自学成才的人来说,这句话太消极了,而是相信“转益多师是吾师”。作为一名从退伍军人到自考生,从硕士到博士的艰难跋涉者,您是如何理解“转益多师是吾师”这句话的呢?
展江:这要从早年经历说起,1976年冬季,我从家乡扬州参军入伍,在东海舰队舟山基地当兵。服役期间曾在海军后勤学院学习财会专业,获得中专文凭,回部队后当上了会计,后来又调到团里当新闻干事。一直到1984年发现脊椎有伤病,在部队医院里治了大半年未得痊愈。1985年,我转业到地方的时候,兜里只揣着一张三等伤残军人证,开始了全新的征程。
9年的军旅生活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也许并不算长,但在这9年中,我从不谙世事,到初步确立自己兴趣和钻研方向,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认老乡、拉关系,当别人推杯换盞,把酒言欢时,我总是埋首苦读,学英语、学军事史藉。无论将来是否一直从戎,有一点我非常明确,那就是学好英语。现代战争需要更多地了解外军动向,掌握最新的国际态势,这一切无一不需要通过英语作为工具和媒介。
我虽然1974年就高中毕业了,但由于受到“十年动乱”的影响,学到的知识少而零碎,而且那个年代的学习资料极少,我只有从母亲在图书馆工作的一位同学那里得到了一本薄薄的《英语语法手册》,花了两三个月把这本书抄了一遍,后来又买了一本《基础英语教程》。在接下来的五六年时间里,我手里只有这两本英语教材。在海军基地,我抱着一本英语字典和这两本书,一页页地啃着,就这样度过大半的业余时间。当时还有很多人对此表示不理解,认为一个当兵的,练好身体习好武就行了,学什么英语呀,又不出成果,这不是“不务正业”吗?可是很快我的英语水平在所在部队就无人能比了,否则我的团政委也不会让我给自己上中学的儿子补习英语。所幸的是团政委把我调职去做新闻干事。
钱婕:真是像前两年谢晋所说的“知识改变命运”啊!
展江:因为为所在部队甩掉了新闻报道“光头”的帽子,我多次被东海舰队和舟山基地评为新闻报道个人先进奖;但是尽管我一年能在《解放军报》上十篇稿件,由于所写的多半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新闻报道(多为编译的外军动向),因此只能拿二等奖。而当时有的基层部队规定,在军报上一篇文章能立一次三等功。1983年8月12日,我第一次在军报“外军了望”栏目发表了一篇《海因里齐的防御战术》,随后多次在这个栏目和学军事专栏发表译稿。我至今还能记得军报的老编辑曾光军鼓励他说:“你写的东西我们很欢迎,栏目现在就缺这样的稿子。”这时,我的兴趣已经转移到了理论研究上去了。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渐渐发现在生与死角逐的战争中,有一种日新月异的武器大显神通,这就是新闻媒介。无论是拿破仑的“报馆一间,犹联军一队也”,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德皇威廉二世哀叹“德国之战败,就在于没有一张《泰晤士报》”,说的都是新闻媒介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新闻与战争,这个全新的课题在我头脑中渐渐清晰。
王永亮:新闻与战争?我记得我刚从事新闻工作时,正逢1991年2月海湾战争打响,不久,我在书店买到一本《新闻与战争》,印象最深的是两位作者的名字都有“江”字,没想到12年后竟然见到了真正的作者!
展江:作者就是我和杨鲁江(我当兵时的战友、图书馆的同事)。当新闻研究者们对海湾战争中美国CNN一枝独秀的表现目瞪口呆,感叹新闻媒体在战争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时,这本书的末章及时讲解了新闻媒体是如何作为一种特殊的战争手段被交战各方加以娴熟运用,从而显示出空前的威力的。虽然这不是一部论著,但却是较早对战争与新闻结缘现象加以揭示和描述的专著,是在军事历史学和新闻学之间搭桥的一次尝试。
钱婕:从您的人生履历看,9年的海军生涯转业后,您还从事过8年的新闻工作,这段经历对您有何收获?您眼中“好新闻”的标准是什么?
展江:我认为好新闻的标准是:在纷纭世事中厘清复杂关系,摆脱流行偏见,表现职业勇气,揭示事实真相,揭露谎言谬论。
我在1986年中进入《扬州日报》,做起了与“潦倒文人”打交道的副刊编辑,而自觉远离被许多人认为风光和实惠的政治和经济记者岗位。我多年来就渴望这种不用坐班的职业,符合自己的天性。20世纪80年代是新闻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当副刊编辑也得从事采访,何况一年后副刊组升格为文艺副刊部,成为报社版面最多的部门,我也在不太情愿的情况下做了副刊部主任。每周除了8个版面的编稿、审稿和值夜班以外,还要经常采写星期刊的头条,其劳累可想而知,但是这些年的新闻实践,与在部队做过的新闻工作相比,无疑有更多的挑战性,我曾因批评报道引起风波,曾因决定刊登一封控诉信而险些吃官司。我写的《谁最先报道南京大屠杀》等通讯作品在省内和全国获过奖。回想起来,我的新闻业务基础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
钱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新闻事业蓬勃发展,记者行业令人艳羡,而考研是了冷门,是苦差事,您为何“逆潮流而动”实现转型呢?是蕴藏在心中的读书情结吗?
展江:百姓的孩子多读书,读书情结当然有。当时,在新闻改革大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下,我迫切感到有必要系统地学习新闻理论,好梳理出纷乱复杂、热闹喧嚣的新闻业界现状,我想到了考研这条路。但是要想在大专学历的基础上直接考研究生,困难可想而知,何况这时已经娶妻生子,家庭负担和工作压力都是很现实的牵制。1990年第一次考研我失败了,总分进入前三名,败就败在单科成绩上。可是我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这时,我已经34岁了,是同学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儿子都已经上了小学。
与同学相比,我的学历起点也算是低的,但是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长期自学锻炼出来的独立思考能力又成了优势。有同学问,这把岁数了为什么到人大来?我回答道:不为跳槽、发财和逃婚(当时的典型考研动机),只为了满足虚荣心——进大学门。凭着始终如一的刻苦钻研,我硕士毕业后顺利地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童兵教授。
王永亮:翻阅您的学术著述,最明显的感受是您近几年致力于西方先进传播理念的翻译引进工作。众所周知,搞翻译辛苦且不去言说,还被视为费力不讨好,译得再多再好不算科研成果,稿费也低。在跟风追名逐利的新闻学界,能够静下心来,花点时间,有具有相应能力来熬在书桌前翻译几本有价值的原著的人寥寥可数,更多的人宁肯有时间弄点“短平快”,攒点什么书就成“专著”,耗时少,效益大,何乐而不为?而您却为何又乐此不疲地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展江:对照国内外的新闻学术研究,我感到国内缺乏必备的研究文本,尤其是西方新闻传播学大师的原著、相关语境材料及经典作品。要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其内涵,困难重重。所以我撰写和翻译出了《美国新闻史》、《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新闻与揭丑》、《正义与勇气——世界百名杰出战地记者列传》等书。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那本洋洋百万字的《美国新闻史》。由美国当代新闻史学家埃德温•埃默里和迈克尔•埃默里父子以及南希•罗伯茨士所著《美国新闻史》在美国已出了第八版,国内1982年第一次翻译过一个老版本,原作者很多观点的发展变化得不到及时修正。我作为主译者,与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多名译者一起翻译了第八版。这本书同时还创立一项国内纪录:由同一个出版社出版新闻与传播学著作的第二个译本,并是本专业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本。
新华社原先是让《参考消息》的编译人员译这本书的,后来给我审阅时,我发现有很多地方翻译的不够准确,特别是新闻专业方面的术语错误很多,所以拿回去几乎是从头到尾重译了一遍,原译稿的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我的字迹。这一改改了八个月,写到最后得了肩周炎,一只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在至今对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归属尚有争议的情况下,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学界能不能拿出学界普遍认可的经典教科书译本显得至关重要。而这样的学术成果与社会期待相比的确太少。究其原因,主要原因是翻译力量不足,更主要的还是重视程度不够。所以我说:“本来这样的大部头译著不该由我这样自考英语大专毕业的人来译的,我觉得我的水平肯定不是最高的,为什么没有别人来做呢”。在我看来,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在不很壮大的国内新闻学术界,80%以上的学人关注的是国内问题,看的是中文出版物,而这个学科80%以上的资源不在中国。这种人力资源的严重不合理配置势必妨碍我们这个本应“得风气之先”专业的健康发展。
钱婕:您翻译了那么多原著,可是到现在一天国门也没有出过。最近手头上还有翻译任务吗?
展江:当然有,人大出版社让我准备《美国新闻史》第九版的翻译,还有“新闻与传播学大师系列”经典著作正在陆续翻译。看看其他发达学科,人家在学科根底已经相当扎实的基础上还在大力翻译学术经典和注重基础研究,对此作为新闻传播学最高学位获得者理应抛却浮名,多做实事。
“如果一味排斥负面的东西,媒体就是失职”
钱婕:中国早期报人章太炎曾说“事不可诬,论不可宕,勿以法理虚言而蔽事实,勿以众情踊动而失鉴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的十余年中,中国传媒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也面临着一些不容乐观的现实:一些突发事件中,公众说“信爹信娘不信报”——传媒公信力缺失。您认为媒体如何应对面对突发事件的尴尬?
展江:这正好可以从近期的一些突发性事件说开来,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发生过这类事件,但是他们的机制可以使恐慌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消弭。据我观察,这种机制有其制度化的安排,长期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媒体的信息传播机制和政府的快速反应机制。
从媒体方面来说,美国媒体有其传统和惯例,普利策说,记者是船头上的瞭望者,瞭望的是激流险滩,当然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望。我理解,所谓激流险滩就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具危险性的事件。
根据这种职业精神,发达国家媒体最关注的就是这种突发性、灾害性的事件,媒体的职能之一就是找这种信息。只要发现有异常情况,特别是涉及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危,媒体就会立即做出反应,哪怕仅仅是传说,媒体也一定会报道出来,对于危险情况,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如美国炭疽袭击,最后证明很多是谣言或恶作剧。为什么发达国家媒介会这样地关注这一类的事情呢?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事件关系到人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
其他的新闻都达不到如此威力,所以,无论是大众化的,还是比较严肃的媒体,都把这种报道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能。
从政府方面来说,惟一选择是和媒体合作,事件发生后,政府作为权威信息的掌握者和控制者,要定期地向新闻界通报情况,绝不能垄断所有的信息,大众传媒会在不影响整体稳定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公布事件的每个细节。
王永亮:有关部门三令五申抵制有偿新闻,传媒的寻租行为却仍然存在——用“堕落”二字不为过……更让人担忧的是舆论监督的窘境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形成强烈反差,促使传媒从业人员趋“利”避“害”,媒体的商品属性被渲染得无以复加,似乎媒体仅是一个赢利的企业,媒体的从业人员也成了打工挣钱的产业工人,传媒研究一时间几乎成了传媒经济研究。您是怎样看待这些怪现状的?
展江:不少记者招待会变成红包会,私利集团冒充公众利益在媒体出现。我们当务之急的是应该发挥媒体社会公器的职能,抵制各种利益集团对它的侵蚀。有一个媒体的编辑对我说,我们也很难,一方面要弘扬主旋律,另一方面要提高收视率,但遇到特殊的“保平安”时期,怎么保呢?就播放韩国电视剧,这样既有收视率,又没有风险。又在别的时段的文艺节目最后,找几个人高喊口号,这样主旋律也有了。他们认为,这样做两头都会满意。但我和他们的看法完全相反,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已经有政治学者在反腐败专著中提出,官办媒体商业运作是当前腐败的制度根源之一。
当年,我们有人嘲笑张季鸾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可是今天有媒体见“赵公元帅”就拜,甚至有媒体从业人员以“舆论监督”为敲诈手段。只有当某一天,中国的新闻媒体能真正不受制于金钱诱惑,不再迫于政治压力,畅其言,行其职,载民怨,表舆情的时候,方可见得天地良心!
王永亮:中国思想家梁启超说“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国民之喉舌也”“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一个世纪后,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诸多难题也不可回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面前,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媒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展江:媒体应该是社会公器。媒体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公共信息的平台。媒体的首要功能是进行环境监测,并把观测到的东西告诉公众。监测是不是及时很重要,当今社会科技发达,人类文明发展很快,但任何社会都不能避免天灾人祸,如果一味排斥负面的东西,媒体就是失职。
以美国为例,美国媒体的很多做法是给政府提意见而不反对他们的社会和制度,这对促进社会整体健康是有好处的,当然,媒体在局部报道上可能存在不实报道,但是马克思曾经强调过报刊的“有机运动”原理:个别报道可能会失实,但是各种媒体作为整体,全面、完整地披露信息,最后得出的是比较接近于真实的报道,或者以越来越准确的事实来纠正差错,它的正面作用是很明显的。
以前不久美国发生的枪击事件为例,每一起事件媒体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是不是引起恐慌?结果是没有,因为长期以来由于媒体和政府的良性互动,整个社会都显得很有理性,无论是政府的决策还是媒体的反应,整个社会并没有因为媒体的介入而失衡,反而会由于获得的信息是比较对称和平衡的而做出合理的应对。
钱婕:前不久,中央领导指出:“我们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的利益党没有自己的私利,这就决定了宣传思想工作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使党的主张和人民利益更好地统一起来。衡量精神文化产品,最终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喜欢不喜欢。”对此类问题的回答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必然要求,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您认为应该为中国媒体发展创造怎样的空间?
展江:马克思认为,新闻出版自由是文明国家的公民权利,它是通过油墨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我想,正因为他和恩格斯被剥夺了包括新闻出版自由在内的基本权利,他们才被迫流亡到赋予公民这种自由的异邦。
马克思还说,“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没有新闻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在专制统治下接受检查的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它有“伪善、懦弱、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为统治者粉饰太平,或为小市民提供一些无聊的谈资,这样的报刊既扼杀民族精神,又破坏人民的教养水平。
马克思把19世纪初普鲁士无聊小报盛行的年代称之为德国人精神上的“大斋期”,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尽力避免这样的“大斋期”降临?
王永亮:新闻作品折射着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价值标准和文化传统,新闻奖的获奖作品更代表着一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文化观。作为美国新闻最高奖的普利策新闻体现了美国的传媒伦理和传媒文化,您连续几年在最快时间翻译、点评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评选结果,在学界很有影响。请您分析其主要特点,对中国有哪些借鉴价值?
展江:简要而言,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价值取向:“全是坏消息”本性不改。与中国媒体奉行的“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不同,美国新闻界一向坚持报道和评论负面题材的“曝光”、“揭丑”传统。美国新闻界坚持悲天悯人的基督教“原罪”说,自诩为环境的“了望者”和“监测者”、公众的“看门狗”和强权的制衡者,它们瞭望和监测的是急流险滩,而不是一马平川,试图通过消灭一个个罪恶和问题以及抑制社会权势集团来改良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二、精英意识:《纽约时报》,总统必读、哈佛日销千份。每届普利策新闻奖评选,就数量而言,《纽约时报》都遥遥领先。自1963年美国首次就报纸影响力开展民意调查以来,《纽约时报》每次都名列第一;它是历届总统的案头必读之物,在哈佛大学这样的精英荟萃之地每日能销售千份以上。该报是高质量报纸的杰出典范,高质量报纸编辑方针的共同点是:(1)新闻准确真实重于迅速,平实而不夸张;(2)以公共事务为重点,强调新闻的意义重于趣味;(3)重视评论,但立论严谨;(4)社会新闻的处理采取严谨态度,在版面上不予突出;(5)版面古朴大方,不常变化。现在国内有一些新派大众化报纸在市场上经过拼杀初步获得了立足之地,其激情与勇气可嘉,然而赢得了市场就自称为“主流报纸”显然是不当的,有时恰恰相反,倒是在不自觉地靠拢了以煽情主义著称的国外小报。
三、专业主义:“政教分离”,报道与评论的分离地位。对美国新闻界自身而言,它最大的职业特色就是奉行陈述事实与发表意见分离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实行新闻报道部门与新闻评论部门分立,文体和版面分离。美国有人称之为新闻学上的“政教分离”原则。尽管美国主流报纸《纽约时报》遗产的不同继承人分别强调奥克斯信条的不同方面,但他们全都尊重奥克斯关于“教会”和“国家”分离的原则,全都坚持要把“教会”、“国家”这两者与“会计室”分开的原则。“教会”指的是《纽约时报》的社论版,“国家”指的则是《时报》的新闻版,而“会计室”指的是《时报》的经营管理。
四、主流报刊:追求深度,继续引领公众舆论。在美国新闻界,从20世纪30年代起,以透视新闻事件和社会潮流的来龙去脉、化繁复为简明的解释性报道开始在报纸和新兴的新闻性周刊上兴起。这种深度报道注意事物的总体关联,将重大新闻事件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在各种事物的互动中加以报道,探究新闻事件的深层含义、背后原因及潜在的问题。中国的新闻杂志是目前最不发达的媒体,因而在社会转型这个呼唤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深度报道样式的时期也是最有发展前景的,未来几年孕育出销量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新闻性期刊决非妄言,因为成长中的中国“公共领域”需要这种的高质量媒体平台。
王永亮:您刚才提到了“公共领域”,这就不得不提起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认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消解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这种情形与封建社会晚期有类似之处,因此哈贝马斯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请您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评析。
展江:哈贝马斯的理论很适合中国现实!中国媒体要警惕“双重封建化”,什么是双重封建化?一方面,长期以来人治、长官意志等封建意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大,去封建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初期市场经济的弊端和它与生俱来的弱点却降临到他们身上。在一些地方,从官媒合一到商媒勾结和官商媒共谋,以私人和团体利益冒充公众利益,以“监督”社会底层和“监督”外乡人为乐。另外,现实的情况是否认媒体的社会公器职能和对权力的制衡作用,对新闻传播领域的调控保留了法制的盲区和人治的特区。
钱婕: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今天,在市场机制发育和社会普遍承认“经济人”的地位和国家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的情况下,新闻传播迟迟不与国际接轨。部分人士夸大媒体的“覆舟”作用,实为早已过时的“魔弹论”的翻版。您如何看待这一事实?
展江:有人将自由与法制对立起来,视国际社会工人的基本人权——新闻自由为洪水猛兽,迟迟不出台《新闻法》,还有人为不出台《新闻法》辩护,称“世界上多数国家没有新闻法”。其实作为近现代社会进步标志之一的新闻自由,其背后的支撑正是法制。中国政府早在1998年就签署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根据我的阅读,迄今没有发现新闻传播学界有人引述过其中的有关条款。
另一方面,新闻与宣传至今没有分野,而迷信宣传灌输者不乏其人;依然在新闻传播中坚持单向灌输,否认媒体的社会公器职能和权力制衡作用,对新闻传播领域的调控保留了法制盲区和人治特区。有的地方官员依然相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训,不时以“正面宣传”为幌子堵塞言路,并且将媒体变成了为其歌德与礼赞的工具。在这种环境下,公众知情权难免不被剥夺。我们从每日新闻事业中了解不到如下事实:1980—2001年间全国检查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年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1.5倍(8%对20%)。有权威经济学家测算,贪官携款外逃资金已超过国家吸引外资的数字。
王永亮:在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今天,我们仍然面临反封建的艰巨任务。正如近期有学者所言: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总体攻坚的新阶段,按照十六大报告的要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需要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社会方面改革的新相互配套、同步推进。中国媒体的“双重封建化”令人忧虑,主要有哪些表现形式?
展江:封建残余的文化观念已成为继续推进改革的严重障碍:第一,人治文化与法治文化的对立冲突;第二,官本位文化与民本位文化的对立冲突;第三,全能政府观念与有限政府观念的对立冲突;第四,政府主导观念与市场主导观念的对立冲突。这些冲突无时无刻不通过当代新闻事业反映出来。在中国加入WTO、公众要求社会生活越来越透明之际,继续阻碍信息的流通、保持新闻传播的人治状态不应该是正常现象,势将以高昂的社会成本作为代价。
另一方面,在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某种伪公共领域制造了媒体的伪公共性。兹举每日新闻事业中的几种现象:(1)传媒以商业和私利集团以各种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等公关形式频频制造的“媒介事件”成为新闻主角,私人和团体利益俨然成了公众利益。(2)商界朋友成了新的媒体英雄,如同自身出问题一样,一旦这样的“英雄”失势和案发,则三缄其口。(3)部分传媒以“监督”社会底层和“监督”居住在本地的外乡人为乐事,对真正的监督对象——不法权势集团——则曲意逢迎。(4)在本地新闻表现歌舞升平的同时,媒体主管并不是不知道“负面报道”的用处,只是更经常地利用别人的“全是坏消息”报道模式从事“进口转外销”,仿佛天灾人祸只发生在异域和外地,似乎还在验证“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真理”。(5)通俗报纸在市场机制下出现,却由于国内报道领域的窄化而过早出现了同质化。
钱婕:您分析了伪公共领域制造了媒体的伪公共性,对于这些不正常现象,您赞同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吗?对于媒体在“公共领域”的作用,您有何建议?
展江:我并不一般地赞同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因为它们只是有限地适用于后工业社会而非我们这种前工业社会),而主张反对两种封建。我相信,一个合理而健康的国家应当努力营造一个公私分明、自由和责任界限清晰的社会。可采取的对策有: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发展适应现代化的媒体理论,为建立消灭“黑箱政治”、建立“白箱政治”做出贡献,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共形成良性互动,维系民主与法治;有步骤地与国际接轨,赋予新闻自由、信息公开和新闻舆论监督以法定地位,为社会转型的有序进行充当守望者,降低转型的社会成本;在法制的规范下建立多样化的新闻体制(尤其是国有公营和社会公营体制),消灭新闻传播领域的法治盲区;坚持媒体的社会公器论,构筑公众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制定和恪守严格的新闻专业标准,反对媒体公司论和集团工具论,抵御不良政治和经济势力的对媒体的腐蚀。
王永亮、钱婕2003年6月6日访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