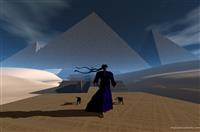绘画的基本艺术构成是点线(笔法)、面体(墨法)、色调(用色)构图。而书法的基本艺术构成则是线(笔法)、墨(墨法)、结体、章法。二者具有相近之处,也有互相吸收互相补充之处。
(一)用笔:驭万为一与以线呈道
绘画作为视觉艺术和空间艺术,能运用点、线、面等造型手段,构成一定的艺术形象,使人在审美欣赏过程中,通过联想,将凝定的画面还原为活生生的情景和事物发展的过程,从而感受到作品所具有的审美意义和艺术意味。绘画艺术长于描绘静态的物体,其主要审美特征是具有可视性。它与雕塑的区别在于,它只占有一个平面的二度空间,使人在审美过程中通过对其绘画语言的直观理解,由二度空间产生三度空间感。也就是说,绘画具有瞬息美,擅于把捉生活中富有意味的瞬间,撷取事物运动的一刹那,通过静止的平面和三维空间塑造完美丰满的艺术形象。
而书法作为视觉艺术却具有音乐的律动感,而成为一门抒情写意的艺术。汉代的蔡邕论及书法艺术的抒情本质,强调“情”、“性”、“怀抱”在书法创作中的重要价值,对书法美学思想具有深远意义。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对书法抒情性、表现性作了全面精辟的探讨,认为书法能“达其情性,形其哀乐”,能充分传达书家的个性风貌和情感意绪。而清代刘熙载也是书法表现情感的倡导者。可以说,书法是通过抽象的点画字形线条表达主体激情和生命深处难以言状的律动,是极富表现个性的表现艺术。
天地万象唯“一画”——线条可以呈其形,摄其魂,得其神。线条处于中国画的核心地位,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人物画方面有“十八描”,在山水画方面,以线条的网状结构造成的皴法更是多姿多彩。这些皴法是画家创造的种种线条形式,用以表现山石、树木等自然物象的阴阳、向背、凹凸等不同的形态和质感。线条的交错并置,构造了造化的千形百态。至于点擢的形式,则多达二十余种。
点是绘画最基本的元素,线与面由点发展而来。线是两点的连接,因而是点的延伸。艺术家在绘画创作中运用带色或不带色的直线和曲线去表现事物的轮廓、质感,性格等,以收到相应的艺术效果。线条在其象征功能方面是人的情感的外化──迹化。这样,线条在作为外物的界面时,具有将对象从背景的混沌中独立出来的功能,同时,线条作为主体的心画,有可使主体情感迹化而禀有宇宙精神和生命情思。这种宇宙精神和生命情思是流动的生生不息的,使得线条成为时间的、节律的、生命宇宙之气运行轨迹的写照。
绘画并不存在纯再现意义的线条,任何线条均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换言之,绘画线条的本质在于它与生命的某种异质同构,通过线条的起伏、流动,通过线条的粗细、曲直、干湿等变化,通过线条的轻重坚柔、光润滞涩、枯硬软柔的踪迹,传达出人的心灵的焦灼、畅达、甜美、苦涩等情感意绪。可以认为,线条中流动着画家的缕缕情思和细腻丰盈的艺术感觉,是艺术家通过想象和概括出来的创造性的可视语言。
线条的审美特性在于,它传达出画像的生命情调和审美体验,反映了作者的风格、品格和精神意志。如晋代顾恺之的绘画线条的敛约娴静,萧散出尘,映衬出画师的简远淡泊的个性风貌。
线条写神。以形传神唯笔之“一画”。石涛说:“太古无法,太朴不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画之法者,尽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夫画者从于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错,鸟兽草木之性情,池榭楼台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尽其态,终未得一画之洪范也。行远登高,悉起肤寸,此一画收尽鸿蒙之外,即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惟听人之握取耳。”“盖自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我故曰:‘吾道一以贯之。’”(《苦瓜和尚画语录》)
线产生于笔法,线条处于中国画的核心地位。中国画的线条,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人物画方面有“十八描”,即:高古游丝描,铁线描,行云流水描,琴弦描,蚂蝗描,钉头鼠尾描,混描,撅头描,曹衣描,折芦描,橄榄描,枣核描,兰叶描,竹叶描,战笔水纹描,减笔描,柴笔描,蚯蚓描等。在山水画方面,以线条的网状结构造成的皴法更是多姿多彩。如:披麻皴,乱麻皴,芝麻皴,卷云皴,解索皴,荷叶皴,乱柴皴,大斧劈皴,云头皴,小斧劈皴,雨点皴,豆瓣皴,牛毛皴,马牙皴,折带皴,弹涡皴,矾头皴,骷髅皴,破网皴,拖泥带水皴等。这些皴法也是画家创作的种种线条变形形式,用以表现山石、树木等自然物象的阴阳、向背、凹凸等不同的形态和质感。线条的交错并置,构造了造化的千形百态。
至于点擢的形式,则多达二十八种,它们是:个字点,介字点,胡椒点,菊花点,鼠足点,小混点,大混点,松叶点,水藻点,垂藤点,柏叶点,藻丝点,尖头点,梧桐点,椿叶点,攒云点,攒三聚五点,垂头点,平头点,仰头点,聚散椿叶点,刺松点,破笔点,杉叶点,仰叶点,垂叶点,个字间双钩点。点线构成面。线本于一,生于笔,指向道,而面则衍于水,成于墨,本乎气。
种种笔法,总括起来,无非是画线条时,粗、细、曲、直、刚、柔、轻、重化为千姿百态。这种种线条,依其用笔而饱于用墨,凭借在时间之维中展开,在轻重缓急涩畅徐疾干湿燥润中获得一种力与势的内在张力,在“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飞动潇洒的自由线条中,参赞天地化育,契合兴会意态而禀有形而上的玄机。
书家用灵动的线条契合元气淋漓的道。书法这一极抽象的线条并不为大千世界万千具象一一写照,而是以一驭万,一画呈万象,一笔存千情。书法线条在延伸拓展某种无法描述的个人体验时所达到的遗象取神,忘物存道之境,使之超越语言物象之上。
中国绘画在这一点上与书法一脉相承。石涛曾在两个方面道出中国绘画美学的关键:一、山川廊大,必须用“一”管之笔,才能参悟天地之化育,以“一”线写神,才能以有限之笔抵达无限之境。这是一种书画互通、以少总多、万万归一的美学观;二、道出了中国画家创作的秘密,可与书法最高境界的“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气;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孙过庭《书谱》)相佐证。在画家那里,艺术不是单纯描绘客观山川,也不是单纯表现主观的情思,而是面对拔地而起气势浑莽的山川丘壑,情思激荡,在感情体验中,把自然丘壑变成为画家胸中丘壑,然后再用完美的形式将这胸中丘壑表现出来,成为画上丘壑。石涛用“神遇”来概括作者变“自然丘壑”为“胸中丘壑”这一过程,用“迹化”来表述把“胸中丘壑”物化为“画上丘壑”过程。这能“贯山川之形神”的“画上丘壑”与“自然丘壑”相比,是“不似之似”,这“不似之似”就是画家在对“自然丘壑”审美体验中,以自身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与自然山川的审美物性融合为一,而“终归之于大涤”。
画家以“一画”括万物的“ 神遇”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画家面对山川丘壑,为其山势的险峻和壮美所动,悠然会心,这是对“自然丘壑”外形式(形,色,质)的审美感受。其次,这时的“胸中丘壑”却不同于自然丘壑,而已经具有画家的审美态度和审美评价,表现了画家的独特审美感情、审美评价方式和审美价值观念。表现了画家从对象的耸然而立,苍苍茫茫,气势雄浑上感到一种震动心魄的力量,这就已经超越对“形”感受的表层,进入到对“势”体味的深层次。最后,眼中丘壑与画家胸中“凛风”之气相激相荡,主体将自己的情、意、德、才、识、胆统统融入山川的意象之中——它那千岩竞秀的气象,灵趣飞动的意志,冲虚简静的精神与画家自己的性灵、襟怀抱负,独立高迈的人格,虚灵简远的精神气质同构,那山川的气势正是自己情志的外观。在审美主客体瞬间融一,达到“气”的感悟——高级审美体验层次,诞生出“胸中丘壑”这一审美意象。
生命是整体的“一”,能把握山川整体的“一”,才能把握到山川的生命。画家面对的一山一水都是面对的整个世界,从而使他从现实的时空中超越出来,在对物象的审美观照中看到自己,甚至在这种“凝神”境界之中,他不但忘却审美对象以外的世界,并且忘记了自我的存在,“意境两忘,物我一体”(王国维),达到一种悠然意远的“化境”。画家达到灵感高峰时,所孕育成熟的审美意象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和勃勃生气,这时,审美意象所表现的审美对象的本质,已经不完全是客观本质的有关部分和主体本质的有关部分的化合。一旦形成这种“化合”“同一”的意象,就不再完全是客体,也不完全是主体了,客体的本质为主体的本质所“顺应”,转化为主体;主体本质“同化”了客体,转化为客体。二者的化合的“一面”指向了一种更深的本体存在──“道”。
可以说,笔法所产生的线条构成了中国书法绘画艺术的本体而与道相通。
(二)墨法:流贯之气与虚实之境
墨法是中国书法和绘画的重要内容。南齐谢赫“六法”中尚未提出墨法,到了五代荆浩《笔记法》中“六要”,才将墨法作为一个方法提出来。
线源于道,墨生于气。笔中有墨,墨中有笔。唐岱说:“古人之作画也,以笔之动而为阳,以墨之静而为阴;以笔取气为阳,以墨生彩为阴。体阴阳以用笔墨,故每一画成,大而丘壑位置,小而树石沙水,无一笔不精当,无一点不生动。是其功力纯熟,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其画所以称独绝也。”(《绘画发微·自然》)董肇说:“弄笔如丸,则墨随笔至,情趣自来。故虽一色,而浓淡自见,绚烂满幅。”(《画学钩玄》)
中国画中的水墨画,格外突出墨的审美趣味。水墨作画,以天趣胜。以墨为形,以水为气。水墨为上的观念是老子美学“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思想的体现。墨分五色而实为一,用色而色遗,不用色而色全。水墨无色而无色不包容在内,故无色为至色。张彦远说:“夫阴阳陶蒸,万象错布,玄化之言,神工独运。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彩;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綷,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历代名画记·论用墨》)r
庄子“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庄子·山木》)的思想是水墨画美学的思想渊源,而尚“真”,尚“清”思想对水墨画影响殊深。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一墨之色,蕴万象之色。这种美学观,张扬虚静待物,遗形传神,摒去机巧,意冥玄化的画境。强调物之神气在灵府而不在耳目色相,故须摒除感官,去眼目屏障,使肉眼闭而心眼开,“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摈落筌蹄、而穷至理。从有限中见出无限,从无色之中睹玄冥之道。故方熏说:“墨浩浓淡,精神变化飞动而已。一图之间,青黄紫翠,霭然气韵;昔人云墨有五彩者也。”(《山静居画论》)
墨并非一色而是五彩,有干墨、淡墨、湿墨、浓墨、焦墨等。用墨与设色的关系,有主墨为主而色为辅,有主墨助色而色助墨。用墨如布阵,如用兵。宋代李成有“惜墨如金”之说,而张璪有“用墨如泼”之说。墨有死、活、泼、破,亦有净、洁、老、嫩,用墨的方法犹如五行的运行。中国画家以水墨肇其天机,把水墨尊为上品。他们感觉到冥冥窈窈之中有神,虽极尽笔墨之巧,也难以完美表达,于是干脆反璞归真,寓巧于朴,以通天尽人之笔把捉其中的深意,以逸笔草草勾勒出极简洁又极富有包孕性的具象,放在无边无际的虚白里,让人驰骋遐想。
用墨如布阵,用墨如用兵。宋代李成有“惜墨如金”之说,而张璪有“用墨如泼”之说。墨有死、活、泼、破,沈宗骞说:“墨著缣素,笼统一片,是为死墨。浓淡分明,便是活墨。死墨无彩,活墨有光,不得不亟为辩也。法有泼墨、破墨二用。破墨者,淡墨勾定匡廓,匡廓既定,乃分凹凸,形体已成,渐次加浓,令墨气淹润,常若湿者。复以焦墨破其界限轮廓,或作疏苔于界处。泼墨者,先以土笔约定通幅之局,要使山石林木,照映联络,有一气相通之势,于交接虚实处再以淡墨落定,蘸湿墨,一气写出,候干,用少淡湿墨笼其浓处,如主山之顶,峰石之头,及云气掩断之处皆是也。所谓气韵生动者,实赖用墨得法,令光彩晔然也。”(《芥舟学画编》)
墨亦有净、洁、老、嫩,方薰说:“用墨无他,惟在洁净,洁净自能活泼。涉笔高妙,存乎其人。姜白石曰:‘人品不高,落墨无法。’墨法,浓淡精神、变化飞动而已。用墨,浓不可痴钝,淡不可模糊,湿不可溷浊,燥不可涩滞,要使精神虚实俱到。”(《山静居画论》)而“嫩墨者盖取色泽鲜嫩,而使神彩焕发之喻。老墨者,盖取气色苍茫,能状物皴皱之喻。嫩墨主气韵,
而烟霏雾霭之际,润淹可观;老墨主骨韵,而枝干扶疏山石卓荦之间,峭拔可玩。”(沈宗骞:《芥舟学画编》)用墨之道犹如五行之运,“盆中墨水要奢,笔饮墨有宜贪、有宜吝。吐墨惜如金,施墨弃如泼。轻重、浅深、隐显之,则五采毕现矣。曰五采,阴阳起伏是也,其运用变化,正如五行之生克”(张式《画谭》)。
墨气烟氲,实是在实境中创化出一片生机玄妙的虚实,用墨实是吐纳大气,泼墨破墨涌动的苍茫充盈,迷离渺渺的墨气,使人感到实中有空,空中有气。而在那大片留出的空白处,则是创化出一种悠远的宇宙大化,“气”流存于画幅之中,使山光水色禀有一种生生不息、涌动不止的“道之流”。使人融生命于宇宙大气流行中,体悟到满纸云烟实是宇宙之生息吐纳,满目混沌不过是墨海氤氲的自然之道。画家冥合自然,经天合天,仰观造化,俯揽外物。化实为虚,以呈现无言独化之道;染墨成韵,以吐纳宇宙万物。
书画相生互补。书法用笔同样是书法艺术的核心。墨法是书法形式美的重要因素。枯湿淡浓、知白守黑是墨法的重要内容。绘画讲墨气,书法讲墨韵,书之法尤画之法。
(三)章法:绘画构图与书法布局
在谈构图之前,有必要谈谈色彩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画在古代称为丹青,丹为朱砂,青是蓝靛,故谢赫把“随类赋彩”列为“六法”之一。
色彩是人的感性中最敏感的感觉形式。中国画有错彩镂金的工笔重彩画和讲究色墨韵味自然清新的水墨淡彩画两大类型。工笔重彩画在秦汉时已趋成熟和流行。设色多采用不透明矿物质颜料,甚至描金,色泽鲜妍,构图丰满,饶有装饰趣味。水墨淡彩画是宋元之后迅速发展成为主流的,它充分发挥笔墨效果,使水墨产生酣畅淋漓、自然清新的面貌。在水墨绘制的主要骨架上省略淡彩,则与水墨相得益彰。水墨画崇尚一种简淡幽远。素净浑朴的色彩,使中国画具有日益浓厚的抽象意味。
从最早的中国绘画崇尚红色到文人画崇尚墨色,中国人的审美色彩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五色到水墨,从“随类赋彩”到“色不碍墨,墨不碍色”;从重用笔到重用墨;从勾勒线条到点染晕彰;从讲究“丹青”到倡导“绘事后素”(素高于绚)。中国画日益走向色即墨,墨即道的“超妙自然”之道。
中国画色彩自王维以后的文人画家,开辟了一个抽象色彩境界,墨色渲染,界破虚实,水与墨合,黑白二色中色阶色值可以无限分下去。从而使中国画臻达水墨为神,见素抱朴,清寒萧疏,莹润蓊郁的境界。这种以墨为荣的幽淡迷蒙的“墨韵观”在黑白两极的色彩世界里将世界抽象化、纯净化,使画幅灵气往来,空白处存有限无限之气,黑白处独领宇宙之奇妙,使人在素净淡然的画境中安顿自己的灵魂。这一点,书法与绘画可谓殊途同归。
中国画的构图相当重要,除了“六法”中的“经营位置”以外,还包括山水的透视法。一般说来,构图的主要任务是物体空间的组织、取舍的匠心安排。如果画面作横向线式构成,通常蕴含着运动、张力和痛苦的意味;金字塔构图表现稳定或僵化;倒三角形显示出危机和倾颓坍落感;而圆形构图则往往表现出完满、圆转和充盈感;S形的构图则表现出流动空灵。一幅画采用不同的构图,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意向性和气势氛围。
在山水画的透视方面,有郭熙的三远(高远、深远、平远)法(《林泉高致·山水训》),后来韩拙又补充了“洞远”、“迷远”、“幽远”(《山水纯》)。中国画远近法为克服绘画艺术的时空局限而提供了独特的视界。总体上看,中国画不像传统西洋画那样采取静止的焦点透视,而常常是大胆自由地打破时间空间限制。
中国画家早在公元五世纪上半叶就已经认识到了透视法则。南朝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了初步的透视理论,隋代展子虔画山水已达到咫尺千里之妙。与西洋画家忠于物象的透视法则相比,中国画家极为重视个人的主体意兴,在处理构图时常使用类似鸟瞰式的观察方法和左右移动视点的独特方式。讲求“六远法”,“七观法”,即步步看,面面观,专一看,推远看,取移视,合六远(王伯敏)。这样,山水透视就显出迥异于西方绘画的审美特色:“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宗炳《画山水序》)。山水画家,“以一点墨摄山河大地”(李日华《画媵》),所谓“一墨大千,一点尘劫”(沈灏《画尘》),“嘘吸太空,牢笼万有”(戴熙《习苦斋画絮》)。这种六远、七观,实际上通过视点的转移,打破绘画二维空间限制,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对笔下之物进行主观意向变形,强化其暗示意味,使小我的心灵扩大以拓展灵境,大我的世界缩小以包揽宇宙。
而“经营位置”(谢赫)乃“画之总要”(张彦远)。一般是“必先立意,而后章法”。构图章法不是一般的形式技巧问题,而是力求鲜明地表现画家的审美趣味。画面结构讲究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艺术上注重象外之趣、画外之意,一树一石,寥寥几笔,巧妙布置,引起无限遐想,常达到引人入胜、玩味不尽的效果。
为了突出气势,范宽等人的山水画多取“全景式”构图,主山雄踞正中,挺拔凝重,这种构图具有夺人的气势;为了表现情韵,马远、夏圭等的山水多取“边角式”构图,所谓“金边银角”,空灵俊逸,更富于情韵。画家总是为达到某一种艺术境界,而选择与之相应的构图方式。中国画构图布局讲求计白当黑和平面布置。画幅中空白大大小小,虚虚实实,若断若连,错落有致,有聚有散,相互呼应,组成了“空白”的审美意境。而八大山人从构图多为圆形,画石则奇特古怪,重心不稳,画树叶则缺枝少叶,残败凋零,而且物象周围常空荡荡的无依无靠,这些形式正是他孤愤、冷寂、痛楚、沉郁的精神气质的表现。潘天寿构图喜作方形结构,常常创造奇险的境界,以表现他雄阔、霸悍、朴质的绘画风格。黄宾虹晚年的山水画更多密实工作,象《大涤山山景》、《坐雨齐山》等,通局浓墨,却利用水面反光的一小部分空白作虚的处理,所谓“岩岫杳冥,一炬之光,如眼有点,通体皆虚”。五代时荆浩、关仝多作层峦叠嶂的“全景式”山水画立幅,章法繁密,气势宏伟。平面布局除了与远近法相关以外,还与中国画以线造型相关。线作为二维空间展开的平面艺术,注重以线概括物象的结构。线描形象的立体效果,是通过结构的透视因素传达出来的,亦即用线条来概括形体结构的透视面,可以说,它没有直观的立体形态,而是一种联想的立体效果。
绘画重在主体的审美参与,如果用感官的眼睛看世界,只能“仰面飞檐”,视野局狭而呆板;则用心的眼睛去观照世界,则“溪谷间事”,“后巷中事”,皆可“重重悉见”,透其皮相,得其真宰。因此,古人不写眼中之自然,而要写胸中之丘壑,不为形象所拘囿,而要用无形的精神包裹宇宙。从这极高的审美意向性出发,中国画强调主体的意气统领笔墨,在抽象的写神中追求气韵生动,中国画正是借助笔墨的抽象性才显得气韵生动。
中国画结构章法充满艺术辩证法,讲求取与舍、宾与主、呼与应、虚与实、疏与密、藏与露、分与合。清王昱说:“作画先定位置,次讲笔墨。何谓位置?阴阳向背,纵横起伏,开合锁结,迥抱钩托,过接映带,须跌宕欹侧,舒卷自如。位置须不入时蹊,不落俗套,胸中空空洞洞,无一点尘埃,丘壑从性灵出,或浑穆,或流利,或峭拔,或疏散,贯想山林,真面目流露笔端,那得不出人头地?”(《东庄论画》)邹一桂说:“章法者,以一幅之大势而言。幅无大小,必分宾主,一虚一实,一疏一密,一参一差,即阴阳昼夜消息之理也。布置之理,势如勾股,上宜空天,下宜留地。或左一右二,或上奇下偶,约以三出。纵有化裁,不离规矩。”(《小山画谱》)华翼伦说:“画有一横一竖,横者以竖者破之,竖者以横者破之,便无一顺之弊。又,气实或置路,或置泉,实处皆空虚。”(《画说》)
中国画家将构图章法同笔法、墨法同等看待,讲求偏正、繁简、阴阳向背。章法灵活多样,不可端倪,既有一定的法则规矩,又有创造的充分自由,于斯,心手达情,方能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构图和别致的氛围,来传达那不可传达的画中诗意。
书法的布局章法同绘画的章法一样,同样充满艺术辩证法。中国书法美学强调多样统一的布局,自由多变的章法。书法章法与绘画章法颇多相通之处。书法同样讲求“计白当黑”,字外行间有笔墨意趣。书法中字的实境,给欣赏者提供直观明确的内容,而空白的虚境则使欣赏者在感官直觉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主观想象,体验到作品可感内容之外的更为深远的意蕴。二者的有机结合,使作品获得完整、宽广、多变、和谐、含蓄的意境美。一言以蔽之,虚实相生,黑白相映,使字与字、行与行、幅与幅形成一个元气浑成的整体,从中透出作品的独特意境。
书法讲求笔断意连,错落有致,以造成全幅字的节奏感、和谐感和飞动感。书法章法布局是人的性格禀性的表征,这一点同绘画可以互相参照。或许可以说,书法章法是人的“心电图”,观书如观人,观人需观书。书家将自己的情感意绪、生命情思、诗意憧憬化为或纵或收、或浓或淡、或枯或润的线条,并通过这些笔墨线条的枯润浓淡的个性因素,反映出人的审美体验。
总体上看,在笔法、墨法、章法上,书法与绘画有相通之处。在笔法中,书画都要求有力有气,反对疲软呆板,书法用笔提倡多力丰筋,画法用笔最重骨法挺拔。书画都讲究水墨为上,墨色华润。书法艺术讲分行布白,绘画艺术讲经营位置,书法讲体势韵味,绘画讲气韵生动。这种艺术上的互通性,根源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
书法的点线、墨韵,绘画的线条、色彩、构图等凝定为书法或绘画那具有“意味美”的形式,并表现出艺术美的本质。这是一种经过审美净化了的形式,一方面表现了自然界的规律(合规律性),同时,又表现了人的情感体验规律(合目的性)。这种艺术形式感是人们在艺术创作和欣赏过程中,不断开创新的书画境界和不断生成新的书法绘画感受力的重要根据。书画美的本质,正在于通过对这种形式意味的把捉和创造,将人的灵魂意绪安顿在一个完美的形式结构中,从而由不确定走向确定,并由确定再次走向新的不确定。因此,只有将书画艺术形式与人的生命情调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洞悉书画艺术的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