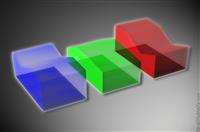从我有意识起,很长一段时间里,祖辈留下的印象都是朦朦胧胧的土黄色天光,典型北方农村的小院里,三两农民扛着锄头的样子,脸上写满穷苦和时代重压下的呆滞。偶然听说姥爷同辈的族人有两个毕业于清华大学,只觉言语两三句中,勾勒出的形象轻飘飘的遥远。我顶多承认,姥爷在当地是有名的美男子,原始生活方式催逼出的才华集于一身,手艺精巧,与姥姥都会读书写字,算不得白丁。
我很羡慕有的人说自己的祖辈满腹经纶,虽自小读书如饥似渴,却鲜有耐心儒雅的老人愿意交流,对于这一点,我始终充满了遗憾,在了解到钱氏家族历史祖训后尤其如此。我总在想,为何有的家族香火绵延,子弟杰出,基因一代代优化,品德一代代传承,以至于人才遍世界,一族百院士,而情怀不改。钱穆、钱伟长、钱三强、钱学森、钱钟书出自同族的事实令我震惊良久,不由感怀于无幸比肩,但也仅仅是略有怅惘地想着,何必那么坚持丁克呢,即便后辈没有继承聪明,也总能教养出善良真诚,顶天立地的凡人,这已经比很多人要好。
我这固有的印象直到昨晚才被母亲的闲谈打破。从前她提起自己的爷爷,我呼作太姥爷,无外乎是他见到母亲从大学放假回来很高兴,张罗着请她喝两杯“冒泡的(啤酒)还是发烧的(白酒)”,以及母亲把父亲第一次带回家,太姥爷偷偷抹着眼泪说“小伙子太丑,有什么能帮的还是给帮帮忙”。平心而论,父亲年轻是也算是眉清目秀,但太姥爷最喜爱我母亲,看在眼里怎么都觉得配不上。这样生活化且平凡的农村老人,曾经是伪满洲国的工程师,这个认知令我脑海中的土黄色背景轰然崩塌,仿佛百年历史从裂缝中透出了光亮。我推开门去粗略一眼,嚼出了无数的唏嘘与悲凉。
东北家族的历史命运,紧紧绑缚在国难的历史之上,每一个时光的吐息都决定了截然不同的走向。关于家族最早的记忆来源于太姥爷的父亲,年代已无从细究,只能猜测是民国初年,是时应逢家境拮据,仅挑选家中两个资质优秀的儿子去念书,一个是长子,另一个则是太姥爷。后来东北沦陷,伪满洲国建立,生活在日占区之下的太姥爷也要学习日语,那时他是工程师,到新中国建立以后,顺理成章地失业,老老实实当了农民。虽如此,太姥爷依然保持着读书的习惯,每到春节,村南村北分划开来,一半归太姥爷,一半归另一个读书人家,二人分别写好楹联,还于各家。
两户均是耕读人家,交往便更加密切,姥爷的妹妹,我称作姑姥,嫁与了那家的儿子,划定成分时,那家是地主,太姥爷是富农,没有挨批斗,却也并不好过。彼时的中国穷困潦倒,东北广袤大地上的农村沉睡在肥沃黑土之上,精神却是贫瘠的。姥爷聪明,却只堪堪读完小学,姥姥更是连小学都没有读完,读书的机会在那样的年代里是沙漠中一碗清水,大多数人碰也碰不到,有人终生游荡在沙漠外缘,干渴愚昧而死,有人指尖浅浅触到一抹清凉,却最终不得不低下头去,匍匐在穷困的大地上绝望。
很多人的家族或许都是这样过来的,哪有那样多叱诧风云的帝王将相,靡靡而歌的文人才子,被撕裂的民国浪漫华艳的文化幻影之下,到处都是流不出血泪,拼命乞讨生活的凡人。到了安定的年代,平凡的家族们依然要想尽办法地活下去,什么是新文化,什么是抒情诗,什么是丁香花一样的姑娘,那是另一个世界的文字,刚刚被血染过的土地上,只有粮食的语言,还能摸几年书本,懂得读写,已然是难得的经历。
那时的贫穷我无法想象,母亲说他们兄弟姐妹轮流穿旧衣,餐桌常年不见荤腥,新年时包不起饺子只能早早睡觉,到了大学因为生活费不足而数次饿晕,但言谈中却总爱提起,即便穷困如此,姥爷姥姥也从不苛待儿女的精神。姥姥算是很爱赶时髦的人,哪怕家徒四壁也要早早买下收音机,一家人听书,听新闻,在院中干活也不忘读借来的《红楼梦》。此后母亲考上了大学,有相熟的村民来来回回劝姥姥姥爷,女孩子读书无用,不如趁早出去工作反哺家里,姥姥虽满心不愿,却依然咬着牙把母亲供到了大学毕业。
那个时候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母亲读了师范,便被分配工学院做导员,后来转入大学,当了教师,她提起的时候还甚为感慨,曾经联系紧密的家人越走越远,那两个清华毕业的父辈只怕也免不了被分配的命运。也许学历是被人无比艳羡过的,却终究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未来,因为一旦辞职,很可能面临的就是永久的失业。话虽如此,我却很庆幸母亲在大学任教,身边接触的都是年轻人,图书资源也丰富,我算是在大学长大,被文化的氛围包裹,比起先辈不知幸运多少。
也许真的是家族传承,上上下下,人数最多的职业便是教师,爱书的习惯一脉相承,我自小被夸赞的笔杆子也不过是曾经的文艺少女,我母亲的翻版。对知识与文化的渴望刻在了一个家族的骨子里,也构成了先辈的教育密码,与此同时继承下来的还有家国情怀。姥姥在最穷的时候依然拒绝损公充私,一生取之有道,一个小学尚且没有毕业,老来沉迷吃斋念佛的农村女人,在一段经毕传送功德时,说出的祝福是愿天下太平,学生都能够好好地学习。不知为什么,在听到这朴实无华的祝福时,我总会想起多年前另一句话,它说华北之大,却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我曾很讨厌的一个亲戚,在两岸争端较为强烈的那个时候也曾毫不犹豫地表态,宁愿捐出全部家产,以卫大国统一。我几乎从未谋面的姑姥,听说我出言不逊直怼那个教我报志愿如何取巧的老师“祖国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的时候,悄悄落泪说孩子的想法没有错。不论血缘如何,这些雷打不动的记忆成为了根深笔直的树干,源源不断地向枝繁叶茂的远方输送着血液和养料。哪怕是生长在祖国快速发展,快速富裕的年代的我,也总是在冥冥之中看到未来的图景,生活清苦,穿着军装,房间狭窄似宿舍,只有书本摞成一面墙,却莫名地让我感到,就像生来便该穿军装一样,那才是我的生活。
我总以为我的存在与性格皆是偶然,生活的改变只能靠父母和我们来一代代向上跨越阶级,可实际上,我所有的血肉和品格,是一整个家族在苦难的百年之中拼命持守下来的,无言的祖训。它或许没有《钱氏家训》那样闻名于世,典雅讲究,但坚韧不拔,且掷地有声。
出身如何?家境如何?长相如何?天赋如何?职业如何?甚至,学问又如何?
百罹的家族从那些连活着都无比艰难的年代传承下来的东西,不灭。
写于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五日,二十一岁生日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