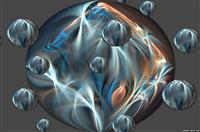若树一样坚实,麦熟一般还高的棉花,正纷纷收获,在岁尾冬晏的晚冬,被众家成田采撷,然后拔出肢体堆于家垣院角,逐步散尽容颜,变得枯干。听说豫中川蜀的冬闲人家,被政府有关部门组织起来,一列一列地开往西北,到南疆北疆兵团式的采花作战;采花大军在人烟稀薄土地丰肥的新疆,所进行的场场战役,对于棉花的及时收获与丰收,不至于糟烂在雨天淫季的丰收,功不可没,而且也增加了自家的收入,里外兼得,双喜双赢。
不能到现场观摩,但是一望无际的棉朵盛开的田野,在齐胸高的树一样坚实的麦田里,成百上千的川妹豫婶,勤劳的双手,在花朵间舞动,应该是千古未有的盛况。他们可知自己是此大观中的一景?他们舞动双手是轻盈的采摘,采摘着如画的生活,还是酸麻了手臂,团团计较着花的重量,收入的丰瘦?别家离子而去的精神追求?不仅如此,即使若我周围的田园,也未见过大批采花的大娘大婶,只是模糊记得,成兜的棉花在他们胸前,到田头翻出,装入袋中或旧筐,一脸的平静,没有喜悦没有忧愁,有些怀疑那记忆里的平静隐含着丝丝的麻木,抑或正是那种都市渲染的冲淡田园?
这个眼前的小男孩儿,是喜悦的,用两只茶杯粗细而高出一倍的盒子,装满整整两盒白色的花朵。我到那里的时候,他仍然在成堆的棉棵间,把那些残留的棉朵细细的寻访,一只只的采撷。听他的母亲说,从城里来到这郊外的农家,当孩子发现这些白色的花朵,便开始采摘,至此已有两个小时。城市的八岁孩子没有见过棉花吧,他的母亲必是告诉了棉的妙用,而洁白如雪,轻若逸云,触之柔软虚荣的花朵,更以她美丽美质美轮美奂,明朗着孩子的眼睛,勾连着少年的心肝。如此积柴成堆的枯棉树枝,早已被人遗弃,却又被孩子发现,那隐藏在枝桠间的棉朵花瓣可以采摘,如此于他纯洁的飞扬的世界;对于孩子,遮盖和发现是怎么样的喜悦和富足的美好。
想我的先人,在深山之中见此白花,手触朵儿绵绵暖暖的野蛮小树,不由摘取研究,计算生存生活的日月,该是相类似的欣喜,谁说我的先人在远古的洪荒之地没有诗情?诗意的生活在古老的岁月里,也是静静的盛开,诗意的栖息。不也包含着,把花儿摘下,晾晒撕开,披于健壮的肩头,纤细的腰身,抵御地冻天寒!这样推测,就看到,先民们豢养家禽家畜一样,培植禾苗水稻一样,开始在田野,培植这种可以开出白色花朵的棉花了。
于是,我不由从院子里出来,来到男孩儿的身边,要和他一同采摘。已经满满两盒子的棉花,尚不够一个枕头呢?他说,要再摘一些。他举着刚刚找到的另一只方形纸盒,向我晃一晃,我看到他灰尘染满的小手和星光一样闪烁的眼神,我也找到了一朵,哦,棉花有坚硬的壳,它枝枝叉叉的树身,树枝一样向上向外生长的枝头,结出核桃大小的花朵,成熟的花瓣拥挤而出,肥肥软软的;也有更多的花儿,躲在棉壳里面,用手扯开,白云一般风儿的手,弄乱成团。
“小心。”男孩儿制止我,示意已晦如霉了的一瓣,不能放入他的花盒。果会有晦霉的花蕾烂在枝头啊,我感叹道。我更小心了,在成堆的花木间躬腰伸臂,细致的寻觅,直到男孩儿的母亲在院门呼唤。说鸡已炖好,该吃饭了。我们举着双手,从花木堆中腾身而出,一边计划着怎样晾晒,一边赞赏着他的明慧,连连对他说,好,很好;好,儿子,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