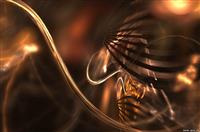
生的底线
生和死是无意义的,准确而言,死对于周围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抑或仅存恐怖,人们躲开它,或者无视它的存在-----旁若无死。刚刚开始到殡仪馆的时候,在哀乐密布的大厅里,在胸缀白花的哀乐里,感染到震痛之中,想到生的珍贵,生的真情真意和忠诚。但是,殡仪馆时间久了,次数多了,谁还会在意呢?当一个孩子在忽然之间,失去了周围的一个熟识的生命,那些痛哭和悲伤会刺痛幼小心灵,留下深深烙印的。
还记得自己失去姥姥的时候,那是何等的恐怖呢?还记得母亲的追悼会上,那成排成队的她的小学生们呜呜扯肺揪心的哭声。而现在,谁还会那么在意这些呢?视死如归,我们注重的是现实,是日复一日的现在,是晨起昏落的一天,是手头的工作。你听,孩子们叫嚣着从楼上群下,然后,一男一女的两个领导声嘶竭力的训话,至今还在外面的阳光下,玻璃落地一样的哗啦。
生,不是指人的一生,要是因死而倍加考虑现实的生活,这一生,应该是一些人肯定的,私下也可苟同。此处的生,是出生。当孕妇痛苦的大叫终于休止,在弥漫着血腥的产室,呜呜啼哭的孩子被他疲惫的母亲抬头扭头看到,当这个孩子出生的事情被亲朋特别是社会关系中人所周知,那众人喜悦的,除去了死亡、继承之类的倾利、抵抗、放心等复杂心情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中的人,又看到了婴儿父亲或祖父的权势或其他存在的牢固,而不由增了敬重。正是这样的,出生,是入世的喜悦,是世间又添了后继者的牢靠感与坚实感。
入世的思想,是社会的主流,而且渗透着引领着也左右着社会底层的风化和观念。那么主流的人群,对入世观念先天性般的认可,使这种风俗变得强劲而专制,巨大却单元却狭隘,谁还会考虑死亡的问题,谁还会知道,这一切所作所为,终究是要疲软、枯黄到秋季的,他们太专注,全身心的投入,变得常庸,势必庸俗。寒冬到来的时候,有谁能抵抗住这突如其来却又是必然到来的风雪和酷寒呢?春秋之季,暴戾乖张,退休之后,在跌落中百病缠身,好死不得。
我想,这样一篇短小的文章,不足以点拨和展开这一生死子题或侧面,入世和出世的小辩证,还是一些小小的事例,更为贴切些吧。
那是一位仍在工作的同学,站在单位大门口等人的时候,在那黄叶飘零、风已微寒的树林尽头,忽然路过另一个熟识的同学,那是小学时期就曾在一起学习,后来又一起工作的同学。他见他站在那里,连忙下了踏车,似笑却难笑的招呼。先是问如此遭遇的原因,不久便扯到近段来的境况,身体怎样?对策如何?这总是身体好的人先问的话,接着就是仍然工作者劝另一个:“退了好,退了可以没有那么多事儿,那么多杂事儿烦琐;退了,清闲,利亮”。
此时,劝慰声,叹气声,尚在世道的自得,和被挤出世道的沮丧,在泛着微澜的秋意中晃荡,这是他们面临的新的问题,是人生躲避不过的一个遭遇。当时,我就在单位的二楼,也只顾算计着这几个人那几个人,只顾想着如何处理门面房租的是非,无暇顾及他们的失落,好像我永远不会失落一样,好像我刚刚新生,一切尚在进行,没有去看枯叶正一枚一枚地从秋末的树上飘落,没有想到无数双眼睛正盯着我臀下座位的阴谋,我的厄运从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逼近,用一年的时光围到身边,再用一年的时光穿透我入世的俗想。大门之外的那两位老人,挥手告别了,但关于出世入世的讨论和观念,在风中旋荡着永远不散,在这个国度里,在这样的时期,有不朽的气息在四处弥漫。
我在这气息里不能完全摆脱,只不过我小小的经验,小小的仿佛是出世入世的两次遭遇,让我思考,有些清醒一些----较之普通的人?而我的理想,也仍然要为众人相纠缠,并且爱美的心,为自己理想之中的奉献味道、这味道的“崇高之美”而陶醉,仿佛找到了生的含义,也找到了死的意义。还有此生的意义更为可人更为高级的吗?更为宏大的吗?当然,我若只能成为普通的一子一父一夫一师,我也会在有生之年,把我的情和热,烘托、培植、给养于这些职务和责任,这应该是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平凡人的最低的生命意义的底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