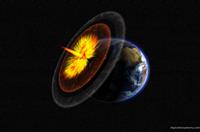十年前你几岁?你在哪里?也是这样一个太阳正酣的夏日,你在干什么?十年前,我十岁,在古老而神秘的秦岭与大巴山的臂弯里,那个太阳正酣的夏日,我蹲在从山里涌出来的汩汩清泉边,正不断舀起冷彻骨头的溪水,朝着不远处几只红蜻蜓栖息的野草尖上洒去,那一手手的水在空中变起来戏法,一会长方形,一会菱形,一会圆形,最后不偏不倚降落在野草尖上,蜻蜓们洗完澡后,摇曳着带有水珠的翅膀飞走了,野草尖水珠久久不愿落下。我抬头寻找蜻蜓,看见它们飞到太阳的半径里,羽翼上镶嵌的水珠,正反射着遥远的光,蜻蜓此时是穿了婚纱的新娘。
小时候觉得一切都很真实,感觉自己的生命真实地存在着,呼吸之间能感受得到空气的喜怒哀乐,感受得到空气的重量和体温。月亮卧在在门前的樱桃树里的鸟窝中,风像一首首钢琴曲,一会儿清澈恬美,一会清脆明快,一会婉转流畅,从屋后的松树林游出来,充盈着门前的院子。小孩拿起自己小板凳,聚集在这里,开始一场“乡村音乐会”,包谷头被用来当做话筒,蛙声此起彼伏,被当做伴奏,那些忙碌一天的男人们,叼着旱烟袋,坐着门槛上,静静听着,那些女人们都坐在樱桃树下,边聊些家长里短,边看着这些孩子们在乱嚎,并不时调侃一下这群孩子们。当时唱的是什么,我已记不住了,但是那个场面,你方唱罢我登台,热闹非凡,那些信手涂鸦的歌声,化作一缕缕轻烟,弥漫到村子的每个角落。老香樟树下一泓长满水草的碧潭,是那些孩子们乐园,有的孩子纵身一跃,全身除头外没进水里,有的胆小的孩子,迟迟在水边徘徊,欲下又不敢下,那些在水里的孩子,便奋力激起潭水,打湿了岸上孩子的衣服,岸上的索性心一横,痛快地跳进一片凉快里。这些后来渐渐消失在我生命里的小伙伴们,那时以为可以一直在一起,可是最后还是像梦一样,醒来的时候,都不在了。那时我以为我可以一直住在这个地方,没想到,数十年后,我已隔家乡近千里之遥。长大后,觉得一切都不真实了,我也不知道我是否真真正正存在,感觉一切都是虚幻的,包括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因此记忆也就随之不存在了,永远停在十年前。
我知道,我们都在长大,或快或慢。而当我捋捋自己的胡须,摸摸已经隆起的喉结,我还是惊讶于时间的速度。当我身边的朋友抽着烟,喝着酒,谈着金钱,谈着女人的时候,我似乎还在孩子的世界,只有身子在朝着成年人前进。因为我这个人一向怀旧,所以身体虽已成年,精神却还停留在童年,想通过追忆,重塑少年岁月,与苍白的人生抗衡,与流逝的时光抗衡。看到沙堆旁几个小孩在用手挖沙,在沙堆上开辟出一个个“山洞”时,我过去准备帮他们挖时,他们都害怕地逃走了,溅起水洼里的泥水,洒到我的脸上,我只好落寞地走掉。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可笑,居然这么幼稚!但是后来我仔细想想,人生有两大痛苦的根源,一个源于对过去的怀念,另一个是对未来的欲望。
这尘世的大多数人,往往对过去怀有留恋,对时光的流逝无可奈何,因而痛苦。同时他们又有欲望,这欲望使他们对未来很焦虑,吃不下睡不下,因而痛苦。而对于我这样一个停留在童年时期的人来说,总是怀念,因而无法体会到人的另一半痛苦,这样看来,我是多么幸运!
经常梦到我站在河边,捡起一块块从海拔二千多米的高山上一路颠簸而来的奇石,把它们揣进口袋,到天黑了的时候,母亲站在门口,骂骂咧咧地喊我回家,我心惊胆战地回家,又是一场雷阵雨;经常梦到,冬天的田野上,田埂上都是干枯的野草,我点燃我火柴,随手扔到里面,金黄的火便和着风肆意地烧着;经常梦到自己躺在刚刚被羊群啃食过的青草地,那里面散发出草腥气,那是人间最自由、最天然的味道。
十年前,我十岁,我用彩笔给天涂上颜色,我给大地穿上衣服,我让瓶子装满空气。十年后,我还是十岁,今天,还是我的狂欢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