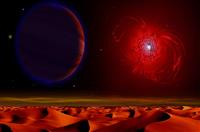冷清霸占了夜深人静,在那熟悉的路口里,老旧的路灯旁,呆呆伫立。
我勉强站在路上,留影子躺在地里。
然后就这样走着,我平行在风里,背后的它就平行在看不见的云里。
慢慢光影远去,氤氲升起。
是谁又跟在了我后头,站在了哪里。
一段孤独的路走长了,慢慢的你就不觉得陌生,一群陌生的人看久了,渐渐的你就会感到熟悉。命里命外,谁还没用过长吁感叹。我们都裹在活着里,被时间推着走。
图勒,唯一一个在我朋友中还高呼要与命运抗争到底的铁骨男儿。他出生于内蒙,少年便学会,骑马,摔跤,吟诗,歌赋。他告诉我这是命中带来的东西,生下来便会。年少时,他是全家的骄傲,全村的希望。被盼成星斗,捧成皓月。他生来便有一副俊俏的脸庞,气宇轩昂,走路生风。来往路人也要驻足观望。很快青葱少年便长大,二十一岁那年,他满怀一腔要振兴文艺界的热情,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偌大的北京城,处处新奇罕见,来往行人也个个意气风发,一时便激动不已。
头一年他在二环外租了间房子,房间不大,房租却挺贵。他一边拿着自己写好的作品投与个大网站,和杂志社一边又在谋求工作以为继生活。晚上便通宵达旦的写作品。他坚信自己一定会在这有一番作为。
生活逼迫着所有人干着不属于自己的事,图勒也不例外。忙里忙外,东奔西走,他称之为“曲中救艺术,困苦求存亡。”
转眼间,春秋往复,图勒的生活一步步陷入了死循环,他开始怀疑自己。一副不修边幅的容貌,和退化后染上的一股子土里土气的臭脾气,让身边的人一个个弃他而去。他当过搬运工,开过出租车,卖过衣服,躲过城管。他鼓足勇气拿着写好的词投去各大音乐公司,但处处屡遭碰壁。他爱的女孩子背叛了他,亲人也一个个老去,甚至死去。他流着伤心的泪水啃着隔夜的馒头哽咽。他回忆自己的过去是何等的风光,那天晚上他做了场梦,他梦见一望无际的草原,蒙古包,还有无忧无虑的羊群,他在梦里笑出了声,久违的笑声。他醒了,呆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邋遢,肮脏,沧桑。他拿起剃须刀一刀一刀刮去了那一撮撮黑白的胡须,然后洗净脸庞,他感觉到无比的清净与自在。第二天就背起来时的包踏上了来时的路,去往了来时。
我在内蒙结识的图勒那时他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喜欢饮酒唱歌,激动之余也会吟上一首。他开着酒楼,整天游客络绎不绝,生意一片大好。他问我在哪里工作,我说在北京。一开始提到北京他便掩面感慨,后又流泪,再就是一顿狂吹他北漂的各种故事,尤其是如何为艺术献身的经历。我跪在谷垫上听他讲到腿麻。他说他现在准备开一家工作室,专门研究古诗词与诗歌。我问“有赞助吗?”他说“全部自费。”我佩服他的精神,也感激他的认真。必竟真正愿为艺术献身的人太少,而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太多。
我有个发小,从小父母便离异,他跟着奶奶生活,好在活在乡下,向来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喝水,这样一来至少不会被饿死。小一点,他靠撅野菜摸鱼虾为食,破衫褴褛,一副肮脏样。同龄小孩瞧不起他,时不时就欺负他,他忍着。春天到了他就靠采野茶挣零花钱,夏天就靠捕鱼虾卖给桥头饭店老板赚取生活费。他平淡,简朴那时他的目标就是活着。
长大后,他去云南跟着一个包子铺老板当学徒,好在他不怕苦,会说话,脑子也灵活,很受老板欢喜。老板也毫无保留的将他的毕生所学传授给他,他欣喜万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老板觉得自己年事以高,又无子嗣,决定收他为义子,并将此店交给他打理,开始的几年里,店铺生意还很红火。
老板死后店铺开始没落,他虽有一身本领但招牌没了,再好吃的东西也无人问津。思来想去他毅然决然卖掉了云南的店铺,辗转回到老家,重新挂牌,开起包子铺。从开始的朝不保夕,到生意兴隆。生活眼见一天过的胜似一天,各村的媒人也纷纷来访,必竟年纪也大了。后来经媒婆介绍娶了隔壁王村的姑娘,从此二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我的弟弟有一同学,从小便精通小提琴,在合肥的小提琴培训班待了俩月,老师便匆匆找到家长并告诉他,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交予他了,建议你们去大城市,例如北京找更专业的老师一对一受教。回到家,俩夫妻就开始合计,北京生活物价如此之高,再加上也没有认识的熟人,但孩子情况又是这么个情况。最后俩人一咬牙一跺脚,算了卖掉现有的房子,去北京。他们卖掉了合肥三室一厅的好房子在北京买了间四十平米的破房子,四环外。后来请老师,昂贵的费用压的他夫妻二人喘不过气来,但转念一想还是的活着,要好好的活着。毕竟孩子一定会出人头地,暂且的付出都是为了今后更大的回报。就这样俩人依旧每天赶着摇摇无尽的地铁和公交,在没有预期的生活里窥探着未来。
遥想古今,这么多人,这么多事。拼命的在拼命,努力的在努力。终究我们还是在为自己活着而证明。无论是为艺术献身的图勒,还是在悲惨命运里挣扎后重生的发小,而或在陌生城市为自己的下一代默默奉献的父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为活着而挣扎,小人物在为蜕变成大人物而坚持着,我也一样。
即便山河破碎,谁都要努力的活着,我甘愿在这寂静的夜,留下我的背影,等光影褪去,换你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