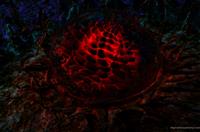三年前,我的父亲母亲相继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算而今,已有三年多时间了。岁月的飞速流转非但没有淡化我对他们的思念,反而随着时间的飞逝,更加深了我对他们的回忆。每至良辰佳节,亲人欢聚,或者在事业上取得骄人的成绩,或者生活上遇到不如意时,更多地会想起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母亲,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农村偏远山区。父亲比母亲长两岁,在艰难的岁月里,养育了我们弟兄姊妹四男一女,我排行最小,姐姐排第三。年龄稍长的人就会知道,在当时的年月里,抚育我们长大就已实属不易。但是在当时条件下,父母凭着他们的含辛茹苦,还供给我们一个个都读了书。由于时代和自然灾害的原因,我的两位兄长和姐姐,没有走出大山,依然沿着父辈们走过的路艰辛地跋涉,把改变生活和命运的梦想托付给了下一代。我和三兄出生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重视教育的七十年代,在父母亲的大力支持,兄嫂、姐姐的扶持及恩师的教育下走出了大山,三兄成了国家干部,我做了人民教师,当年一家考出两个学生成为公职人员的事在我们的家乡一时传为美谈。
当年,突然降临的家庭灾难,让父母亲走到了一起,他们虽无海誓山盟的约定,但一走就是相依相伴的六十年。父亲在别人正要享受花样年华的十七岁时,我42岁的祖母得了顽疾,久治无效,撒手而去。这犹如晴天霹雳的灾难,击碎了踌躇满志的父亲想干一番事业的梦想。父亲面对的是一个残破的家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上有悲痛欲绝的祖父,下有6岁的三叔和不满1岁的小姑母(二叔因过继给了族内的另一位祖父,有人照顾;大姑姑已经出嫁)。十七岁的父亲,面对上天不公的命运,只能将眼泪咽在心里。作为长子的他,别无选择,强忍失去母亲的悲痛,用稚嫩的肩膀勇敢地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就在这样的境况下,好心的人们给父母牵线搭桥,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共度人生的风风雨雨。在后来的岁月中,我的母亲在家中承担着多重角色,对我的三叔和小姑,既是长嫂,又以母爱般无私的情怀拉扯他们成长,二十多年如一日,无怨无悔。直到三叔成家,小姑出嫁,在祖父的安排下父母才另建了新家。
2008年冬至节的前一天,天气奇寒无比。父亲怀着对亲人特别是对我母亲的无限依恋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我们都很伤心,但我发现,其实最伤心的还是我年迈的母亲。我永远忘不了母亲时刻守在父亲灵前,就像对待父亲生前一样,一会儿挑挑油灯(据说那灯是给父亲灵魂照路的),一会儿又给父亲换杯热茶,一会又叫来我的女儿,咐咐给爷爷点上一支纸烟,那情那景,让我终生难忘。那一刻,我对“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内涵才有了刻骨铭心的理解。送走父亲不久,我就接母亲到了县城,计划让她安度晚年。但是时间不长,心中只装着亲人却很少顾及到自己,一直健康、很少吃过药的母亲就得了重病,虽多方求医,再也没有治愈,在我们没有半点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刚刚半年后也离开了我们。我想,要是父亲没有先离我们而去,我的母亲的病也不会那么快发作。事后,我详细推算了一下,自父母亲从1948年结合到父亲2008年离我们而去,他们一起度过了整整60个春夏秋冬。我在想,母亲最终还是割舍不下对父亲的牵念而追随他去了。因为我深深地知道,父亲最后的十多年里,一直身体不好,由于子女们为了生计,都在忙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照顾父亲的重任基本上是母亲一人完成的。母亲即使偶尔离开父亲几天,都是寝食不安的,总是担心父亲这样那样的。虽说他们的人生极其平凡,但默默相守60年的情感,也可以说是一种永恒!
在我的记忆里,父母间几乎没有发生过较大的矛盾,与乡亲邻里也总是和睦相处。八十年代,在村上干部分地不公、甚至违背分配规则时,父亲总是一让再让、与世无争,显得似乎有点懦弱,这曾让家人非常生气和恼火。父母遇事总是以和为贵、忍让为先。村里或亲朋中有了纠纷,总是请父亲出面解决。九十年代,乡政府干部在我村遇到棘手问题无法处理时,总是找我父亲出面寻求解决良方,在他们的眼里,父亲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村干部、信守承诺的老党员。父母亲遇事总是协商解决,即便为了一件事争得不可开交,但只要哪个子女来了,他们争论的声音会马上变低,甚至转移话题。小时的我和三兄,难免为了小事而起争执,一向脾气较为暴躁对我们管束极其严格的父亲,有时也会用巴掌教训我们,但运气较好的我们,父亲正大发雷霆时,与三叔一起生活、与我家有百米之遥的祖父总是适时而至。只要祖父来了,父亲总是转怒为喜,悄悄地放下手中的“家法”,迎上祖父,倒茶、卷烟,问长问短。而我的祖父也从不问父亲发火的原因,他们爷儿俩聊一会家常就各干其事去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作,父亲也就不再追究我们的错误。如今已做人父、人师的我,常常在想,父母为了不影响子女的心情,他们总是将不快乐留给自己。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有时虽说难免粗暴,但他尊重祖父的态度,让我终生难忘,因为现在看来他们父子俩的那种默契中似乎蕴含无以言说的育人艺术。也许祖父是母亲特意叫来的,也许是祖父听到了父亲发火的消息赶来的,也许父亲只是在吓唬,并没有存心要打我们的意思,只是怕调皮的我们走上邪路。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只读过高小, 是偏僻农村少有的一名地下党员,生前一直还享受着政府津贴。我记得,八十年代末期,当组织部调查我家(地下党员家庭)的经济情况时,父亲说现在可以自食其力,没有多大困难,主要任务是能供给两个小儿子读书。他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多年来,读书、看报和关注新闻,是他的必修课,并且对部分文学经典还有独到的见解,对历史有清醒的认识。当我给他读现代作家张一弓先生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时,他激动地告诉我,好的文学作品,都是从现实中取材的,那篇小说就是典型……说到那里欲言又止了,神情异样,我颇感诧异。后来我从别人的口中了解到,父亲的身上有小说主人公李铜钟的影子。我从小喜好文学,偶有诗文发表,后来成为一名深受学生欢迎的高中语文教师,与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他广泛的阅读开阔了他的视野,涵养了他人生的厚重,再加他丰富的人生经历,造就了深广的悲悯情怀。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初,我的父亲一直担任村干部。在是非难辨、黑白不分、人性严重缺失的文革时期,父亲正担任村支部书记。由于他对社会有较为正确的认识,对当时政治上极左的做法深恶痛绝,在他能力范围内做到了同情弱小、扶危济困,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好多人的命运,受到当地人的爱戴和好评。如今回到老家,好多年长的人当知道我是他儿子时,对我非常热情,都会感叹地说我父亲是一个好人,并给我叙述文革期间父亲是如何巧妙地周旋,阻止了好多起无端批斗好人的事件发生。最为他们称道的是,因我父亲在给乡亲们偷偷分了点自留地而要被县上下派干部组织群众纠斗时,竟无一人出面,随后我父亲怫然大怒,拂袖而去,让县上干部非常尴尬。据说,那是最能显示父亲血性的一次举动。看来人世间还是自有公道存在。他们说话时,那种因感恩而将笑意写在脸上的表情让我非常欣慰,我为有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而感到自豪。
母亲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只上过不多时日的夜校,但她能认识我们全家人的姓名,粗识一些简单的文字,准确的记着父亲和每个孩子的生日,七十多岁时跟孙子学会了接打手机,子女们的电话号码她都熟记在心,但唯独没有记住她自己的生日。当我一再追问她的生日时,她说,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我的外祖父母逃生尚且难保,哪有心思记住孩子们的生日。她只听外祖母说她出生在一个飘雪的日子,于是我就自作主张给母亲定了一个生日,约定每年家乡落第一场雪的时候就给她过生日。但是,我们只给她过了一个生日,就再没了机会。而今,每逢给家人或者朋友过生日时,母亲在她唯一的生日聚会上激动得眼泪花花的情景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我在想,父母给我们的是何其多,而我们给予他们的是何其少。我遗憾我没有早点长大,没有更多地孝敬父母,如今,已是子欲孝而亲不待啊!
父亲是一个心灵手巧而又热爱秦腔艺术的人,而母亲总是站在父亲背后默默的支持。他对秦腔艺术的热爱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每年的冬闲时间,他总是和他的秦腔爱好者朋友们聚在我家或别人家里,由请来的秦腔艺人给他们排戏。在我们的家里,经常有人来串门,即使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月,家中总是谈笑风生,充满着生活的快乐。我的母亲总是很热情,不断地给他们倒水添茶,从来未嫌过麻烦。父亲对秦腔表演,非常投入,每一句唱词,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他都要练习、揣摩好多遍。因此他的演出,总是赢得众人的喝彩。父亲很少饮酒,也没有其它嗜好,秦腔表演是他生活的唯一调剂,是他生活中唯一释放喜怒哀乐的方式,也是他化解生活苦闷的精神食粮。他在年轻时扮演过《白蛇传》中的白蛇、《游西湖》中的慧娘、《三娘教子》中的三娘等角色;到中年以后,他扮演过《打镇台》中的王震、《调寇》中的寇准、《串龙珠》中的花婆(花云的母亲)等角色。由于受他的影响,我们全家都成了秦腔爱好者,我的几位兄长和姐姐都曾登台表演过秦腔,二兄长还是远近小有名气的板胡演奏者。我们全家人,都曾从那些秦腔故事中汲取文化的养分,懂得了好多为人处世的道理。
为了生活,为了我们那个大家庭,我的父母付出的艰辛比别人更多。由于我和三兄在外读书,大兄一家远迁河西走廊,家中的劳力相较就太少。他们在七十多岁的时候,看到二兄忙不过来时,还坚持下地干活。父亲是一个干庄稼的行家里手,他对庄稼的侍弄,不亚于园丁对于花朵的热情,他对牲畜的照顾也总是充满着爱心情怀,不允许我们糟蹋一粒粮食,不允许任何人随意鞭笞牲畜。他经营的庄稼和种的菜,总是长得很好;他种的白杨树,让我家不缺烧柴,还可变卖一些作为零嚼用;他种的果树,让我们不会望着别人的果子去眼馋……父母总是对时间安排得很紧,每至年终岁末,他和母亲就已安排好了来年每块土地的播种计划。每到雨天不能下地干活时,父亲要么捻麻线以备母亲给我们纳鞋底,要么捻毛线给我们亲手织手套和毛袜;而母亲呢,总是给我们缝洗衣衫,手中从未闲过。有时,父亲也还以口袋编织师傅的身份被请到邻村帮忙。父亲一生从未睡过懒觉,当然也不允许我们浪费光阴。
父母亲对子女的关爱和体贴,让我多次感激涕零。我和三兄参加工作时,他们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工作,他们常常一边牵挂着我们,一边又打电话说他们一切安好,不要想家。当我们带着妻儿看望他们时,常见到他们倚门而望的情景,在老家度过的又大多是长谈到天明的快乐之夜。父亲很少流泪,但有一次流泪让我难忘。那是一个周日的午后,已是七十多岁的父亲,由他口述,让我代笔给远迁酒泉金塔县定居的大兄长一家写信表达问候之意和相思之苦。当我给他读信时,他的眼圈发红,泪湿衣襟,无语凝噎,让我手足无措,那是我平生看到的父亲第二次流泪。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是1982年祖父离世的时候,当时的我尚在懵懂之中,对人世的悲欢离合没有丝毫的体验。
岁月的日历一页页被无情地翻过。如今,我们都已长大成人,都已为人父母,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我在我挚爱的教育事业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然,父母亲对待事情的勤勉态度、执著精神是我在事业上拼搏不息的不竭源泉。每每回想起父母,总是不由人在心底涌动起情感的波涛,感念他们厚比高天的大恩大德,感念他们深似大海的爱子情怀。
我想,我的父亲母亲,是天底下众多平凡父母中的一例,但是,正是他们平凡生活的层层叠加,才让我们有了不断为之奋斗的事业和生活。正是天底下有无数个像我父母一样的人,才有了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和繁荣。
刚刚步入中年的我,不久前才过完了我的四十岁生日。在妻子为我张罗的家庭生日聚会上,为儿女倾尽心血的父亲母亲的人生经历在我的心底又掀起了滔天巨浪。时至深秋,窗外寒意渐浓,我坐在靠阳的窗前,陷入了沉思,父母的过往在我眼前若影片一样呈现。于是,我拿起久违的笔,写下对他们的回忆。
在我看来,回忆父亲母亲,是人生的一种幸事;回忆父亲母亲,是纪念父母的最好方式,同时也是对自己未来的鞭策与鼓励。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