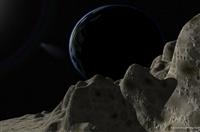怀念,家乡蒸菜的味道
一年四季,家乡的蒸菜吃不断。
打罢春,最先被端上饭桌的,是榆钱儿蒸菜。一般的植物春华秋实,榆树却是先开花结籽,后长叶片。河边的岸柳垂下鹅黄的枝条后,榆树的枝头便挂出一嘟噜一嘟噜的榆钱。榆钱小如指甲盖,中间鼓起,四缘为薄得透亮的边儿,很象动画片中外星人乘坐的飞碟。榆树就是靠这成千上万飞碟般的榆钱儿,撒播种子,为自己开拓生存空间的。捋榆钱儿要在青嫩时,否则,成熟的白色榆钱儿将随风飞散,想品尝其清香滑嫩,就为时已晚了。
暮春,正是洋槐树的花季。村庄的空地上,林场、河边、路傍,到处都是洋槐树,巨大的树冠上,披拂的全是洁白的槐花,真成了所谓的“香雪海”。洋槐花内含糖量高,引得成群的蜜蜂嘤嘤嗡嗡地在花丛中采蜜。随便在树上折下两枝,便可采足做一顿蒸菜的槐花。它的软香可口,让人吃不烦。直到现在,洋槐花蒸菜仍然常常出现在家乡人的饭桌上,其鲜嫩的诱惑,实在让人难以抗拒。
端午节前后,是吃马屎菜蒸菜的时候。马屎菜学名马齿苋,茎叶肥嫩,满含汁液,叶片总是亮闪闪地泛着阳光,开出细碎的黄色小花。大棵的马屎菜一棵就有半斤多重,要不了几棵,就够做一顿蒸菜了。
夏天要吃芝麻帘儿蒸菜。芝麻帘儿学名苋菜,大概因为叶片如芝麻叶片,才叫这个名字。芝麻帘儿生命力极强,春天随便在空地上撒一把籽,夏天就会有吃不完的菜。
能从初夏吃到晚秋的,只有红薯叶蒸菜了。红薯耐贫瘠,产量高,那些年一直是乡村的“救命粮”,它肥厚的叶片,是做蒸菜的好原料。生产队里的土地上,到处种的都是红薯,下工摘一把红薯叶,只是举手之劳,它是贫穷岁月“瓜菜代”的主力军。
秋天过去,草木凋零,萝卜却在寒冷的季节生长着。白萝卜叶片阔大,收获时只能切下来,开水焯后一挂挂地晾干,为漫长的冬天做好储备。红萝卜就不同了,从播种出苗后剔下的幼苗,到收获后拧下的叶,都可做蒸菜,特别是幼嫩的红萝卜苗,风味更佳,受到人们长盛不衰的喜爱。
吃蒸菜要有好调料,几瓣辛辣的大蒜是少不了的。除了盐、麻油,要是再配点青辣椒、芝麻酱、荆介之类,在蒜臼里捣成糊,加水搅匀,浇在蒸菜上,就算是万事俱备。吃上这样一顿蒸菜,简直是“改善生活”了——在那一年吃不上三两回肉的年代是这样,在今天吃腻了肉的时代也是这样。
仅仅三十来年的时光,蒸菜,从贫困的乡亲用以果腹充饥的“下里巴人”,提升到宾馆饭店堂而皇之接待宾客的“阳春白雪”的地位,完成了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角色转换。每当吃起蒸菜的时候,就不能不让人细细咀嚼它所蕴含的多样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