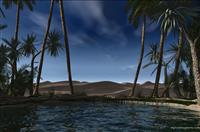到处都是人群,路旁是接送孩子的家长,翘首以待着,家店的货物或器具摆满店前,只能推车步行,况且脚踏车后轮胎气不足,专为此而去修理。
实际现在秋深,两街行柳掩映,可以为色,大街南邻西湖公园,园内有山岗及岗林高耸,朝阳在林间丹红一展,鸟鸣婉转传唱。下班则闲情,放眼望去,松弛的一天而紧张的各路神经之时,可见此路的转弯处,仍有丹阳在楼宇之间,展示出无限的温柔。
此时却不能够,要到修车老人那里,给脚踏车打气。这条不长的街道上,相距500米便有一个修车地摊,都是60多岁或70岁的老人了,50年代出生的吧,新中国后的生年有过旧时的家教吗?但绝对是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这样的老人应该是值得尊重的,他们勤劳质朴、忠厚平凡的一生,真诚的做人,愿意和他们打交道的,却又有些疑惑的。
此前,也是修理自行车的一次,到到湖滨路桥头的老人家那里,他躺在竹椅上,眯眼听着流转的戏曲,被轻声喊醒后,很快充好了自行车的气。我摸一下口袋,没有零钱,只有一张50的。就说老先生没有五毛钱的零钱,你看我明天给你,我天天从这里路过。他伸手过来接过钱,说找不开。但听说我的后半句后,敏捷的转身说,我找你吧!走开的时候,我接着那一把钱,那种不被信赖的感觉,久久不散。
所以,这次我到东面这个老人的地摊。也是经常在这里经过,看他总是一副闲不住的模样。我说能打气吗?他劳作着回头说能。见他的气筒是机械的,就说你这个气筒我不会用啊,他谦虚道,唉,下力人,我来打吧!他熟练的噗噗噗,不到十下,充足了气。我说只打一个(胎),看看几天之后是否又泄气;再泄气,那就是要换内胎了。问他打一个多少钱?他说五毛钱。我递过去准备好的一块钱,他扭扭头看一眼车摊,说没有零钱呢,要不我给你的前轮添几下气?我微微摇摇头,说算了,不用添了,钱别找了。
推车回来的百米路上,只躲避着等孩子放学的人群,并不看他们,更不会注目远处的柳林和更远处的公园,只低头感到沮丧,沮丧混乱着丝丝悲哀。不知道为什么,不觉想起了去办房产证的时候,被一位少妇刁难数次的景象,她的嘴脸和我的叹息;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了浙江温岭的医患冲突,死了的医生和要杀医生的某人。回到办公室搜索这个新闻,又寻找到类似的案件,不禁自问谁是受害者呢?谁是罪人呢?人与人之间到底是怎么了?人群与人群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吗?还是我一个愚人,孤陋寡闻,大惊小怪?
午休很好,午休使人苏醒,回到初心。午休之后的上班,人车稀少,略宽的道路上,真的可以见到朝夕相见的柳林了。柳树,这一种最早发芽和最晚落叶的乔木,人们却常常忘记或者熟视无睹,他给我们的袅娜多姿的彩,坚韧又飘扬的本性,我还在。
文章已经修理,却想到近日思虑的诗句: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