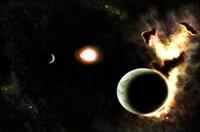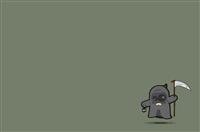在毛主席逝世后不久,震天动地的秋收大会战就打响了。当时我们也知道,虽然毛主席逝世了,可党中央还在,太阳也还会照样出来,我们还要继续生活。我们那时候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具体到每个人的实际行动就更简单了,那就是苦干、实干加巧干;出大力,流大汗,轻伤不下火线。
我跟你说,那时候我们割地真都跟玩命似得,谁有个小病小灾啥的,都不在乎;就我们女的来例假那几天,就跟没那事一样,照样你追我赶。
记得第一天割地,割的是黄豆,没在农村干过的人不知道,在割地当中,最难割得就是黄豆。关键是豆荚扎手,手刚沾上它就扎的你受不了,而且是你越怕它,它越扎你手。
在没开始干活之前,外号叫“老鹰”的张队长还给我们示范了一番,就看他右手把镰刀一挥,左手就好像抓老虎一样把那黄豆棵子抓住,就听咔、咔、咔,不一会就割很长一块地,我们在旁边看着,心里说:“真不愧叫老鹰,飞得真快!”
别看人家老鹰飞的快,可我们就差远了,一条垅都没割到头,手疼的就不行了。再看那手上给扎的全都是小眼;一个上午下来,一个个都跟霜打的茄子似得,蔫头耷拉脑。
说到这,你可能会说:“怕扎手不会戴手套吗?”
可我对你说:“不是不可以,当然可以戴,但是,你戴得起吗?”
你没想想,啥样的手套能扛得住那么扎呀!一副新手套刚戴上没几下就扎完蛋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豁出去,“老鹰”为什么不怕扎呀!就是因为他的手扎出来了,现在不怕扎了。
第二天再干的时候,就比头一天好多了。我也学“老鹰”那样,豁出去了,嗨!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灵,手当然是照样疼,但是活干的快呀!别人才割一半,可我都要到地头了。
等一条垅割到头歇着的时候,刘淑华就问我:
“国英,你那么使劲抓,不扎手吗?手不疼吗?”
“不扎手,不疼。”我故意把手伸开然后又攥上,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
刘淑华后来也学会了,也都割得快。可还是有好几个女知青,干活跟不上,那些人在家没下乡之前什么体力活都没干过,不像许丽、尹桂琴我们几个,十五六岁就在矿山器材厂干活,那活比割地都累,什么抬土、抬媒,动土方,啥累活都干过,所以,现在我不觉得太累。可有的人就不行了,如今干一天活下来,她们连腿都抬不起来。
我们女知青中,有个叫郑晓丽的,她从小在省城长大,是跟她爸爸下放来到农村的,啃书本还行,可对庄稼地的活那是一窍不通,经常被累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看着也怪可怜人的。
有一天割豆子,我们大伙都割到地头了,可回头一看,郑晓丽还在地中间晃悠呢。我就弯下腰迎着她就割过去了,我这一带头,又有几个姐妹也过来帮忙,不一会就割到她跟前了。我们原以为这下子她该笑了,可没想到她见了我们还是哭,而且哭的比之前还厉害。有的人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就开始劝她:“晓丽呀,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也有的人说:“肯定是累坏了,精神不正常了。”
话音刚落,再看郑晓丽“噗嗤”一声笑上了。
我心里想:“还别说,八成真精神不正常了”
我正胡思乱想呢,就听她说话了:“我这是感动得哭了,我精神好着呢。”
大伙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这边一闹腾,队长看见也过来了,跟郑晓丽半开玩笑地说:“小郑啊,以后可不能这样了,你这连哭带笑的弄的我们心里没底呀。”
还有一回也是收秋割地,我还是先割到头,回头帮助黄丽萍割,她也是省城来的,我们俩关系好,经常互相帮助。等我们俩打对头的时候,就见她累的腰都直不起来了,抓着我得手带着哭腔问我:
“国英,你说咱们可啥时候能到头呢?”
我和她开玩笑,用手指着黄豆垅,逗她说:“这不是已经到地头了吗?”
此时她也忘了累,苦笑着称赞我:“国英,干活我真服你,我没有你那两套!”
我还真不是说大话,就论干活,什么种地、拔地、割地,我真都干在前边,没服过谁。就连张队长、王岐都服我,说:“那小刘可真能干,一般男劳力都不是个!”
我们的手也扎出来了,黄豆也割完了,紧接着就开始割谷子,谷穗子长在头上,就像顺口溜说过的那样,一个个都笑弯了腰。
想想我们那时候一个个真都跟铁人似的,一年三百六十天,没有节假日。有个伤风感冒、小病小灾啥的,也不在乎,再说也没人管你。领导就管干活,别的事人家不管。要是见面说上几句像什么“干活时多加小心,别碰着。”“看你脸色不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等等关心我们的话,那我们都感谢的没法,那就算是领导关心我们啦。
我们在田里干活的时候,领导经常在田埂上坐着看,看到我们用镐头常喊:
“留神别刨着脚。”
我们用镰刀时,他更不放心,时时说:
“大家注意,别把手割破了。”
他老是在一旁提醒也没有用,活太多,我们必须快干,一快就免不了砍了脚割破手。手脚一受伤出血,领导看见就该不高兴了,会站起来挺着腰杆用手点着我们说:
“看看,说啥来着,让你们加小心,你们就是不听,这要都受伤了,活还咋干呢?”
听他那么说话,我们就小声在背后议论:
“听他说的是人话吗?就好像咱们不愿意干活,故意整出血了似的。”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领导也不能那么想,只是要干的活太多,再加上农活又有个时令节气的事,他也是着急上火没办法才那么说的。那时候的人都皮辣,不象现在人这么娇贵。干农村活整天跟庄稼和土垃块打交道,镐头铁锨,镰刀锄头不离手,所以,手脚割个口子,擦破皮是常有的事。
说到这儿,有的人可能就说了:
“不就是割破了手吗?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呢,用个创可贴或者缠块纱布就行了呗,也不耽误干活。”
我跟你说,那时候哪来的纱布啊!创可贴更没有,连名都没听过,别说贴了。看哪里割破皮出血止不住,就从衣服上撕下一条布包上,这还算不错的了,还有比这个更简便、更简单的止血方法,那就是用土。这个用土止血法是王岐传给我们的。
那好像是我们下乡的第一年的秋天,有一天割谷子,领导又是跟往常一样对我们叮嘱一番:
可他话音还没落呢!就听那边黄丽萍“妈呀”一声尖叫,随后又听“当啷”一声把镰刀也扔地上了,割手了。你别看那镰刀割谷子不快,割不动,割手那可快着呢,镰刀刚挨上手,就是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吓的黄丽萍爹一声妈一声地叫。
领导看着了,站在田埂上用手指着黄丽萍没好气的喊:
“告诉你们别割手,别割手,到底还是把手割了,都听不懂话吗?”
我们也没人理他,都往黄丽萍跟前跑。队长看见不高兴了,冲着大伙没好气地喊:
“都瞎跑啥呀,手破了出点血有啥好看的,离心老远呢,大惊小怪,都回去干活去。”之后就看他朝站在远处的王岐摆着手喊:
“老王,你快过来给看看!”
紧接着又说:“他有绝招。”
就见王岐赶紧跑过来,要跑到黄丽萍跟前时,抓起一把土就往伤口上抹。我们知青中有的人就说了:
“把土弄到伤口上,那伤口还不得感染化脓了呀?”
可你猜王岐咋说:“土可是好玩意,它不光长庄稼,还是止血的灵丹妙药,不但不会化脓,伤口好的还快呢。”
现在我们才明白,原来队长说得妙招就是土。
你说还真怪,经他那么一弄,黄丽萍伤口还真不出血了。从那以后我们身上哪弄破皮。都用土来止血,正像王岐说的:
“可别小看了土,那土可是治百病的。”
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王岐所谓的止血绝招竟然就是土,土不仅能长庄稼,还能治病。
割谷子也有说道,要尽量贴着地皮割,到时候把谷穗弄下来后,谷子秸秆是牲畜过冬的主要饲料,乡下人把它叫干草。这就要求割的时候,人要弯下腰,镰刀要紧贴地皮割。再有就是把割下来的谷子还要捆成捆,用几根谷子对头系个套,然后把谷子捆上,大概都捆成人的腰那么粗,最后把捆好的谷子根朝下谷穗朝上立起来,此时再看那地里一堆一堆成金字塔形状,成捆的谷子头靠着头立在那里,大家好像亲姐妹似得相互簇拥着。
割完的谷子是这样,高粱也是如此。只不过高粱长得个高,捆成捆的高粱立起来会形成金字塔形状的一个个小屋,里面有一定的空间。在田间作业的人们会躲进里面休息,以躲避秋老虎(太阳)的伤害;更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好去处。
我亲眼看见当地的农民在田间休息时,坐在那高粱秸秆搭起的小屋里一边抽烟一边拉家常的情景,有的用那很厚的书纸卷着手指那么粗的纸烟,有的是长管烟袋,都滋滋啦啦的冒着火,然后从嘴里吐出浓浓的烟雾。抽纸烟的老汉会求我们:“学生,有纸吗?啥纸都行!”
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懂他要纸干啥,还以为他们是解手用呢!后来我们才知道,敢情他们解手根本就不用纸,只要有石头和土块就足够了,要纸是用来卷烟的。实在没有纸卷的时侯,他们就用玉米皮来卷。后来我们把书纸、报纸以及洋灰袋子纸送给他们,他们都会点头哈腰,千恩万谢:“你们这些城里的后生们,好啊!
当然,在那高粱秸秆搭起的人字架形状的小窝棚里,也有过青年男女之间的恋情,随着生产队长一声号令,劳动再次开始,女青年会带着与那红高粱一样红的脸从那窝棚里钻出来,掸去头上的柴草和身上的土,跟什么事也没有一样,嬉笑着跑开。
我现在跟你说这些,决不是我一时大脑发热而瞎编,更不是空穴来风而乱扯,的确有过那方面的事。就是我们知青中,当时男女之间也有七八对恋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再正常不过的事。但不一定都在那人字架的小窝棚里谈情说爱。可我要说的是,我当时不谈情说爱,我立誓:“不当工人,不处对象,不嫁!”
我们青年点经营管理的田地,较比生产队的要少得多,不到半个月就割完了。留一部分人往场院里拉庄稼,其余的人去帮助生产队收割,当时叫支援农民兄弟。
到现在为止,农村人,尤其是那些农村女人们,看我们的眼神,不再像我们刚来到乡下时那么不顺眼了,也不再说我们是女妖精。因为,此时的我们和她们已相差无几,原本白嫩的面皮而如今变得恰似红高粱一样的颜色,梳着齐耳短发,一双手变得又粗又硬,和他们的手一样,手指如同树枝,而手掌更像树皮。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别看我们外表变得和她们一样了,可乡下婆娘有几样绝活我们一直到最后也没学会,当然我们谁也不想学,那就是说男女之间那难听的荤话、骂人和耍赖皮打架。
你说农村的生产队长厉害吧?在生产队他简直就是土皇上,但要是遇上不讲理的、耍赖皮的婆娘,那他可就倒霉了,甘拜下风。就在那年的秋天,我们去白塔子生产队帮助秋收,就赶上那么一回事。
当时白塔子生产队长与一名妇女发生争吵,那女人冲上去就要用手抓队长,出于本能,队长用手扒拉她一下,这下坏了,就见那女人“咣铛”一声躺在地上,同时抓起一把土往她自己头发上撒,张开大嘴嚎啕大哭,喊着:
“快来人啊,队长打人啦!”
这还不算,她看人们围上来了就指着队长喊:“他想强奸我。”
一边说着,还把上衣脱下来,臊的我们都用手蒙上眼睛。队长吓得都变声了,撩起上衣把脑袋蒙上说:
“我的妈呀!妈!你是我亲妈,行了吧!我求你了,快把衣服穿上吧!”
那女人仍然不依不饶:“一会我就去公社告你去,你想强奸我。”
队长彻底服了,一个劲鞠躬认错:“姑奶奶,我怕你了,你们家那个事我答应你,行了吧!”
其实我跟你说这方面的事,主要目的就是想告诉人们,我们当年在农村啥事都经着过,啥事都见识过。另外我还告诉你,在农村道德败坏、长歪心眼的生产队长也不是没有,但大多数还都是好人。
农民说:“三春不如一秋忙”。那话是真不假,从割地的场面就能看出来忙还是不忙,那真是镰刀飞舞,刀光剑影,我们一个个都使出吃奶的力气,整天是汗流浃背,脖子上系着的羊肚手巾让汗浸得都能拧出水来。你说得出多少汗吧?还有就是累不累吧?
累,出汗还不说,有些昆虫还欺负我们女生。秋天是蚂蚱横行的季节,此时的蚂蚱已长出了翅膀,乡下人管它叫“撒撒虫”,成群结队地到处乱飞,它虽然不咬人,但它落人身上很吓人。
那天刚刚干上活不久,就听任秀梅和卢秀荣不约而同地“妈呀”一声叫,大伙回头一看,原来是撒撒虫飞进她们脖子,吓得她俩七魂丢了六魂。
和蚂蚱斗还不算,还要和瞎蚂斗。瞎蚂不像蚂蚱,它咬人,吸人的血,而且是越热天,越出汗,它越叮人。我不怕累,不怕苦,可我怕瞎蚂叮!
地里的庄稼割完,要用大马车、小驴车把成捆的庄稼运回到我们居住的地方,堆到场院里。谷垛和高梁垛都像一座座小山一样矗立在场院里,而那黄橙橙的玉米会不规则地堆放在那里,太阳光照在上面会反射出刺眼的光,都金光闪闪的。
打场了,就是把高粱穗、谷穗以及黄豆棵子均匀铺在平坦的场院上,然后用毛驴拉着石头磙子在上面碾,一圈一圈地转,知道把粮食都碾下来为止。当然,也有人拉石磙子打场的时候,我们两三个女的拉一个石磙子,那也没有一个毛驴走得快。男知青笑话我门说:“看你们三个毛驴六条腿,都没有一个毛驴能干。”
我们也不甘示弱,会对他说:“再加上你这毛驴子,八条腿就能干了!”
他看没捡着便宜,就改说邪嗑了:“人家都说一个毛驴,拉两个磙蛋子,你们三个才拉一个。”
他说完,还不怀好意地哈哈大笑。我们虽不懂他说这话的意思,但从他得意的表情来看,知道应该不是什么好话。此时我们会沉默不语,要么就是横着眼睛瞪他们。
说起当毛驴拉石磙子,也不仅限于在场院里打场,春天种完地,我们也曾拉石磙子压地,只不过压地的石磙子是鸡蛋型的,用毛驴拉磙子压地就真的像男人说的那样,一个毛驴拉两个磙蛋。而我们只能拉一个,拉两个拉不动啊!你想一想,那石磙子自重就有一百多斤,再拉着它走在那刚犁过的和海绵一样凸凹不平的垄沟,那得需要多大的力气啊!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力气,再想想,我们一个个大姑娘当驴拉磙子,那又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啊!我们承受的不仅是累的痛苦,付出的也不单单是汗水,更有人格上的折磨和心灵上的创伤!我们那时候累的不行了,躺在那垄沟里,望空兴叹:“这样日子啥时候能出头啊!”
任秀梅躺在那对我说:“国英你说,咱们都不如毛驴子!驴还有人疼呢!可咱们,没人疼没人爱的呀!”
我就劝她说:“别瞎想,没听李书记说吗?毛主席逝世了,不是还有党中央吗?”
我听她没说话,过一会我又接着说:“不是听说咱们知青回城有新消息了吗?”
她听了一骨碌坐起来,大声道:“真的,你听谁说的?
这时候许丽也过来帮腔说:“是,我也听说了,可能快了,无风树不响啊!”
任秀梅高兴啊!我们都高兴,我们三个抱在一起哭,那眼泪都滚热滚热的。我跟你说,我们当时之所以能在那艰苦环境里苦苦支撑,全靠藏在心中的那个希望,就是好好干,将来好回去当工人,别无他求。我现在还经常想,甚至后怕,要是当时没有那个希望作为精神支柱,我们会怎么样?还能有今天吗?
但我还是那句话,当时苦也好,累也罢,我们从来没放弃和怀疑过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始终相信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绝不会忘记我们,更不会把我们扔在农村不管。
我们不气馁,不言败,保持旺盛的斗志。在农村三年多,除了在毛主席逝世那几天情绪低落、担心不会出太阳以外,始终对前途充满信心。所以,当我们休息一会以后,就又坚强地站起来,擦干眼泪,重新拉起石磙子,迈着沉重而坚定的步伐,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
【作者自述】
讲到这里她停住不说了,有些湿润的眼睛凝视着远方,此时她仿佛回到了刚才讲述的四十一年前那个阳光充斥的上午,拉着石磙子走在耕牛犁过的垄沟上。
眼前的小鸟在山坡的树上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叫,好像急着听我爱人下面的故事。我不像小鸟,不急,有足够的耐性。我不想打破她片刻的宁静。我在她思绪万千的回忆中等待。
此时,让我想起我自己,为了完成这次写作而做的一些努力。在那段日子里,我东奔西走,就如同一名问路的过客,在那些知青们当中问来问去,我不放过任何一次与他们接触的机会。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有机会与她们相遇在一家酒店,有幸和他们近距离的接触,面对面的交谈。当她们得知我正在写她们的时候,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说话的口气也变得一本正经了,甚至认为自己刚才的谈话是顺嘴胡说,为自己的随便感到担心,红头涨脸的看着我,连连说:“刚才说的不算数,随便说说,随便说说而已。”
我非常清楚他们此时的想法,因为,一想到自己的名字会被写进书里,今后还有可能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又怎么能不让他们脸红呢?但我同时也发现,她们非常感谢我,好像我为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他们是因为自己的经历得到我的重视而兴奋不已,直到热泪盈眶,频频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
我也为他们今天的行动感叹,感叹他们选择在裤子还穿的很挺拔的时候相见。正所谓:人生短暂,不留遗憾在人间。
那个中午我一直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有说有笑,互相倾诉着离别之情,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光景。我恨自己的眼睛不够用,竖着耳朵去倾听,不放过每个人的谈话内容。可后来他们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在那些老掉牙的歌曲声中哈哈大笑,随后又一落千丈,会在不知不觉中泪流满面,用手将眼泪抹去,如同掸去身上的尘土。
他们的举动和激动,招来餐厅两位年轻女服务员不解和猜疑,她们俩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这群人,我赶紧走过去跟她俩解释:“今天是他们知青战友们聚会,情绪有点激动,请别见怪!”
女服务员听了我的话,疑云变得更加凝重,摇晃着脑袋说:“什么聚会?知青聚会,没听说过。”
此时,我也变得有些激动,就大声的对她们说:“知青,知青不知道吗?”
这回她们俩不摇头了,但转身走出了房间,可能是我说话的声音太大,让她们感到害怕,要么就是认为我也和那些知青们一样,精神不太正常。所以,在经过了短暂的窃窃耳语后,嘻笑着快步离去。
顷刻间,我的心头感到一阵阵酸楚和不安,联想到前后两辈人形成的代沟有多么的深,它像一堵无形的墙,让两代人无法沟通。以此也更加坚定了我继续写下去的决心,否则,天聋地哑的悲剧,不能用文字呈现,真的会被生活的泡沫冲刷得无影无踪,知青们用青春和生命创造的豪迈和壮举,真的会被后人遗忘的一干二净。我甚至想到了当今社会上流传的一句顺口溜:“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看看知青那一辈;甜不甜,看看今天小青年;美不美,看看祖国山和水。”
大概是这个包房的场面太引人注目,要么就是这群人的举动让人感动,反正最后餐厅女老板亲自来了,同时还带来了炒菜,就听她说:“我代表酒店祝贺知青战友们团聚,这几个菜,是我赏给大家的”
之后就见她还给每个人满了一杯酒,举起酒杯说:我妈当年也是知青,不幸的是她没能活到今天,否则……
说到这她哽咽了!我爱人问她:“你妈叫啥名字?下乡到那个公社?”
女老板回答后,让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半晌没说出话来,就听她答道:“我妈叫俞媛媛,下乡到北塔子公社。”
大家这才知道,女老板原来是当年战友的女儿。禁不住怀念起那些已故的姐妹们:张大力、郁凤兰、赵国琴……
聚会结束了,他们在互相嘱托的依恋中离去。我望着她们远去的背影,消失在空气流动着的车水马龙的城市中。此时,我爱人好像也从遥远的知青时代回到了现实中,我对她接下来的讲述,就如同一名书痴看一个长篇小说那样,想听下文分解。
她也心知肚明,知道我的全部心思就是急于想听她们后来的经历,因此,她也不再推诿,在我面前尽情展示她清晰的记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