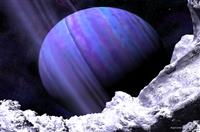我和我爱人约见许丽,当我让她讲述知青生活的时候,她第一句话就说:
“我们下乡那个破地方实在太穷,我们当时也太苦太累。”
紧接着他说了几件与她自己有关的苦、累以及有趣的事,她看着我说:
“不知刘国英跟你说了没有,我们住的那房子是人字架的,四处透风,那真是外面刮大风,屋里刮旋风;要是下雨,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下。”
这时我假装听不懂,插嘴问她:
“外边都不下了,屋里咋还下?”
她也装着不懂,笑着说:
“就说这事呢,人家都说天上下雨地下流!可天上都不下了,我们住那破房子照样流水。”
“我和你说,我们睡觉那炕,都能长出高粱苗来。”
“炕上还种高粮吗?”我明知故问。
她不理我,顺着她的思路讲:那炕抹完都没等烧干,我们就住上了。那天晚上睡醒一觉,我总感觉脚底有东西,就坐起来找,王淑洁就说我:
“许丽,你不睡觉瞎折腾啥呀?”
我说:“有毛,找毛呢!”
可王淑洁就问:
“你说啥?哪来的猫呀!”
我跟你说,她那是听错了,以为我说找猫呢。
等大伙打开灯一看,我在炕席底下拔下来一把高粱苗子,接着,大伙也都把自己褥子掀起来一看,我的妈呀!全都是高粱,我们的头儿陶秀云还故意开玩笑:
“这地方人可真会过,连人睡觉的地方都种上庄稼了?”
我跟你说,那地方风大吧!还缺水,我们这些女生洗个脸都费死个劲,屋里就是有点水明天早晨也都冻成冰。我们就用饭盒装点水,放进被窝里,被窝热乎,第二天早晨起来好洗脸。雪花膏也放被窝里。
此时我笑着问她:“雪花膏还放被窝里,晚上都睡觉了还擦雪花膏吗?”
她也笑了,说:
“擦,不擦脸干巴,再说,不放被窝里,雪花膏也冻上。”
去的那年秋天,有一天早晨我们刚刚撂下饭碗,队长就召唤上了。我跟你说吧,那时候队长一会都不让你闲着,就怕我们没活干,就听他说:
“吃完饭,上南山背谷子去!”
我就跟队长说:
“队长,谷子还用人背吗?不是有马车吗?”
队长回头看看我,不高兴,冷冷地说:
“那地方车上不去,懂吗?”
我就嘟囔一句:
“还用人背,拿我们当驴使啊!”
我这话可说坏了,就见队长用手指着我说:
“你咋说话呢?谁拿你当驴了?你不想去就别去了!”
我当时一听他说那话,连大气都没敢喘,再也不敢对付了。你是不知道啊!当时我们最怕领导说不让干活啦。明着是不让你干活,其实就是停你的产,那还了得,不仅没有工分挣,还不给你粮食吃;说不定还和政治挂上勾,甚至会影响到将来回去当工人。
我跟你说,把我吓得,后来我都不是走着去的,简直就是飞过去的,到地里背起谷子就往回走,我走得有多快就别说啦,愣是把先去的王兰芝、王淑洁她们几个给超过去了。背着那谷子真累呀!快要到中午的时候,我腿都抬不起来了,就差没累死了!
虽然说没累死人,但确实有累出毛病的,我跟你说,王兰芝就是背谷子累成胸膜炎的。
那天我看着她背着谷子往前走很费劲,就站在那喊她:
她停住用手敲敲胸说:
“这里头疼”
我一看她那样,就说:
“你准是累坏了,要不回家上矿山医院看看去吧!”
她还跟我逞强,说:
“没事,哪有那么娇乖呀!”
可当天晚上她就疼得就不行了,气都喘不上来了,我们赶紧请示队长。二卜赶车给她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胸膜炎。
当时我问医生:“胸膜炎是啥病?要紧吗?”
医生把大口罩往一边挪挪,瞅我一眼说:
“这种病不要紧,要命。”
我回到青年点队长问:
“怎么样?要紧吗?”
我告诉他:“医生说了,不要紧,要命。”
他听了不说话,好像不相信,我就吓唬他说:“医生说就是累的,以后怕是不能干重活了。”队长还是没马上说话,转身走出几步才自言自语地说:
“真他娘娇乖。”
等到王兰芝出院回到青年点,队长就安排她去喂猪。当时还对王兰芝说:
“喂猪去吧,喂猪用手喂,用不着胸。”
<作者旁白>许丽不是专程从锦州赶来,更不是给我做专场演讲的,而是途经北票与我爱人相约作短暂停留。我们仨人相见在公园的长椅上,当她二人见面又像当年那样手拉着手,坐在那长椅上想说点女人间的悄悄话,此时我选择离开,但我不会走远,我像个哨兵一样在那棵树下守着她们。
当她用些许锦州口音讲述完前边的故事,我丝毫没有让她离开的意思。我看着她,几乎用恳求的口气说:
“请你再讲点当时有趣、快乐点的事好吗?哪怕是一点点!”
她听后笑了,像是用感激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是我正在为她做些什么,她是因为包括她自己在内知青战友们受到别人的重视,显示出了喜悦之情,所以才对我爱人说:
“真的是很感谢你们家赵老师对咱们知青的关注呀!真的是太感谢!”
之后又说:“那我就说这么一个事吧!”就听她说:
别看干活累,可吃饭简单得很?高粱米籽、苞米面饼子是顿顿少不了的,更没有菜。刚到青年点那几天,我吃不下,见着那高粱米饭就够,我懒得瞅它。有一天吃饭,队长看我不吃就喊:
“许丽,许丽。”
我没好气地说:“那么高声喊啥呀?我不聋。”
队长说:“吃饭。”
我说:“我等菜。”
队长就说:“想吃菜回家去吃,这管饭不管菜。”
我说:“那米饭都拉嗓子,喂猪,猪都不吃。”
队长开始给我上纲上线了:
“你这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姐作风,革命群众就得吃这个。”
我再不敢抬头看他,低着头看桌子上两个菜,一碗盐水,几棵葱叶,还有那破高粱米饭,眼泪掉下来落到盐水碗里,盐水更咸了。
<作者旁白>此时我注意到,她眼眼睛里真的有了泪水,为了分散她的情绪,我就问:
“为啥说是破高粱米饭?”
就听她说:
“高梁都没睁开眼睛,米能好吃吗?”
我看她还是说苦故事,就提醒她说:
“还是拣点高兴地说吧!”
她开始想起来了,笑着对我说:
“看我这记性,总觉得苦事说不完,其实也有很多惹人发笑的事。”
说到这,她问我爱人:
“国英,你还记得他们男知青用耗子吓唬牛那个事吗?”
就听我爱人说:“
不记得,当时我可能干别的活去了!”
于是,她开始讲“牛”故事了。
那好像是我们下乡的第二年春天种地的时侯,有一天我们男女一大帮去西山去种地,种地都是男的扶犁杖,女的点种,西山离我们青年点有四五里地,中午走着回来吃饭,累的腿都抬不起来,可那也得走啊!人家男的不走着走,人家骑牛。可那老牛也累呀!走得很慢,男知青们嫌牛走得慢,也不是谁就想出的馊主意,把抓来的耗子用绳子拴上,人骑上牛背以后,把耗子挂在牛角上,把牛吓得跟疯了似的飞跑,我们女的看了以后都吓得东躲西藏,还妈呀爹呀地叫。牛一撒欢到家了,你说他们男生有多坏。
<作者旁白> 讲完这些许丽走了,我们笑着分别。她给我扔下一个“牛”故事和一大堆苦和累的经历。其实与牛有关的趣事黄丽萍也讲过一个,只不过她是用手机微信,通过语音讲述的,但牛都是一样的,都是拉犁杖种地的牛。
就听黄丽萍在手机那头说,那时候我们都非常封建,男女知青之间基本没有交往,甚至都很少说话。和我一块种地那男的,我们俩在一起干了好几天活互相都不说话,更不知道姓啥叫啥。那男的宁可跟牛说话也不跟我说话,你说气人不气人?
我听黄丽萍这么说,心里感到困惑,就问我爱人:
“之前都是同学还至于那样吗?我好像没听你说过!”
我爱人就说:“你不知道,包括她,还有郑晓丽、二公子等好几个知青我们之前不是同学,它们是从沈阳随父母下放来到北票后,又跟着我们一块下乡的,因此,男女之间很少说话!”
当她说到一半的时候,我已经顿悟,此时用手示意她听下面的手机语音,此时听黄丽萍正讲到男知青和牛说话,就听她学者当年那个男知青口气说:
“老伙计,你比我都强啊!到地头上还有同伴跟你说说话,可我只能跟你说话呀!”
你说他说话有多气人。
那牛到地头不听话,他就拿皮鞭子使劲打那牛,最后他把鞭稍打丢了,他就转圈找呀,我也不知道他找啥呀!也跟着瞎转悠,最后他都找到了,可他不告诉我,我还在那瞎转悠呢!他这才跟我说一句话:
“你找啥呢?”
我说:“你找啥我找啥!帮你找呢。”
他说:“我找鞭稍呢”
我就说:“那我也找鞭稍。”
接着就见她从身后把鞭梢拿出来摆弄着说:
“我都找着了,你还找啥?”
当时把我气得,真想抓把土攘他脸上。
当时在青年点啥活都干,不都是种地的庄稼活,空闲的时候也搞一些副业,用我们领导的话说就是不能让我们闲着。好像也是1976年的冬天,我们自己烧酒了。刚开始大伙都不会烧,在当地请一个说是懂烧酒的师傅,可来了才知道,也是个二百五。点火那天早晨,大伙都早早来看热闹,队长用手指着劈柴对二公子说:
“下去点火。”
人群里有的人就问:
“真要点火呀?”
队长赶紧说:
“那当然,烧酒,烧酒,没有火咋烧啊。”
二公子拿着火柴对着劈柴开始点火,可点了半天火也没着,队长急了,对着下边喊:
“你磨蹭啥呢?点火呀。”
就听二公子在底下说:
“队长,木头太湿,点不着。”
头几天下的雪,再加上没有引柴,所以点不着。队长更急了,又开始背着手来回溜达了,嘴上还说:
“我就不信知识青年的火还点不着了。”
说着卷了卷袖管就准备自己动手。有人说:
“浇上油,一点就着。”
队长一想,然后说:
“对呀,他娘的,我咋没想到呢?快去食堂取油。”
我们几个女的就站在一边看着,看着他们把好端端的豆油倒在劈柴上。我们就想:
“一帮败家子啊,那油可都是我们从嘴里挤出来的呀,就那么一把火给烧没了,太可惜了。”
可想归想,火还是点着了,劈柴浇上我们吃的油,火苗子忽忽地往上蹿。火上边是大铁锅,锅里是红高粱,底下一烧火,上边黑烟冒出来。
队长就问请来的“二百五”师傅:
“这冒烟了,看看咋整?”
师傅说:
“那咋整呀,不烧火也烧不出酒啊。”
队长正愁没法呢,就听四眼说:
“铁锅里应该放上水。”
大伙听了笑,队长说:
“放上水,你小子是想煮肉吧。”
四眼接着说:
“要不酒没烧出来,锅底先烧烂了。”
队长听了这话,眉毛往上一吊,看看大伙说:
“还别说,这小子说的还真有点道理。”
随后他冲大伙喊:
“来,往里放水。”
四眼听队长表扬他了,心里更高兴,下去烧火去了。这时队长冲着地下喊道:
“烧酒的事就听四眼的了,二卜烧火。”
其实四眼是出了个馊主意,大铁锅里还真放上水和高粱,锅底下架上了火,又盖上个木盖,就这样烧起酒来。里面的水一开锅,那木盖就扑扑地跳,水蒸气呼呼地往外冲,这烧酒跟煮肉煮饭还真差不多。
队长一会就过来看,第一回揭开木盖时,里面发大水似的冲出来蒸汽都吓得他跳开好几步,嘴里还喊:
“烫死我了。”
等到水蒸气少一些,他就拿着个干瓢去接木盖上的水,然后送到嘴边用舌头品尝,吧嗒吧嗒嘴说:
“他娘的,这也不是酒啊。”
以前都认为酒就是蒸馏水,木盖上留下来的就是酒呗,可烧了还几天,酒也没出来,最后锅里连高梁都烧没了,还是没有酒。后来李书记领着个技术员来了,在技术员的指导下,这才烧出了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