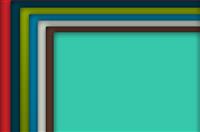后英雄时代
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总觉得,这样填词的,才算是男人。
没有他,华夏,太寂寞。
终于,魏晋,在笔下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渐渐远去。后英雄时代的悲剧,也已被使人翻拍了无数次。真的,写这篇后英雄时代很难很难,每下一笔都承载了太多的负重。夜已深了,猛地想起了他,稼轩。很欣慰,深夜竟有他相伴,走访那个治世中的乱世。就为这,熬他个通宵,也值得。
他是个悲情英雄,或许,是他生错了年代。亦或许,错其实是对。不幸,实为万幸。也只有南宋,才是它的归属。若生于一个狼烟四起,民不聊生的年代,他也许会成为一代名将,点兵沙场,也可能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而还,继而被历史的烟云所掩盖。名,不是谁都能成,也不是任何时候皆可成。
稼轩出生前十三年,北宋为金所灭。自幼生在敌占区,使他内心充满对女真统治者的仇恨,和杀敌报国的凌云壮志。早年丧父,辛弃疾由祖父辛赞抚养长大。辛赞虽投降金国,民族意识却始终未曾泯灭。于是,十四岁的稼轩,便受祖父委托,以赴进士为名,到燕山考察地形。随后,又招募乡勇,率两千部众,投奔由耿京领导的起义队伍。二十一岁,他追杀叛徒义端和尚,追回义军大印。之后,在南归复命途中,得知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辛弃疾只带五十轻骑,奇袭五万金兵镇守的济州城,直闯敌营,生擒安国,押送临安斩首。一时间举朝震惊,“壮声英慨,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二十三岁,已是“壮岁旌旗拥万夫”(辛弃疾《鹧鸪天》),已是金戈铁马的烽火生涯,已是驰骋疆场的王者气概。而我们,二十三岁,又能如何,除了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之外,只要不迷醉在灯红酒绿的喧嚣闹市,不因一场花期短暂的恋爱而自甘堕落,已实属万幸。时代,早已不是少年的时代。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因为不曾经历,所以很难理解。最多,也只是捧着书本,在课堂上高声的诵读。那声音,太沉闷,太空洞。若只为了考卷上更高的分数,全然不会多想,中原大地,尚且有这么一位英雄,于国家走向末路之时,挺身而出。“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范开《稼轩词集序》)。填词,绝不仅仅是慷慨忧愤的曲子,其意,更是悠远,更是深邃。笔下,行云流水般的,还有充满卓识远见的长篇奏章。《美芹时论》和《九议》,这些对复兴大业进行具体规划的策论,“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论衡》之风。”(刘克庄《辛稼轩集序》)。梦是他的,可命运不由他说了算。朝廷,主战与主和闹得风风火火。重用与否,更只在天子一念之间。错,就错在当初太过信任着朝廷。既然走到今天这步,就必须接受这宦海沉浮。
夜凉如浸。我想,人,只有两个结局可以接受,被对手打败,或是被自己打败。但,就恨被现实打败。败的惨烈,败的不甘。一个人,贪图享乐是错,苟且偷生是错,可过于执着也会是错。而且,错的比前两个更深更彻底。我很清醒,很清醒的认知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愈是追求,愈是得不到。奇迹,竟总在不经意间发生。命运,是上天和自身共同决定的,掌握在人手里的,只是一半而已。或许,连一半都不到。我们,被现实骗了。听过那个苏格兰寓言吧,一个王子,六次起义失败,心灰意冷,可当他看到狂风中,蜘蛛七次结网成功,便顿时有了信心,终于在第七次起义中获得成功。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我们也因此懂得了执着,学会了执着。就这样,思想已经走到了一个极端,一个片面概括整体的错误。他很幸运,仅仅是幸运而已。他成功了,可失败的又有多少?没人会去想。就像冠军永远只有一个,可其他人的付出也未必比冠军少。华夏河山,只属于那么少数几个人,登上至尊的顶峰,身后,究竟有多少人,湮没于历史的长河,化作繁星点点,化作沙堆座座。一将成名万骨枯,历史却只能容的下一将,容不下这万骨,历史,太累,太无情。成王败寇,世界就是这样,更多选择记住成功者。世界,太难,太吝啬。
青春,之于人生,太年轻。人生,之于历史,太年轻。年轻既是资本,也是错误的源头。成功,本是一种失败,因为成功过后,生命便走到了一个结点,历史也会因成功而停滞。
而狭义的失败,往往会促进人类的发展。年少,对成功的渴望是难免的,就怕成功后的沾沾自喜,还有失败后的自怨自艾。年少轻狂,是无休止的誓言,换回无休止的抱怨。无法逃遁的空虚,要用一味的妥协退让,抑或是无法估量的自我优越感来填满。我们,要么把自己定义为神,不惜一切代价的争取,最后,竟被命运嘲笑。要么把自己看得很淡,不思进取,自甘堕落。两种心境,无不是一步步,把自己逼向无底的深渊。哪怕是走到了绝路,也不过是淡然一笑,看似随意,看似豁达,看似释然,可是只其中包含了多少苦涩,多少酸辛,多少失望。唯有自知。也不想为他人所知。那样,这会给自己平添更多的痛苦。掩饰,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解脱。我们,除了年少让人嫉妒,还剩什么呢?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
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真的英雄,从不承认自己是英雄。不是谦虚,而是包含对现实与时代的敬畏。我想,稼轩能懂。一个将百夫长的思想凝结于笔端的文人,定是不愿与那满朝文武,一起卑躬屈膝,向敌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好想当年,好想当年北方的峥嵘岁月。韬光养晦,我匣中的宝剑何时出鞘?不过是个江南游子,“江头未是风波恶,最是人间行路难”(辛弃疾《鹧鸪天。送人》),我不适合这官场的明争暗斗。想归隐,家却在那沦陷的北国。大丈夫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而还,幸也。可面前,是关河路绝,是山河破碎,是“南共北,正分裂”(辛弃疾《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不想,不想再苟活在这个狭小的江南,哪怕是这个多湖多雨多寺庙多多燕子和风筝的江南。无尽的痛,还是无尽的痛,挣扎在崩溃的边缘。想想曾经,曾经我们也是泱泱上国,也是万邦来朝,长安,是矗立在第八世纪的纽约,西来的骆驼,风沙的软蹄踏大汉的红尘。而今,是不断缩小的版图,是南逃的悲剧。
多想重回故乡,或许,一切都是多想。
是的,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和这时代一同沉沦。
少年的回忆,是人和人,是考试和考试。杜拉斯说:“当一个人开始回忆的时候,他就已经苍老。”那么仔细想想吧,你,是否已经开始遗忘。原来,我们连唯一值得骄傲的东西都失去了。用一种悲情的格调来写文章,累人,累心。可不是我不想高昂,是这些受了伤的少年,是这个受了伤的时代,实在找不到高昂的理由。理性的看待现实,是自私,是冷酷,是懦弱,是麻木,是残忍,是无情。坚强的外表,实际是脆弱不堪。受伤的灵魂,实际已学会了隐忍。我们的命运,就像是古罗马的角斗士:要么打败对手,要么被对手打败。树敌无数,连人之初始的善良都荡然无存。我们,渐渐成熟,青春的叛逆,被无情的压制,取而代之,竟学会了服从,是被动的服从。就像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就像是欧洲大陆中世纪的德意志民族:精神上激情勃发,无所拘束,生活中却喜欢循规蹈矩,一丝不苟。灵魂在上帝与魔鬼之间徘徊,现实世界又绝对服从命令。思想是在为人性而歌,但实际上残暴不仁。从内心到外表,无处不体现着矛盾。德意志,集创造力与毁灭性于一身,换来的,不过是百年的分裂而已。路,开始变得模糊。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语还休,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辛弃疾《丑奴儿》
终于,辛弃疾,选择了沉默。
就像一切都从未开始一样,或许,一切都不该开始。
夜由未央。九零后,用笔蘸着泪水书写疼痛。是无尽的抱怨,是辛辣的讽刺,是感人的诉说。路,还长。我们,只能奔向那遥远的远方,奔向那不可知的命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究竟,我们会遇到什么?沧桑的几十年过后,我们,将怎样可待今日的思想,今日的文字。也不知道,这十八年受过的伤,算不算是挫折。这时代,这少年,算不算是一种痕迹。多想再回到童年,回到那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切,也仍是多想。
没有熬完这个通宵,辛弃疾和他那个治世中的乱世就悄然凝结。不去多想,静静的,酣然入睡。
梦里,定会有人来接我,接我会前世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