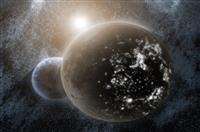在儿时,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听过童谣,甚至唱过童谣。一首童谣,那就是一个故事,就是一幅童画。
不时,在心里吟唱。
螃蟹歌
很小的时候,大人就教我们唱《螃蟹歌》:
八呀嘛八只脚哟喔,
两个厉害的大夹夹,
一个硬壳壳。
横起横起爬下河,
立起立起滚下坡。
那天从你门前过,
你夹住了我的脚。
夹呀嘛又夹得紧,
甩呀嘛又甩不脱。
痛呀嘛痛得喊爹妈,
眼泪水儿掉下河。
夏天,河滩的石板烫得我光脚板直跳,一脚踩进天井窝,从石块下被吓出来的那只躲在天井窝里乘凉的螃蟹。
瞧,它瞪着两只眼睛,举着两只大夹钳,张牙舞爪,趁你不留神,就会夹住你的手或脚,叫你甩也甩不脱。
我怕它,但至今都很喜欢它。
喜欢它大模大样,横行霸道的样子;喜欢按住它的壳,逗它向你张牙舞爪;喜欢把手从它眼前晃过,让它抓也抓不着;喜欢它瞪着双眼,向你发怒。
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唱这支歌谣,但唱得很斯文。不像我们那时,唱起这支歌,很卖力的吼,左右跺着脚,舞着双手,到处乱夹。
点兵歌
月夜,月色朦胧。
院坝里聚了一大群伙伴,做“逮雁”的游戏。参与游戏的要由两个头领点兵,把伙伴们分成两头。于是大家吼起了点兵歌:
羊子下山来点兵,
点到哪个就是我的兵。
小米小虾由我选,
大兵大将由我挑,
挑到哪个就是我的大头兵。
点兵歌本来是头领唱,结果大家喜欢一起吼,吼得越凶越过瘾。唱一个字就点过一个人,唱最后一个字,落在谁的身上,谁就被点中,成了大头兵。
有时点兵的人发现最后一个字落到跑不快的人身上,他就会故意把最后三个字唱成“大头头兵”,好跳到下一个身上。但另一边的人就不答应了。因此,花在点兵上的时间往往就很多。
不过大家也很乐意,把点兵歌多吼几遍,其乐趣还大于逮雁游戏本身。
我经常是属于很弱的“雁”,跑不快,头领都不愿点我,最后往往是哪方人数不够,就把我摊派给哪方。有一次,作为摊派的兵,被敌方头领追击。眼看快被逮住,回不到自己这方的“雁窝”,索性,我扭身往院外的田坎跑去,逃脱了敌方的魔爪。敌方提出了抗议,但抗议无效,因为没有规定不准跑出院外。于是我成了敌方始终逮不到的野雁。
下一次,头领都争着点我的兵了。
点兵了,点兵了!点兵歌又唱起来了:
羊子下山来点兵……
但月色下,哪还有伙伴们的影子?
往日的“大头兵”,你们在哪里?
日白歌
我家院子,有个伙伴叫金生,比我大个三四岁。知道的故事很多,唱的童谣也很多。
他问:世界上的动物哪个最大?
我说:是大象。
他说:错。是海里的鲸。
他问:哪个动物命最长
我说:是人,长命百岁。
他说:错。是鳌。
他问:我们的陆地下面都是水,为什么没有沉下去?
我说:地下是岩石,没有水。
他说:错。地下没有水,啷个打个水井就有水?
我答不出。
他说:我们的地下有四只鳌,在大陆四方撑起的,所以有水也不沉下去。鳌一直撑到现在,你说他命长不命长?
我就一直相信了,地下有四只了不得的鳌。不过后来才知道,他这讲的是神话。
金生不但会讲神话,还很会吼日白歌。
“昂——”有牛叫一声,就知道是金生要去放牛了。牛还没有看到,金生“日白歌”的吼声就先响起了,一直从牛圈,吼过院边的竹林,又在田野上吼:
日白就日白,日个白来了不得。
我三岁走成都,四岁走川北,
五岁飘南洋,六岁到外国。
牯牛生个儿,三天就犁得。
公鸡生个蛋,蛋里装条蛇。
我拿起手去砍,一砍砍成三半截。
捡到一根棒棒糖,一吃吃到丹凤场。
捡到一匹布,一扯扯到龙安场。
布上有只鹅,一飞飞到临江河。
夹起二两泡泡肉,办了酒席十八桌。
吃得像个偷油婆,个个胀断裤袋索。
金生的日白,很神奇,但不是神话。
日白,是方言,换一个说法叫冲壳子,再换一个说法叫日天冒狗。还不懂,那再换一个说法,叫吹牛,吹大牛。不过吹牛,哪有日白来得有趣有味。
金生,什么时候,再听你吼日白歌,并且用川剧腔:
牯牛生呐个儿呀,三天就犁呀得。
我们给你帮腔:
三天呐呀啊就犁得,
就呀犁也得呀啊得……
童谣,是快乐的源泉,它让人童心不老。
童谣,是春天的小鸟,轻轻一叫,便拨动了我的心弦,唤醒了我的童年。
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