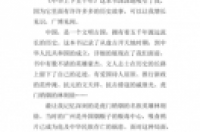《弗兰肯斯坦在巴格达》是一本由[伊拉克] 艾哈迈德·萨达维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32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叙事与故事都说不上有什么出彩之处,背景完全成了作者拿奖的工具,小说写成了符合西方人想象的样子,也算是种本事了
●科学怪人,生于战争制造的支离破碎,被复仇意志复活,于现世执行称义的审判。但在面对受难者不止,无罪者难辨时,救世变成疲惫虚妄的无限杀戮,救世主只是彷徨乱闯的科学怪人。渐渐地,科学怪人的存在价值只是为抨击敌对,曲解恐怖、混乱、糟糕制造理由。小说塑造伊战以后,乱世难平,欺世障目,恐惧横行,浮生无明的众生际遇:街头黑帮,幕后权势,趁乱自大,不择手段;不动产商巧取豪夺,无惧冒险地投机逐利;记者顺着模仿之路平步青云...唯一例外的老妇出入教会,坚守破屋,把希冀变成信仰来抱持,看似丧失理智,实则有着叫板战争、以爱续命的逻辑——在同样的逻辑下,她剪下圣像,丢弃战袍与矛尖。
●温柔中混杂着冷酷的幽默,有点让我想起大师和玛格丽特
●乱世巴格达的群像剧。这本书的有些东西没法简单说是成功还是失败,比如写独居老太太的那些章节,叙事节奏就变得特别缓慢凝重,乃至于飘忽起来,真的是一个孤寂老人的幻境。这些描写是很有味道的,然而老太太相关的故事跟别的剧情却有些脱节感,放在全书剧情里就觉得奇怪了。书中也有别的这类问题,但我没能理清思路。
●读过的第一本伊拉克小说,翻译很流畅,故事不错。推荐!
●算不算战争奇幻小说?叙事冷静画面感超强,拍成电影肯定卖座。不知道改编权拍出去没有?好本子啊!
●伊拉克小说,极具画面感,但不是什么美好的画面,如果拍成一部电影也是看起来心情也不会好吧。ps:今年竟然能读完~
●“弗兰肯斯坦”之长久被国人所误解有三,一是其实它并没有名字,弗兰肯斯坦是造他的人之名;二是它并不是怪物,纯然是洛克所谓的“白板”一块;三是它的邪恶并不源自科学力量之不可控,而是周围人误解的结果。萨达维把“弗兰肯斯坦”借用到自己的小说里,套用悬疑故事的外壳讨论了伊拉克战争后的人性境遇,毫无PS痕迹,特别好读且意味深长。
●连起来差不多八小时读完,看得手都开始抖起来。宗教,政治,奇幻传说,所有的元素都是我心头爱。这个迷人,危险,可怕,恶与神圣同在的地方,欲罢不能。
●翻译再流畅一些就好了。“那些支离破碎的伊拉克居民才是主角”,可贵的书写。
本书入戏相对较慢,剧情展开以后颇为吸引人,行至结尾正期待惊天大逆转时,又平平淡淡地收了场,于是只能安慰自己这是生活不是美剧。若用平常心去看待这本伊拉克小说,仍是可圈可点。作者想表达一个宏大的主题,被服务于小说本身的形式,点到为止。 ”弗兰肯斯坦”是什么,国家被颠覆、法则被破坏、家园陷入混乱时,众人用“以牙还牙”的罪恶拼凑出来的巨兽。巨兽自以为替天行道主持正义,却在以暴制暴的杀戮中迷失自己,最终沦为为了活下去而不分好坏杀人的罪犯(还认为自己合乎道德,反正巴格达每天都要死好多人,无论好人或者坏人)。看似莫大的讽刺,其实这样的人性再常见不过,几乎书里的每一个主要角色或多或少都浮现出这样的影子,每个人都为自己背负命运的十字架而自怜不已、自以为合乎某种道德或是天性、背地里却打着小算盘自私自利。正是每个人——每一个不是百分之百受害者、也不是绝对犯罪者的人——各自的这份罪恶,合围拼凑出了这个心理甚于物理的罪恶巨兽,滋养着恐惧、散播着暴力,大家在恐惧中变得更绝望、更自私、更暴力、更麻木、更自我催眠。国家每况愈下,家园永变异乡。 混乱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小说并没有详细的论述这个话题,入侵者肯定算一个,只言片语中都能感受到作者对美国的反感:“美军可能是没有能力,或者说不愿意解决暴力问题,因此才会想创造一种均势的暴力平衡”(可暴力平衡不就是弗兰肯斯坦所追求最终又因此而迷失的方式吗?)。原罪当然也算:“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有罪的,在各形各色的黑之中,人心的幽暗最为漆黑”。人类狂妄自大亦不可或缺:“人类过于志得意满,向来都不会承认自己的无知,也不会承认自己对于这些事背后的法则一无所知”。本书不是严肃的历史类书籍,问题答案更有赖于我们自己去探索、去反思,作者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天窗。 虽然巴格达和奥斯维辛形式迥异、性质不一,但这都不影响它们作为地狱级人性试炼场的历史意义所在。尽管“弗兰肯斯坦”是虚构的,但书中描绘的巴格达和众生相却真实存在,我们可以看到那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西方国家推翻独裁统治后建立起来的民主社会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在独裁年代经历了九死一生,到了新的‘民主时代‘却死得一文不值”,这是暂时的阵痛、还是真正的倒退,没有谁能确定,美国人自己也给不出答案。 近段时间围绕着HK,大陆建制派和自由派嘴仗打得不可开交,我以前也向往自由和民主,但现在也并没有那么一厢情愿。我希望自己努力做到不冷漠、永远保持好奇心,见众生、见天地、见自己。
现代巴格达早已不复它的荣光,在这里,每日都充斥着暴力、痛苦与勉力度日......
这是一种书中描述的事实,作为部分的关键点,它也是书中的主线之一。本应被引路天使接引而去的灵魂本不存作为游魂的可能,是暴力,暴力的袭击毁却了他的肉身,从而成为无肉体的游魂。灵魂与智慧作为真主后天赋予人类的禀赋,并不天生存在于肉身之中,这才给了“无名氏”以寄身的机会。正是这种较为出格又合乎情理的安排,才使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苏生。无名氏不依靠电流这种“亵渎”的手段复生,而是“魂兮归来”,这无疑暗示了本书中的弗兰肯斯坦不同于玛丽·雪莱的怪物夏娃,无名氏并无触犯禁忌,他也并非“堕落”。自始至终,他都有一种带有神学意味的使命感,即使这种使命感被他无奈的维生手段所冲淡,然而他仍然是无名氏,一个由不留姓名、不著声名之人聚合而成的复仇者,他的维生一开始就是复仇,即使到了结束,即使被人利用,他仍然带有着复仇者的因素。
若以一种相对传统的口吻来反驳,即“不记名的抵抗并不构成抵抗的主要部分”,而且如果在书中引章摘句,我们也会发现无名氏不仅对其构成部分的仇人进行了复仇,同时也在或主动,或被动的使用无辜者的肉体。这当然是难以反驳的,无名氏的复仇并不改变伊拉克正在继续倾颓,在用暴力对暴力的还击之上,是美军和伊拉克政府掌握着这种暴力的均衡。弗兰肯斯坦是无数属民的聚合之物,难道弗兰肯斯坦便能脱离这种暴力的均衡而存在吗?但是他仍然以一种圣战士的热情、以一种属民的无奈去尝试对此还击,这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无名氏对于无辜者肉体的使用,与其说是他“被暴力所吞噬”,不如说是暴力本身就是无名者的组成部分。暴力是抵抗的源泉,同时也是痛苦的源泉,这种源泉并不汇聚成一条河流,但是巴格达的属民却每天都沐浴其中。无名氏的两个面相便说明了这种暴力的均衡,以弱者的视角,他最终也未能见到监视着他的马吉德准将,而准将却也只是美军驻扎下的伊拉克政府毛细血管的末端而已。这是一种痛苦,这也是一种现实,这种暴力的均衡必将被打破,然而打破的契机内生于诸众,作为诸众投影的无名者是运动的第一声啼鸣,却不能代表运动本身。
无名氏的存在是一种悲剧吗?就像是前段我们讨论过的那样,即使他努力过,“情势也在一天天的坏下去”,他的缔造者用自己的生命付了债务,他寄托自己情感的老太太在内战的威胁下也迁去了澳洲。最终陪伴他的只剩下失去了自己面庞的圣骑士与基本不剩下毛发的老猫,这是一种悲剧吗?很明显,作为一种书中之书,这本书也并不能超越现实的枷锁,弗兰肯斯坦可以、本可以飞的更高,但是他已经触到了现实的壁垒,并且这种壁垒可能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不减反增。比起发问无名氏的存在是否是一种悲剧,不妨我们应该问问:我们的现实是否又是另一种悲剧?
庆幸的是,关于伊拉克战争,我们能接触到非美国主流媒体的声音。所以大致可以了解到曾经萨达姆的血腥独裁、美国人对伊拉克内政的粗暴干涉和武力入侵、战后的混乱与凋敝、各种武装派别和恐怖组织惨绝人寰的平民轰炸和恐怖袭击。但更为细致的了解,又多来自于各种英美影视、文学作品,美国人及其同盟永远是事件的主角,支持者宣扬着他们一向自以为是的救世主情结和英雄主义行为,他们是战胜邪恶、给人们带去自由与希望的福音战士,对他们造成的混乱、灾难与伤害绝口不提;反思者或疑似“反思者”则细心地描述着战争对英雄式的美国大兵的精神摧残,最多虚伪地通过“悲天悯人”的美国“英雄”的双眼看到伊拉克也有无辜的儿童与平民。作为真正主角的伊拉克人民,却永远被模糊在西方世界投射的聚光灯之外,没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也没人在乎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当摄像机跟着美国人的坦克走过巴格达的街道,本该作为主角的他们在镜头前一闪而过、成为背景,从不曾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未打开书页之前,仅伊拉克作家关于战后巴格达故事这个事实本身,已经具有了别样的价值与吸引力。
这不是一部英雄主义的故事。被称为“弗兰肯斯坦”的无名氏,听到可怜人的呼唤而来,为替他们报仇而生,化身为“复仇天使”:“要在这世上实现最终的正义。人们再也不必煎熬地痴心等待,不必等到死后上天堂才见到迟来的正义。”(146页)但什么又是正义?“只要是拿武器的人,哪有谁是无罪的呢?”(161页)“没有百分之百的受害者,也没有绝对的犯罪者。”(239页)他并不是正义的化身,也并非救世的英雄。他如同不同人的合体,善良与邪恶共生;他又如个体一生的缩影,善行与恶行同存。从最初为受难者复仇,到最后滥杀无辜只为不至消解地永生,从他诞生起,就在正义和邪恶的交叠、模糊与退变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他就好像杂志社老板赛义迪想要拍摄的电影,“中心思想是众人如何一起造就出邪恶之事,但同时间却都自称是在对抗邪恶。邪恶就在我们心中,而我们却只想从外在消灭邪恶。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有罪的。在各形各色的黑之中,人心的幽暗最为漆黑。现在危害大家的邪恶巨兽,正是我们共同拼贴而出的。”(254页)他不是唯一的主角,他像一种隐喻、似一条线索,勾勒和拼接出战乱之下,形形色色并不都是高尚的小人物的悲剧:固执地等待二十年前走上战场后杳无音讯的儿子归来的伊利希娃太太,突然失去视如己出的徒弟后古怪乖戾的拾荒者哈迪,从充满正义感到渐渐不知何为正义的记者马哈茂德,唯利是图的地产商法拉吉,一心想着自己的前途和官位的马吉德准将……这些似曾相识的普通人,在灾难下抱着对过往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寄、对灾难的痛苦和对正义的渴望、对邻友的关心和对仇敌的恶毒,怀着自己或悲天悯人或自私自利的小心思,在创伤中艰难地生存。这里,不是美国电影中英雄登场的华丽舞台,而是战乱中还努力生活着的普通伊拉克人的巴格达。
奇幻的故事背后,是战争残酷的触目惊心。随时出现的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已经侵蚀到每个普通人的内心深处。有时人们变得麻木,死亡好像拾荒者哈迪身上难闻的气味,“那些味道吸久了,也就没那么重了,像是没有味道一样。”(192页)死亡好像变成了与己无关的新闻和数字:“他就等着这具尸体的家属前来,把它移到墓园之中,撒下泥土,将它/他们安葬。至于墓志上写着谁的名字,对他来说一点也不重要了。”(39页)“甚至有时候我外出走在巷子里,经过许多死者的尸体时,竟然觉得他们像垃圾一样。”(157页)面对死亡,恐惧也从人们的内心深处觉醒。“每天都有人因为恐惧死亡而死亡。为什么有些地方会支持基地组织,提供他们藏身的地方?那是因为他们害怕被其他地方的人欺压!而其他地方的人也是出于一样的原因,他们怕被基地组织攻击,所以组成武装团体来保护自己。他们因为害怕被杀,所以也成了杀人武器。”(126页)谣言与猜忌横行,“这些人已经陷入失控,好好跟他们说话也听不懂,宁愿相信谎言和谣言。”(226页)面对无名氏无法阻挡的暴行,“恐惧蔓延着,滋润着人们对他的想象。杀人事件接连发生,绝望的感觉更壮大了他的形象。”(315页)在真正的危险来临之前,恐惧已将人们掠杀殆尽。各种丑恶的嘴脸在灾难中被放大,抢夺、恐吓与欺骗的地产商法拉吉,肆意殴打、侮辱无辜群众后冷静地抢夺财产的政府官员,恶意栽赃、勒索的警方……可是人间毕竟还有默默的温情,路过爆炸现场的人第一时间确认幸存者的安好,对“疯狂”的母亲不离不弃的女儿们,危机中依然冒险助人的教堂执事,照顾遭人嫌弃的拾荒者的街邻……这就是伊拉克的战后百态,这才是这场战争中真正主角的真实生活。
割裂的叙事线索、不断切换的叙述视角,并没有使故事变得繁冗与零碎,没有故弄玄虚的卖弄与长篇大论的吟咏,作者是个讲故事的高手。略煞风景的是“大咖”、“怪咖”、“小嫩咖”、“有的没的”这些译辞的出现,不知作者(或者编辑)预设的是哪一群读者。
今天的现实富得像是一个矿,而小说的内容却穷得只有几颗。——阎连科
作者:钟天意
我想以一句《共产党宣言》的戏仿作为本文的开头:“一个幽灵,一个复仇者的幽灵,在巴格达的废墟上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警察和记者,美军与狂信徒,都联合起来了。”这是我能想到对《弗兰肯斯坦在巴格达》一书最简明直接的阐释。
艾哈迈德·萨达维,伊拉克小说家、诗人、编剧,1973年出生在巴格达,曾做过纪录片导演,著有诗集及3本小说。萨达维的作品多次获奖,2010年,他作为40岁以下最优秀的阿拉伯作家之一,入选“贝鲁特39”(Beirut39)。凭借本书,萨达维成为首位获I.P.A.F.(阿拉伯国际小说奖
(一)
“今天的现实富得像是一个矿,而小说的内容却穷得只有几颗鹅卵石。”阎连科这个略显悲伤的论断道出了今日写作者们最大的困局。尽管现实的确像是一座矿,但最外层的富矿早已在二十世纪之前被开采得所剩无几。新的现实埋藏在这座矿山的更深处,而我们还在试图找到一条通向它们的缝隙。这并不容易,因为越是向下开掘,旧的经验便越是难以胜任。
艾哈迈德·萨达维的写作无意间呼应了这个问题。2003年,美军对巴格达内萨达姆可能藏身的地点进行了猛烈轰炸,无数建筑被炸成废墟,平民死难者更不计其数。2005年,美军接管巴格达。基督教徒伊利希娃老太太独居在巴格达,而死亡就与她比邻而居。死亡发生在人行道上,发生在酒店门口,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艾哈迈德的任务是发现,作为工具而存在的文学,究竟该如何完成对全新的现实的书写。
在巴格达生活,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习惯死亡的存在,把它视为亲密的睦邻。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让死亡科学化、精细化(“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保罗·策兰),逼迫人们(譬如乔治·斯坦纳)一再追问文明与野蛮的边界何存;而恐怖袭击则让非自然死亡如同病菌一样侵入生活,最终让死亡变得日常化。这意味着死亡的悲剧性不仅被消解了,甚至还成为某种苦中作乐的素材。
伊利希娃老太太的邻居,一个孤独的拾荒者哈迪,收集了死于人体炸弹的死难者的碎尸,并把它们拼合在一起。这大概是出于纯粹的无聊,因为哈迪并不是一个富于黑色幽默的艺术家,也并非一个用琉特琴对抗强权的勇敢流浪诗人。他最大的愿望无非是用奇闻轶事在酒馆里抓住听众的心,这是像他这样地位卑微的小人物获得尊重的唯一途径。
一条死于恐怖袭击的冤魂急于找到可以用来栖身的尸体,于是它钻进了哈迪的杰作中,并把它唤醒。于是在这样一片土地上,诞生了一个新时代的弗兰肯斯坦。
(二)
作为小说而言,《弗兰肯斯坦在巴格达》的结构无疑是松散的。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如傀儡般登台又退场,各自的故事迅速地交错,又立刻各奔东西。这使得小说本身,或者说,整个巴格达,也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弗兰肯斯坦,向读者肆无忌惮地展示着将尸块缝合的粗陋针脚。
理解艾哈迈德的缝合术更为重要。在这里,拼贴的形式重要性远大于内容。但这里并没有波普艺术的轻佻。围绕着无名氏,挣扎求存的拾荒者,充满野心的记者,利用超自然顾问追捕无名氏的准将,这群人的行动在阿帕契直升机的阵阵轰鸣声中汇聚成了一支不甚和谐的交响曲。
艾哈迈德笔下的“无名氏”同样取材于随处可见的血肉碎块,同样有着不死之身与一身蛮力,但它已经迥异于他的先祖。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在本书中已经变成了一个借喻。与前者反复强调的人性相比,后者几乎是在以最大限度剥离其人性。无名氏放弃了喋喋不休的追问——“我是谁?”“为什么制造我?”“我该去哪儿?”;在短暂的失落与彷徨之中,他迅速找到了自己需要成为的目标:一个复仇者,复仇天使。
他的确扮作伊利希娃老太太早已死于恐袭的儿子,在她家中陪她坐了好一会儿。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组成无名氏的每一个部件都不想重新获得人类社会的接纳——它们都在以腐烂相威胁,逼无名氏奋不顾身地投身于永无止境的复仇行动。不复仇还能回到哪里呢?在巴格达,尸体甚至没有坟墓。已经不可能回到生前的那个社会中了,因为正是那里让他们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变成碎尸。
被人的碎块拼合而成的弗兰肯斯坦变得比任何一个独立的人都要单纯。为了让这个庞大的躯体能够像人一样行动,这个躯体中只保留了一个理念,那便是向暴力复仇,而复仇同样需要暴力的介入。一个悖论出现在他的复仇之路上:每用暴力消灭一个施暴者,无名氏身上的一块肉便会因为心愿已了而迅速腐坏。这使得他不得不去寻找更多受害者,用他们的肉来维系自己身体的完整。但当受害者也不够用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就只有那些施暴的人。到最后,善恶的边界也在这里被模糊了。
伊恩·麦克尤恩认为,在小说中注入科幻元素,是为了指向现在,而非指向未来;而对于无名氏来说,它也已经深陷死循环,不会再有什么未来了。
(三)
经由不断的再发现与再书写,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已经成为了一种想象科幻的符号。她所创造的那个由血肉碎块拼贴起来的怪物是一个造物,而同时也可以是一个人——如果他的父亲,弗兰肯斯坦博士,愿意接纳他的话。他需要一个类似于洗礼的命名仪式,但最终没有得到。他由此而成为一个游荡在人与造物罅隙之间的幽灵。
在不断的再创作过程中,拼贴永远是一种想象弗兰肯斯坦的最重要的方式,同时也是理解弗兰肯斯坦意象的武器。无论是在电影或是动画作品中,弗兰肯斯坦的标志都是盘亘在脸上的,粗大如蜈蚣的针脚。
要想理解这个怪物的真面目,就不得不理解它是如何被拼合的,并沿着拙劣的缝线将它重新拆开。之所以从这个角度切入,是因为拼贴是一个无论在东西方语境下都能迅速得到理解的概念。比如在中国,每当一名婴儿降生,民间有收集左邻右舍家中的布条为新生儿制作百衲被的传统。与日本的插花不同,在制作百衲被的过程中,拼贴这一行为被反复强调。它的人造属性、非自然属性正是它的力量之源。
一方面,拼贴象征着群体的力量;另一方面,拼贴的非自然也带来了恐惧与不安。在当代,拼贴也可以如徐冰的《凤凰》——“凤凰悬而未决,像一个天问”(《凤凰》,欧阳江河),直指我们的焦虑。它宣告了在新千年,郭沫若式的对凤凰的想象已经破产。
长诗《凤凰》最初的写作直接起源于艺术家徐冰的大型装置艺术品“凤凰”,该作品由12吨工业废材料搭建而成。
徐冰的拼贴术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它用庞大而包容的凤凰之理容纳了数以吨计的电子、建筑垃圾。但从上古活到当代的始终是作为骨架的理念,或者说,除了理念之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一切都不再相同。
这或许可以为我们该如何理解弗兰肯斯坦这一意象提供参考。弗兰肯斯坦的出生注定是一个悲剧。其一,这个庞大的活跳尸诞生于从坟墓中盗掘的尸块,这象征着宗教意味上的不洁:它的诞生本身便象征着以暴力手段破坏神圣的生死界限。这种隐忧早在俄尔普斯的悲剧中便得到书写——试图将爱妻从阴间召回的音乐家,最终死于狂女们的手中。
其二,由无数的尸块拼合这一过程,则象征着其身份上的含混,以及“自我”边界的模糊。如小说中所言:“快去找你的遗体……否则就要大祸临头了”、“……他们彼此呼唤着对方”(p33-p39);身份的混淆与缺失最终导致他与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一样,不得不走上放逐之路。
其三,电气刺激所赋予的灵魂,则暗示了对上帝造人手段的卑劣模仿,而这便直接将弗兰肯斯坦推到了上帝的反面。弗兰肯斯坦的悲剧,与其说来自于被自身造物主的抛弃,不如说是命中注定。
(四)
弗兰肯斯坦的生命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减退。在玛丽·雪莱的小说结尾,造物者和被造者一齐掉入大海,同归于尽;但造物者死了,被造者却爬了出来,仍旧隐姓埋名地生活在我们身边。
《弗兰肯斯坦在巴格达》取了同样相同的结尾。政府抓不到无名氏,最终只得草率地抓住拾荒者哈迪,把所有的罪行都扣在他的头上。在无名氏诞生的那条老街上,该走的人走了,只剩下无名氏和被伊利希娃老太太遗弃的猫。在小说的结尾,旧的演员悉数退场,而无名氏自己仍旧站在巴格达的土地上,等待着下一次开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艾哈迈德·萨达维用自己的家乡作为素材,完美地完成了一次弗兰肯斯坦故事的当代续写。理解了无名氏身上的针脚,也就足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暴力,以及孕育暴力的土壤。让几十个不同的意志坚定地合而为一的,正是对以暴制暴信条的绝对信赖。巴格达之于无名氏,就像大地之于巨人安泰。它完美地回答了开篇之中阎连科的问题——对于现实的富矿,如果找不到足够新的工具,就再回到旧的工具箱里找找。
(注:为便于表达,文中用弗兰肯斯坦这个名字直接指代玛丽·雪莱小说中弗兰肯斯坦博士的造物。)
作者 | 钟天意
编辑 | HeavenDuke
本文为科幻百科独家原创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科幻百科」(微信号: scifiwi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