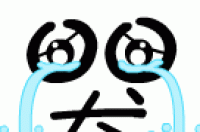他敲打着屏幕,“你怎么不为自己想想。”她看到的一刹那,怔住了,所有人都会以为她的付出是理所当然,即使是没有回报。从未有过人会这样对她说。
呆呆地看着屏幕,看着屏幕渐渐变暗。她还记得他说,能不能换个头像,它太暗了。她回答,从没有人会这样想。我会。他总能这样,总能在不经意间就能轻易打破她好不容易筑起来的防线,然后彻底崩溃。
他问,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笑得出来,你做到了几样?她失笑,我说我全做到了,你会相信吗?你一样都没做到。她再次怔仲,的确,她一样都没做到。她可以吃饭,但食不知味;她睡得着觉,却总会在睡梦中惊醒,然后睁眼直到天亮;她可以笑得出来,可是只是强颜欢笑。他怎可以这样,她所有的伪装在他面前顿时不过变成了一张白纸,竟然还是透明的。也许吧,以后再也不会有人会对她说这些话。只是一瞬间的失落,却是永恒的遗忘。
她对他说,你知道你身上最美好的地方是哪里吗?你说。是你的笑,你的笑太美好,美好的让人无处可藏。所以,我不想你脸上的笑有一天也会消失。他不知道,在他面前,他的笑会让她感到自卑,卑微到骨子里,陷到尘埃里。对于她们这类人来说,微笑已经成为了一种奢侈,他们可以做到的,而她们却只能远远地观望,无法企及。所以,她害怕和他在一起,哪怕只是和他并肩漫步,所以,她在他的面前只会表达开心,她不想会有一点阴天会笼罩在他头上。
那天晚上,他们有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她在这边大喊,你不该有这样阴郁的朋友。你果然承认了,竟然用阴郁。你本该生活在阳光下,不应该有乌云,而我恰恰就是那片乌云。他沉默,然后荧屏闪亮,我不会。我会是那种别人说一句话就会离开的人吗?他的话竟然让她一瞬间想流眼泪,她会有多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久得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多久。她以为以后再也不会有什么事能够让她动容,她早已成为了木偶,僵硬的脸,控制好的步伐,她在按着宿命给她的结局生活。可是那一刻,她突然有了看到阳光的愿望,她想要看看天空,看看白云,看看那翱翔的生命。
她对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认你当我的蓝颜吗?不知道。因为你的一通电话,在我生病住院时的一通电话。其实,人在最落魄最无奈的时候,任何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者一句简单的问候都会让她们认为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在她对她的那些所谓的朋友心灰意冷时,他及时给她送来温暖,就算只是短短的三分钟不到。他让她对别人还有一丝的期翼,至少不会绝望。
后来,她主动更换了头像,那天晚上,他们从晚上九点一直抱着手机聊到了凌晨三点。他在那头说,你有没有发现你不一样了啊。什么不一样啊?各个方面都不一样。她傻傻地笑。奇怪的是,她话并不多,在人前几乎是处于空气的状态,可是和他说话却从不会冷场。他回答,我是话唠啊。的确,像个老妈子一样。他爱看屋塔房上的王世子,她于是一时兴起,叫他计时子。他回答,挺好的。他和她聊了很多,他谈起他喜欢的女孩子,她问他为什么会喜欢那个女孩子,他说因为她爱笑啊。其实,她早就猜到了,他这样阳光的男孩,自然要一个能够和他同样媲美的人和他站在一起。可是郎有情妾无意。他喜欢的女孩并不喜欢他。她说,被你喜欢的人一定很幸福。为什么啊?因为你的喜欢没有负担,是你的自然会到你身边来,得不到的会放手。这样的爱,才是最单纯,最无邪的。
她对他说起她喜欢的人,这是她长到十八岁以来的第一份感情。她很幸运,她没他那么命苦。她喜欢的人同时也喜欢她。他说,既然彼此都有好感,为什么不试试?她苦笑,既然知道没有结果,何苦再继续追求那不可能的存在。她只是害怕,她不敢想以后真的深了,再失去会是怎样的痛,她的心已经禁不起再受伤了,所以,她宁愿选择逃避,选择自私地保护自己。
他是她的高中同学,高中对于她来说是不可触碰的痛,可是她却记住了他,记住了那个戴着眼镜,稍稍方方的脸,总是嘴角上扬一个完美弧度的他。他应该是她黑暗生命中的一道光吧,虽然很微弱,虽然会很短,很快就要消失,但是,他却让她感到久违的温暖。她想起安妮的一句话,总是想要一点温暖,哪怕是一点点自以为是的纪念。现在的安妮,已经改名为庆山,她现在已经开始学会拥抱温暖,而现在的她至少也不会再走上极端了。她的改变,理所当然。
他喜欢刘诗诗,最爱水蓝,想去西藏,喜欢抬头看天,最想靠近草原,那个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他很容易满足,有时候却又像个吃不到糖的小孩子,喜欢和母亲聊天,会很有女生缘,很多女生没办法做到的事他都能够做到。
她对他没有太多的希望,只是,真诚地祝愿,以后不论他的脸上的表情会掺杂着什么样的因素,只要他能够嘴角始终保持上扬一个弧度,太多的话,只需一个眼神,她自会明了。
他是她的蓝颜,是她一生的知己,即使一切只是她的一厢情愿,即使他们以后会形同陌路。他,是永远的,计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