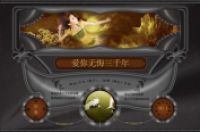有人说,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信仰,好象有时有,有时不但没有信仰,连原则都没有。
我漫无目标地漂流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边缘,始终找不到通向城市中心的路标。
周围的人,忙碌的人总是来去匆匆,不知在滚滚红尘里寻寻觅觅什么?而那些悠闲的人却365天如一日似的坐在茶楼里喝着茶,好象时间对于他们而言似乎就像手中握着的钞票一样,永远用之不尽,喝之不结。
一年以前,我的生活简单而简单,过得一成不变,在我们那条不大不小的街上,白天拥着一群哥们走进茶楼。晚上随着动感的音乐节奏在酒吧里喝着一杯又一杯的啤酒,日子就那样在我的手中逝去了许多-----于是有一天,我爸对我说:你是不是应该结婚了?不要整天吊儿朗当像流氓一样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回想起来,每到那样的时刻,我都应该去教堂或佛面前忏悔,然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很可惜,我却没有那样。
如果就那样过下去,生活也许也一样依然混乱不堪,只是不至于死。可是,我觉得我没有生活,至于没有什么样的生活,为什么没有生活,我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反正觉得自己没有生活,灵魂空虚而麻木。
就这样,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了蓉城,行囊里只有年轻的梦想和飞扬的激情。
漂流到城市的边缘,熙熙攘攘的红尘里,我一无所有。前途渺茫,没有未来。
张楚曾经说过: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我也会寂寞,像喧嚣的烟花。黑夜是适合我湮灭和沉寂的怀抱。
疲惫不堪的生活让我无法热爱这座城市,破碎的心每夜都在回租住屋的路上被寒风撕裂了,痛意泛出,新的,旧的,近的,远的。
我不想再自欺欺人。
唯一支撑我努力不至的是,那遥远的家园那群期盼的目光------
其实我以前想象的生活不是这样的。我曾经想我应该住在美丽的湖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湖岸的山上搭一间竹棚,这样我每天推开窗,温暖的阳光洒满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可以看到美丽的湖光山色。
放上一曲那些历经沧桑的男人唱的忧伤而深沉的情歌,匆匆吃毕早点,背上简单的背包,骑上一辆不会太旧的阳光型自行车。做的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广告公司的创意设计或自由摄影什么的。
晚上下班之后,房间里飘出的音乐是凯丽金的萨克斯独奏曲《回家》亦或理查德的《海边的阿狄丽丝》钢琴曲,斟上一杯如血液般的葡萄美酒。用ZIPPO火机轻轻点燃那种大小仲马喜欢的女人的烟。
那种烟身洁白修长,外壳上写着两行斜体字“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当时针指向午夜时,我又换上那套有白色袖边已洗得泛白的牛仔裤,戴上一款时尚的牛仔帽,背着我那把已破旧,但视若生命的木吉他,骑着我的上海宇宙去演译另一种身份——歌手。穿行在城市的某一隅,在那些眼波流转,涂着眼睫膏和指甲油的幽灵间不停地穿梭流连。
带着这份纯真的想象中的生活,我不停地奔波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我希望有一天这一切不仅仅只是我想象中的生活------
记得有个名人曾经说过:击败失败的惟一办法,是去证明你比失败时的自己更优秀。
只是太多的时候,这个世界不符合我的梦想,现实与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
午夜寒风中的孤独,白日忙忙碌碌的疲惫不堪,以及那刻骨铭心的恨铁不成钢的心疼,都在刺痛着我不停地向前奔去,酸楚的眼泪只能暗自流向心中------
因此,二十一世纪年轻人必读的70本书,我最多只看过几本,必看的100部电影我最多只看过1|10,必听的100张CD我一张都没有看过------
也许,这就是漂人的生活。
没有人知道漂人流离失所的酸楚。
没有人理解漂人那种踏上不归路,只能眼含热泪回望故园的感觉。
只有一种人才最透彻的明白——那种人就是漂人自己。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有一天让他们的母亲为他们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