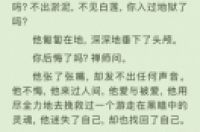以前我住过的那个村子里,有一个老太婆。不知道她的全名叫什么,只是听村里人叫她“春”。她大概有60多岁,无儿无女,是讨饭过来后定居在村里的,好象是从河南那边过来的吧。村里人说她有些傻,所以常有人去捉弄她,甚至是一些小孩。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在该村借住过一段时间,因每天上班早出晚归的,我呆在村里的时间也不多,因此对村里大部分人不是很熟,也包括太婆春。记忆中也见过她两次,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冬日周末的下午,她穿着一件破旧的土灰色肥胖的旧棉袄,外面罩着同样破旧不堪的外衣,由于过于破旧,衣服只能用一根布条系着,整个显得极臃肿、笨拙。她右手挎一个破竹篮,左手拄着一根木棍,从村中一条小巷中蹒跚地走来。“春,去做某事?”“过来坐坐吧。”刚走到村前一排房子前,有人在叫她,那里有几个村里的女人在晒太阳。她马上转过身,木然的脸上立刻堆满了讪笑,缓缓地走过来站在几个女人前面。“春,你这是要做某事?”一个女人笑着递过去一个凳子。“出去……转转……捡点野菜……没什么……吃……吃的……”她嗫嚅着。几个女人互相看了一下,都笑了起来。“坐下吧,跟你说个事。”“坐……好……好……”她笑着,慢慢地坐了下来。“帮我扎草靶吧。”一个女人笑眯眯地看着她。那时农村多烧土灶,需要将秸杆扎成团以并于烧火做饭。
“嘿……嘿……”春搓着手,只是一味地笑着。“扎不扎,给你钱。”那女人看着她,嘴角向上挑了挑。“嘿……嘿……扎草……靶……嘿……”她仍含糊不清的笑着,但分明眼中流露出希冀。“你捡一天能捡些啥,再犹豫就不要你扎了。”女人的嘴撇了一下。“嘿嘿………在…哪里扎……”她缓缓地站起身来,傻傻地笑着。“喏,那边一堆草,把它全扎完。”女人笑着指点一个很大的草堆。“扎……扎……嘿…嘿…”春笑着,缓慢地拿起凳子蹒跚地向那草堆走去。女人们又说笑着唠起了家常。
冬日的暖阳静静地照着,是如此的煦暖,此刻春的脸上是如此平静与坦然,竟也看不到她的笑。她只是专注地忙活着,干枯的稻草在她的僵硬的指节间弯折着,发也悉悉簌簌的声音。稻草扬起的灰尘弥漫着,不时听到她嘶哑的咳嗽。因为时间关系,那天我没能逗留太久就离开了村子。后来听说春终于还是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两元钱,那天她忙得很晚,而且好像身体不适,在家睡了好几天。
隆冬终于逼近,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我依然是早出晚归的上下班,只是期间竟很难再看到她了。村子里也很难得看到有在外串门闲聊的人了,唯听到冷风刮过光秃的树梢所发出尖锐的哨音和几声断续的犬吠。偶然地在这样的一个上午,听村里人说春死了,我有些诧异。“死在水里了,塘已干了,应该淹不死人的”“是在水里冻死的,这么冷的天,池塘坡太堵,爬不上去……”,“听说是夜里偷别人的稻草,可能怕被人发现,就绕道走,后来失向了,塘里还有一捆草……”村里人笑着在平静地侃着。那池塘我很熟悉,距村子很远,春在寒夜里为何要走那么远到哪里去呢?我不得其解。只是有次在村里吃饭,酒过三巡后,村民免不了没完没了的唠嗑,偶尔提起了春。一关系很好的村民呷了口酒,压低着声音说:“什么走失了方向落水,是被人赶到水里的……”“什么……”我不由一愣。“偷别人草呗。”“事都过了,喝酒,喝酒,别说了。”另一村民端起了酒杯。我想再问些什么在,可欲言又止。
春的葬礼很仓促,也很平静,就如同她蹒跚的步履。那天来了一辆黑色的小车,车上下来几个人,听说是春的什么亲戚,从河南过来的。他们从车上搬下两个冲天炮,点燃了就噼里叭啦的放起来了。春住过的那间低矮的房屋已被清理一空,屋子只有一间房,类似于农村一般猪舍的结构,屋内是黑糊糊的,遍布稻草、灰烬及一些杂碎的垃圾。屋前堆放着一些破衣乱絮,一张老朽的破桌子歪倒在一边,这些可能是春的全部家当。她的遗体摊放在屋前的空地上,下面垫着一张破旧的床单。稀疏的围着一圈人,大多是小孩,几个人在闲聊着,那些小孩不停的在大人身后追逐着捉着迷藏。没有哭灵的,春静静地躺在那里,面孔发乌,有些扭曲,可以想像其在死神逼近时是如何努力地想爬上那道土坡……
简单的料理后,下午春的遗体被送上了殡葬车,鞭炮又响起来了,随着殡葬车渐渐远去,稀疏的人群迅速散去。空气中唯飘浮着一股火药的气味。
这似乎是一个过于平静而单调的终结。但对于春而言又何尝不是其漫长一生中最排场和风光的时刻呢。
以后的日子村民们仍是边慵懒地打着哈欠,边悠闲地嗑着东家长,西家短,但没有人再提起春。也许她本不应属于这个世界,而此刻她是否正在那边笑着呢。
一阵冷风吹过,我不禁瑟索了一下,我知道,这又是一个冬季。
2011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