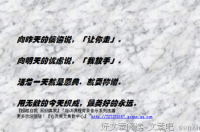2009年5月,我在繁忙的高中生活的余暇里曾写过这个题目的杂文,心情很重很重,笔调很沉很沉。面对那些无法逃避的事情,我很努力也很虚伪的为自己描绘了一个梦,只是那些思念总是如那每年如期而至的敏桂的花期,每个孤寂难耐的夜,它随风潜入,让我的痛变得更深刻,深刻到足以让我麻木…一直以为,二十岁的我可以摆脱如斯的困扰,只到这个五月,我才深深的明白,有些事与年龄是全然没有关系的。
写到这里,我又不得不说到一些关于我生活的事,而我对生活最初的定义是从我的十六开始,十六岁,我玩自责,因为自己始终为我和安然犯下的错忏悔着,才发现原来自己真的无法象个孩子那样毫不在乎;十七岁,我玩寂寞,从一份感情的寂寞开始,一直蔓延到我整个世界的寂寞,原来,我本身就是个寂寞的个体;十八岁,我玩回忆,他们说,一个人开始回忆一些事情时,说明他长大了,而当他的生活里只剩下回忆时,说明他开始老了,我的十八岁与八十岁的区别只有单纯的个位与十位的倒置;十九岁,我玩茫然,象个瞎子一样走着路,没有白天与黑夜,不断的走错路,做错事,说错话,牵错手,甚至上错床…我想拼命的遗忘时间,却总是被时间先遗忘了;如果人活着真的有种东西叫宿命,那么我的二十岁可能是个意外,但这种意外绝对不是传说中的奇迹。面对自己描模了三年的幸福,我却自卑得不敢去挽它的手!
如果说男人的一生里,三十而立,四十而获,那么二十岁的我们有的是惑,这种惑就是一种茫然,无为的茫然!因为这种惑,我们连做梦都开始现实,甚至不敢再说那些信誓旦旦的誓言与承诺…纯真、快乐、幸福…那些童年里推之不去的东西竟然成为了二十岁的奢侈品,这就是所谓的长大!
异域的桂和故乡的桂从嗅觉上而言没有什么差异,同样有着淡淡的幽香,可有些东西是经不起比较的,比了就会察觉到太多的不完美,从而蒂生出对一些逝事的怀恋,就如同有些话是真的不能说出来的,说了就会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