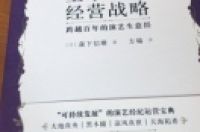我还是赞同刘心武先生对妙玉判词的理解,肮脏应读kangzang。
(寻典—文天祥之《得儿女消息》:“肮脏(kangzang)到头方是汉,娉婷更欲向何人!”。肮脏在此的诠释是坚强不屈的,执拗的,坚定的!)
雪芹先生的文章,纵观其文字功夫,可以说是“简炼精纯,力透纸背”,尤其是其残本中的文字,如其所言“呕心沥血”,而我们所寻常理解的肮脏义为污垢,不堪入目的,它介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属于通俗词汇,既不细致,也没有更发人深醒的含义。个人认为雪芹先生是不屑用此词汇的!
可以说雪芹先生已掌握的中华语言的精髓,使他常炼词,而规避陈词。现成的词,耳熟能详、缺乏想象。它们一般修炼的不到火候,既无法作精致的表达,也不能予人想象的空间。一言以譬之,不够真切!
我曾在厨师行当中听过这一层词叫“冧”,义为烂而不碎,对烹饪的准入是食物停顿在烂但不至于碎的地步,它对火候专注的切乎吝啬的苛求正在于此,异曲同工,有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中对女子的刻画:“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也是对真准要求甚甚。
我们讲究炼词,对词本身表情达意进行千锤百炼,可以说是一词千金重!这并不殚于严谨的科学态度,而是对真美的苛求,一词可以深刺骨髓,一词却如隔靴搔痒,一词可以醍醐灌顶,一词却混淆明智一词可以浮想联翩,一词却如芒刺在背……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文字的魅力尽现于此,而不止于此,写的人殚尽力竭,读的人更应斟酌反复,怎能草率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