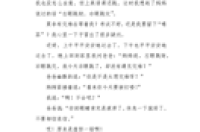土地流转
三河岔地
前公河和后公河分别从刘公河岔出,就在村子的西边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地带,村里人就习惯称它为河岔地。
千万别小看这一片河岔地,它可是翻着筋斗过来的!
古时候,浑浊的黄河水曾在这里滚滚东流,湍急中也曾掀起层层大浪;它施虐时也曾冲过堤岸,轰隆着漫上田野,漫上村庄,所过之处,冲垮了房屋,冲毁了农田;卷走了老和孩子,以及他们的牛羊。岸边的老百姓也不知多少次被它逼得无家可归,抛妻弃子,背井离乡。那时他们叫黄河不叫黄河,叫害河!大明朝弘治六年,朝廷委派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刘大夏、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到这里治理黄河,在黄陵岗决口堵塞成功后,于当地建庙立碑。“黄陵岗塞河功完碑”至今仍存,在兰考县城东北四十五公里处的宋庄村。 大葛庄就在“功完碑”南边的两公里处——撇开这些不说,从大葛庄周围横着竖着的几道大堤,和一些河流的走向看,似乎也能看出当年滔滔的黄河水滚滚东流的影子。
河岔地是华夏母亲河养育、哺育过的土地!同时它也见证了沿岸老百姓的苦难历史!
解放后大集体时,河岔地长期被河水侵润,土地盐碱化,不长庄稼,夏天只长两种野草,丫儿嘴和芦草拐,冬天则是白茫茫一片。因为是一片不毛之地,河岔地便成了没娘的孩子。它北边的后公河上有一座桥,离桥不远就是小葛庄。大葛庄不说是他们的,小葛庄也不说归他们所有。时间一长,河岔地成了“公地,”所有权就模糊不清了。
进入八十年代, 由“大集体”进入到“生产责任制,”施肥也步入到多种化肥施用的年代。化肥的大量使用,原来的不毛之地就变成了良田。因为土壤中含有盐分,它甚至比原来的良田还要肥沃。河岔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大葛庄和小葛庄争夺所有权的矛盾也就出现了。开始,小葛庄的人牵着牲口扛着农具,越过后公河到河岔地来耕种。那时葛洪斌的父亲老支书葛振彪还健在,就去和他们交涉。可小葛庄人并不把他的话当回事,而且还举出一万个理由一千个证据证明河岔地的所有权是归他们所有。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葛振彪就在村子里大声疾呼:各家各户老少爷们听知——凡是有种的、不蹲着尿的男人现在就抄起家伙,走出家门,和我把入侵者赶跑!村里的男人谁愿意承认自己是蹲着尿的?大家有举着铁锹的,有扛着抓钩的,没有铁锹和抓钩的就抄起扁担,跟着葛振彪嗷嗷叫着冲向河岔地!小葛庄人看来者不善,慌乱中牵着牲口,扛起农具就走。当走过后公河,他们才意识到:还没有见到人家一跺脚,就像狗一样夹起尾巴逃跑,实在是太丢脸了! 就丢下牲口,决定反戈一击,杀一个回马枪,就把扛着的农具举在手中,向大葛庄的人群冲去。
老支书的胳膊就是在那次混战中,被小葛庄的人打断的,为此还坐了一年牢。
为确定河岔地的归属权,县乡两级成立了联合调查组,通过和双方反复协商,最后采用了折中的办法,就是把河岔地从中间分开,南边归大葛庄,北边归小葛庄。后来又觉得不妥,为避免以后双方再起争端,就把大葛庄在后公河北岸的二百多亩土地划归了小葛庄,这样河岔地自然就全部归大葛庄所有了。
现在的河岔地被分成了三大部分,从南到北以次归一组、二组、三组所有,再细分,就是村民各家各户大小不等的责任田了。
在大葛庄和小葛庄争夺河岔地的事件中,由于老支书鼓动村民打架斗殴,并在械斗中断了一条胳膊,后又被依法判了一年徒刑。可他这个判刑和小偷小摸的判刑不一样,他是为全体村民争利益才坐牢的。临行那天,全体村民出动,眼巴巴地看着他被带上警车,相跟着送出村外,很多人还掉了眼泪。三十多年来,村里只要一走进河岔地,看到那绿油油的庄稼,就会想起老支书葛振彪。为了报答,二零一二年选举,村民就把他儿子葛洪伟推向了支书的位子。
支书葛洪伟上任十多年来,政绩平平,并没有干成一件大事,这次就要干成一件大事了,那就是他的“千亩桃园。”今年秋末,或明年春天,河岔地将被全部栽上桃树苗,桃树挂果快,很快就会开花结果。县政府搞美丽乡村建设,先疏通了河道,河坡规划得坡度一致,整齐划一,棱角分明,然后沿河又修了水泥路,路边栽上了松柏和其他绿化树。有河、有水、有路、有绿化带,那格调也就不同了,和以前先比,那时候的河岸杂草丛生,七弯八扭,像一个农村肮脏的庄稼汉,现在就像城市里花枝招展的小姑娘了。
这本来就够美了,可二年之后,在葛支书的想象中,这里摇身一变,成了“千亩”桃花林,并且夹岸数百步,中有杂树,芳草鲜美,落英嫔纷,路人甚异之——难道这是要走进桃花源吗?这里成了人间仙境,哪里还是“够美”两个字能够形容得了的?
所以,葛支书认为,别说果实,单说夹岸桃花,就足以证明他的项目“千亩桃园”是十分英明十分正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