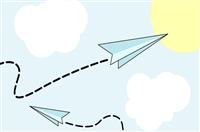没有星星,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北京。夜晚,天通苑这座巫山隔绝了城市与郊区。其上浮动着冥冥鬼火,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积越多,越来越明,零辰时分又越来越淡。一大片玉米地挤在天通苑的公路旁。借着冥冥鬼火,玉米地深处,玉米梗儿呈扇形斜倒,滴滴热血还在顺着杆儿流向它的载体。一个男人张开双臂仰卧在地上,他的肥胖的脸转向一侧,他只能用暗红色的血来渲染自己的与众不同,因为没有星月来制造闪烁,光彩夺目是不可能了。玉米地的另一侧就是一连串的低矮平房,其中就是民办学校。身在这所学校操场上,抬头看着天通苑,仿佛就在其脚下,但深知谁也不属于那。操场上寸草不生,浮土到了夜晚被寝室投来的灯光激得不甘沉默。灯光却是死白的,周围万籁具寂。
可总得听到点声音吧,总得证明存在的意义吧。是有人在思索着这类问题,躲在死白的灯光下。这是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只有一张床,一张课桌,一把椅子。而他却蜷在角落里,手里拿着一根烟。这是新点燃的烟,陆易先生的眼睛凝视着烟发红的一端。细细的烟雾向上飘去,妖娆地跳着舞步。陆易先生的眼神紧随着,生怕错过哪个细节。烟雾消失了,他就使劲抽一口,眼睛死命盯着火红的烟丝,仿佛是他在燃烧、沸腾。一看就知道他刚学会抽烟,看他拿烟的姿势,只是专注品味,而忽略了毒性对大脑的刺激。
新近毕业的大学生找到这个地方来过活,难免有人要注意,指指点点。路易先生是这样应付这些人的:白天,他要上五节课。除了课上,像个蹩脚的演员在讲台上手舞足蹈,其于时间总是颓废见人,一个忏悔者自居,一个要干枯的人--才25岁。夜晚,他就像死人一样体会周围的一切。他的眼神中总闪着火光,淡淡的黄色火焰,却不被查觉。
陆易先生还有一个任务。早上,他得比其他老师提前起床,去接学生。他是押车人。学生班车跑到天通苑三区和二区之间的马路时,他就可以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他的眼睛就睁不开了。也不知是讨厌还是害怕,反正这不是他最喜欢的地方。陆易先生最着迷的地方是半截塔村。路过那时,他总是要看看那座半截塔。其实塔的一角也没有,只是一个底座,其上有两块岩石。陆易先生喜欢在放学送学生的时候看到它。那时,正值太阳快落下了。他的眼神中再次充满火焰。但他从没有下车或找时间来这。
他一如既往地颓唐,别人开始忘记他的外壳,穿过他。他也认了,拿几百元在这过活。他还想看看落日时的半截塔,就盼着放学。车按时走着规定的路线,沿途一个一个放下到家的学生。陆易先生不知不觉闭上了眼睛,车上的学生依然说笑着,他也没反应。他看到了半截塔,阳光在西面照着岩石,岩石逾发暗淡。而他却全身通红,感觉就像一张纸烧成火粉一样;他的眼睛也在冒火,黄黄的火苗射出来,灵魂也像是跟着被拽走了。随后就是冷到心要冻结了。
“老师,我要下车了,开门!”
陆易先生睁开了他那红肿的眼睛,先看了看车外,早已过了半截塔村,然后看了看学生的脸,那样暗淡无光。
“下车小心点,看点车。”这是他常要说出来的,不管有心没心。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他又回到本位死人般体会狭小的世界。现在他抽烟更急速,丝毫没有烟民的风度,就好像要用那红火的烟头来取暖似的。陆易先生的确有点不同以往。他的黑黑瘦瘦的脸也开始泛着惨白,他的眼睛也没有尖锐的凝视,就像,就像是被吸血过一样。他不停地抖动身体,哼哼叽叽,要躲避什么,就在眼前的什么东西,他却不敢动。还是睡去的好。陆易先生就这一点好,躺床上就能睡着,而从不做梦。他真地不知道吗?他不知道在他睡觉时做过的一切不堪入目的事情吗?
一觉醒来,他就感觉不好,什么东西都在扭曲,而且越来越白,又达到刺眼的程度。渐渐地,一切都成了黄黄的色调,又恢复了正常。来到办公室里,陆易先生和其他老师问了好,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参与他们的话题。
“你看看这操场,啊,这些土又都刮起来了,那些学生还在里边玩,脏不脏!”这位女老师用手指点点窗户,皱起眉头不说,还撇嘴。
陆易先生望着那些操场上被尘土裹着的学生,不自觉地
说:“是应该治治了。”谁也不知道他说是应该治治谁。而他仍然望着忽隐忽现的那些学生在尘土中玩,心里却想说出另一番话:你们这些吸血鬼,我终于发现是谁在我的生活中搞恶作剧,你们破坏我的身体,又破坏我的工作。我现在不声张,我等,我等。你们想群起而攻之,没那么容易!我在岩石那已经看透了你们的罪恶,你们吸我的血,不知不觉地被你们玩弄,我在岩石那被地狱火炼时与面对你们是一样的歇斯底里。不行,我要躲,我要走,别过来!
上课铃声响了,每位老师各就各位了。只有陆易先生还不动地方。最后他拖着步子来到了学前小班的教室门口,战战兢兢地窥视屋里。所有的同学都在大呼小叫,好不快乐。他们手里拿着一年级上数学课才用的空心小棒。有红的,有蓝的,有白的。这是陆易先生最不愿见到的场面。他的眼睛近乎要爆炸的火球,怒视着学生们,走近教室。他想用狂吼来压倒他眼中的“吸血鬼”。但他发现他再也办不到了,他太脆弱了,在讲台上无力地寻找依靠的地方。他要跪下去了,是在重压之下,不情愿之下。他的眼睛被粘液涂裹着,趁着还没有干,用劲抬起头看着下面的……
该怎么说呢?这群学生,不,这群吸血鬼静静地浮在自己的座位,黑黑的眼睛里透出刺眼的白光,转而又像太阳的余辉。才五岁大的身材,却凝聚着压迫所有物质的力量。他们手里都拿着空心小棒,死命地捏着,而且从下端口滴出红红的粘稠液体。液体在管口越积越大,滴下来却没有落下去,而是上升,慢慢地众多液滴汇集到教室中央,越积越大。这时,陆易先生绝望地叫喊着,不过声音也敌不过那些吸血鬼在空中吸吮大血球的声音。他在劫难逃。现在他轻得足可飘起来,在空中张牙舞爪,还在嘶声裂肺地吼。吸血鬼们也滿足了,开始啼叫,像婴儿,像女童,像幼狼,像……就像人们心里的鬼,不用任何配音,只要时机一到,它们就做声,一开始还小声,逐渐就忘乎所以。
什么时候最残忍?就是看着别人慢慢地、一点一滴地杀死你,何况还是你眼中的乌合之众。陆易先生挺不住了,他快干枯了,已经没力气了。他想求饶,但已张不开嘴,就在那擅动他的嘴唇,手无力地向前举起,指尖指向更远处。好像他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一个男孩,在学陆易先生的样子,做垂死挣扎,其他吸血鬼到是在旁边装作害怕的样子,惟妙惟肖,好不生气。
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人们总是有怪异的想法,还得找时机去实现它,不论怎样,固执地坚持自己是对的。眼见为实,这是道理!对吗?人们有很多种欲望,有些欲望促使人们成为地狱使者,而这些人往往伪装:把自己扮成受害者的样子,接受任何怜惜、怜悯。他们到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大施法术,兴风作浪,在哪个剧本里都扮演占有优势却不会使用的家伙,却用一些卑鄙的手段毁灭人性。
下课铃声响了。教室门被其他老师踹开,强烈的阳光从门外射到屋里,正好射在那个刚才还学人样的吸血鬼脸上。房子里的所有生物都在痛苦着,新加入的老师愣住在那里,有的老师都喘不过气来,有的老师跑走了,随后才有老师歇斯底里起来。阳光就这样照着那个东西,是什么?走近点,再走近点。那就是一个孩子,有一张稚气的脸蛋,却没有了眼睛,没有了舌头,胸膛被扒开,哪都是血,器官都被抛在洒水盆里,混乱一片。陆易先生跪在一旁,双手曲起来,还“热泪泉涌”地叨叨着:“我得救了,我得救了!”他用那血糊的手到处触摸,在地板上胡乱蹭,拽住旁边的学生不放,眼神中还不时放出黄黄的火焰。
报纸上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