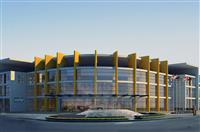
二
知青宿舍的门窗透过很弱的灯光。每一个房间里的知青。都各自整理着日常的生活用品。张文秋则躺在炕上的被褥垛上。翻阅着从家里带来的一本小说。王继昌则摆弄着收音机。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联播。还不时的转动着方向。阎明凯。李小锁翻腾着衣箱里的东西。土炉子上做着没烧开的一铁壶水。热气从壶嘴处冒出。快开的水发出嘶嘶的响声。
隔壁知青的女生宿舍。冯继华。郭玉英。孙桂兰。在安抚着泪眼汪汪的王小丽。其实四个女孩子的内心。都有想家的那种离别的痛苦和失落感。王小丽此时才感悟到守在父母身边的那种快乐和温暖。感情有些脆弱……夜晚整个知青宿舍显得沉静。郁闷。
村南面的京包铁路线上。在火车巨大的牵引下。拖着长长的煤罐车呼隆呼隆的驶过。一声长长的汽鸣声。打破了何家屯黑夜的寂静。知青宿舍的门窗开始有些震动做响。王继昌关掉收音机。听着远处的火车鸣笛声和看书的张文秋说“哎。你听。这是我老爸的车。……”显然他在想家。王继昌的父亲是铁路运输司机。专跑张家口到大同这条铁路线。何家屯紧靠在铁路线的北面。张文秋合上书本放在一边坐起身说“继昌。是不是想家了。不会吧……”
“没错的。就是老爸的车。我们铁路的职工家属都知道。车不进站是不鸣笛的。这是老爸有意识的在鸣笛……”
张文秋笑了笑说“看来。你们铁路职工家属。有坐车的优越。这会。你回家做车可就方便了。省得再去花车钱……”
“肯定是不会花钱的。哥几个。到时咱们回家坐车。跟着我上我老爸的车头。啥事没有。”王继昌向几个知青承诺着。隔壁女知青的房间传来隐隐约约的哭声。在地上正收拾衣箱的阎明凯。李小锁停下手里的活。疑惑的问“谁在哭?……”几个人细细的听了听。李小锁很确定的说“呀。是隔壁的。…过去看看……”张文秋。王继昌先后从炕上跳到地上。随严明凯李小锁来到隔壁的女知青的房间。四个女孩看着推门进来的男知青。脸上还挂着泪水。张文秋看着眼前几个哭的向泪人的女知青问“这是怎麽了……哭啥?……”冯继华擦了一把泪水。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王小丽还在抽泣着。张文秋明白了笑着说“想家了?……哎呀。…我说王小丽。咱们今天上午才认识的吧。说心理话。今天上午。全市几万人夹道欢送咱们这些知青。在车上。我心理都有点酸楚楚的滋味。眼泪总在眼圈里打转。看到自己的父母在车下挥着手时。我都差点掉泪。不是我强忍着。怕我妈看见伤心。也许。还不如你现在呢。可看到你当时的哪个样子。又跳又笑的。我感觉我还不如你们女孩子坚强呢。”王小丽忍不住扑哧的一声笑了。张文秋看了看摆在炕沿边上的饭盒。里面是从食堂打来的小米稀粥。接着说“小丽,现在是怎麽了。嗷。原来都是装的。你们姐几个可真行。能装到现在。还是比我们强……好了。别难过了。该吃饭吃饭。啥事明天睡醒了就全忘了……就这样吧。我们过去了。”张文秋与几个知青回到自己的房间。王继昌开玩笑的说“这个叫王小丽的。还真漂亮。哭都那麽好看…不错…”张文秋看着王继昌自做多情的那种神态说“你以为她是谁?西施。吗?”
“管她是谁。文秋。咱们过去还真是去对了。那几个姐妹。在咱们几个人中间。也许。有选择的。还能看上咱们谁了……”李小锁插嘴说“真是这样。那到挺好。下乡第一天就挂上一个。别说。还真有点不白来的意思。”半躺在被褥上的张文秋还在翻阅着他那本扬沫的《青春之歌》若无其事的说“别自做多情了。当心那不是蜜罐子。可是盐坛子。”王继昌把座在火上的水壶拿到一边。用炉火的通条在炉内扎了扎。把炉旁的黑煤球放进炉内。接着刚才的话说“哪个王小丽。早上上车的时候。看她那活泼样。又是招手。又是跳的。还以为自己是西哈努克亲王呢……你别说。王小丽还真的没掉一滴眼泪。还挺招人喜欢的……”张文秋接着说“我也是觉得这个王小丽挺耐人寻味的。当时我也怕让我妈看见。真是强忍着。这个小丽。在那种场合。表现的也太坚强了。事也真怪。没人了。到哭的这麽伤心。让人不可理解”张文秋话里有话补充着……
知青宿舍的院子里。没有月光的时节。更显得黑漆漆一片。阴冷的夜空看不到繁星点点。村东边的驻军部队的营房传来了熄灯号。何家屯的整个街道小巷进入梦幻般的寂静……村子里传来狗的叫声和大牲畜的嘶叫声。声音紧接着一阵阵的叫着。街面上开始有人跑动。逐渐跑动声音越来越大。嘈杂的人群有人呼喊着“起火了……赶快救火呀……”一时间水桶的碰撞声。人们的呼喊声混成一片。小孩子也吓的哭叫着。人们都往起火的六队方向奔跑着。知青宿舍张文秋立即起身对身边的几个知青伙伴说“快起。快起……着火了……快点……”几个人这才慌里慌张的找自己的衣裳鞋子。抄起各自的脸盆冲了出去。所有的知青呼啦一片的跟着人群跑向起火的方向。此时。驻扎在郭垒庄某部的营房里。响起了紧急集合号……
大火已照红何家屯的半边天。大队的大喇叭这才开始叫人。突如其来的火灾着实让每一个知青感到恐慌。六队门口的机井水泵。哗哗不停的抽着水。人们再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争先恐后的奔跑。朝起火的地方实施扑救。起火地。是堪塌多年的破庙。几天前。拆庙时所有的门窗木料柃条都堆放在一起的起火地。因为紧靠六队的几间库房。周边又是一垛垛的玉米麦秸。火势很大。远远的让人感到烤的脸上发烫。人们站在房上地上一桶桶一盆盆的水泼向火原。部队的战士卡车也随即赶到。混乱的场面火势开始减弱。人们还在不停的将水浇在余火处。未燃的玉米高粱秸被人们一捆捆抱到远离库房的空地上。治保会的干部。从生产队接出很长的照明灯线。开始清理余火。防止死灰复燃。人们开始清理燃烧的废弃物。张文秋站在石台子的高处。接过递上来的水盆。一盆盆的泼向玉米麦秸垛上。一个围着红色长围巾的女孩。双手把水盆举的很高。冰凉的水流进她的袖筒里。她的身边还有另一个女孩也在传递着送来的每一盆水。围着红色长围巾的女孩对张文秋说“知青。接水。……”张文秋接过水盆。看了一下眼前的女孩。转身将水泼向玉米麦秸垛上。这才将水盆送还给眼前只有十八九岁的女孩。女孩接过水盆。无意离开。文静端庄的脸上显现着女孩的聪明善良。眼睛充满着一种期盼……火势熄灭。生产队的所有库房一片狼极。玉米籽种遍地都是“……散了。散了……”人们陆续散去。知青每个人的裤脚都是湿漉漉的。王继昌。李小锁。阎明凯。张文秋相跟着离开。那个女孩跟随在他们的身后。张文秋下意识的回头看看。那个围着红色长围巾的女孩。很腼腆的在看着他。女孩已停在自家的巷口转弯处。目送着离去的陌生知青。这才进了自家的院子……
知青们回到宿舍都在换衣服。把湿透结冰的衣裤架在炉火前烤着。王继昌上衣口袋的一盒官厅烟也湿透了。只好把烟放在炉火旁。披着被子再炕上盘座着。手里把湿了的烟丝重新用报纸卷了一支。点燃。品着烟草的香味……
何家屯逐渐恢复了平静。此时已是午夜时分。各家都在谈论着一个话题。“这把火烧的。六队明年开春地里下种就是个问题。”郝万田家。爷几个都在收拾整理着救火用的水桶扁担和湿漉漉的衣裳。老大郝学有把早已湿透的鞋脱在灶台前说“……堪塌了这麽多年的破庙。就让它在吧。非要那些不能用的破木头烂椽子干啥。不闹出点事来。就不歇心似的。老人们早就说过。再破的庙。时间长了都有灵气。前几年村北的那棵老槐树……爹…那棵老槐树也有近两百年了吧。说锯就锯了。结果锯树的锯子上粘的满满的黑血。锯下的树洞里。藏着都是枣大的黑蛛蛛往外爬。能不吓人吗。还好。支书也害怕了。六队门前那棵也有两百年的槐树。再没人敢锯了。算是保留了下来……上辈人就说过。六队门前的这棵是龙头。村北的那棵是凤尾。是不可轻易动的。看看这几年。村里出的这些事。学校的李万长老师。多好的一个人。担水时在井台上叫辘轳把头打了。现在傻里吧唧的成天在街上。蹲着自己瞎唠叨。二队李庆元家的二小子掉进村西的大口井里。还有勤月她现在的爹。咱们来村的时候他就在铁匠炉给牲口打铁钉掌的。年初时叫牲口给踢了。到现在还在炕上躺着呢……听别人说把腰子踢坏了。咳。事是不出。出了就接二连三的。真他妈的邪行。”学成接过话说“大哥。你没听别人说。那些椽子木头是自己着起来的……爹。前几天街上的人都吵吵。拆庙堆放的那些门窗。椽子。一到夜里。从这些木料里飘出来怪异的火球。在周围转游。天亮就不见了。大队派去下夜的人。第二天说啥也不给他不去了。这不。还没几天。着火了……好不哒的。……”
郝万田把烟锅子在炕沿边磕了嗑。吹了吹烟杆对哥俩说“我说老二。你可别跟着瞎吵吵…啊…回屋睡去吧。少说那些不着边的话。”
女儿赛赛上炕把爹的被褥卷拉开。“爹。你也睡吧”
学成这才说“爹。跟你老说点事。我想过几天去躺大同。听说煤矿上干临时工不用开证明。一天能挣一块五毛六。别的村得人。都悄悄的去了”
“学成。你这孩子匝就不听话。啊。你也是非整出点事就歇心了。回你屋睡觉去。别想那些煳七八糟的事。你安分点。让你爹省省心。行不。”
老大学有对老二学成说“学成。你听谁说的。现在去那干临时工。没证明都不行……你呀。这要让大队知道了。有好吗?趁早你死了这份心吧。再说了。你成天的不出工。叫爹匝给你打晃子。”
“哥。队里知道匝地。不就花点钱买他的工分吗。又不是偷来的……”学成看了看爹“反正我想好了。过几天我去试试。不行我在回来”
大哥学有想了想说“学成。你要想试试。等过了年再说。现在还不行。你没看见这把火烧的那惨状。大队肯定会调查的。这个时候找不到你。你这不给咱家找麻烦吗。”
郝万田一声不吭。两个儿子看看爹。老大学有说“爹。那我们去睡了”转身回西屋打点睡觉。赛赛这才把门闩上。上炕把被褥铺垫好对爹说“爹。二哥是啥意思。老这样跑里跑外的不着家。马上年底就分红了。也不知道拉了这麽多饥荒。今年还能还点不”
“你二哥也是想在外边抓麽几个。看看吧。今年一个工多少钱。谁也说不准……咳…塞塞睡去吧。别想那麽多了。”
六队的库房起火断定由外面的玉米高粱秸引燃而秧及到六队库房。白天。虽飘有零星雪花。地表潮湿。着实让人们匪夷所思。三间库房全部塌陷。玉米籽种。麦谷。豆类散落在地上。库房周围及沿途的街巷路面。经泥水践踏无可收拾。垛垛的玉米高粱麦秸大都被水浸泡。所有的周边墙体表面残留着烟熏火燎的痕迹。大火涉及邻里旧舍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寒冷的冬日。地面上泥洼积水开始结冰。勤月躺在母亲身边。被子裹的严严实实。冰凉的身子在烧热的土炕上逐渐暖解。母亲坐在炕边。上身披着棉袄下身盖着厚墩墩的被子。被窝里躺着早已进入童贞梦香的十岁润月。润月在母亲的被窝里享受着母亲给她的。温暖。呵护。慈爱细嫩的脸上泛着红润。勤月的继父赵启光已卧病在床半年了……
赵启光萎缩着身子极度消瘦的脸上显得苍白而力不从心。他翻转身问“勤月。是谁家着火了?”勤月看看坐着的母亲“爸。谁家也没着火。是队里的库房着了。没事了。您睡吧……”母亲看着躺下的勤月。少言寡语几次抿着嘴流落着一丝笑意便问道“勤月。有什麽事吗?”从女儿绯红的脸上。勤月妈已看的出勤月的不寻常。进门的举止完全超出了她自己以往的规矩模式。勤月的突来变化。她开始担心。勤月并没有回答她的话。这一夜娘俩都不能入睡……
勤月的母亲张凤巧六三年带着勤月改嫁到何家屯与铁匠赵启光结婚。那时。勤月只有七岁。原本姓耿的勤月改姓姓赵。勤月与母亲几天不说话。还是赵启光劝勤月妈。“不改就不改吧。给孩子留个念像。不要为难孩子。”所以。耿勤月慢慢的接受了赵启光这个爸爸。第二年勤月妈生下润月。一家人日子过的还是挺舒心。勤月也顺利念完初中高中。赵启光比勤月妈年长六岁。一直在大队的铁匠炉靠打农具和给马牛钉掌维持生计。人朴实憨厚。简朴持家。照顾俩个女儿无微不至。勤月妈非常感动。十一年了。勤月高中毕业回家。本打算能帮家里做点事。还是赵启光阻拦“孩子还小。明年开春再说吧。让孩子歇上一年半载。家里有我。不会解不开锅的。”五月时节。赵启光意外因马受惊吓。叫马踢伤。裆内流血不止。被送到公社医院救治。后转张家口市医院诊治。随有好转。也只能维持现状。出院后每日靠打针吃药维系。小便时常带血的症状缕不见好转。肾脏损伤面难以愈合。从此卧病在床……自从赵启光卧病以后。勤月的母亲张凤巧经常暗自落泪。长嘘短叹。半年时间显得苍老了许多。不到四十岁的女人经受了两次致命的打击。让她感到生活的无奈和凄凉。她再一次把目光投向身边刚满十八岁的勤月。她再想。勤月天资生就漂亮。身段窈窕。这也是她为女儿最炫耀的筹码。明年又是啥前景。谁也不能预知。刚刚的一把大火。浇灭了一家人的希望。也让所有的六队社员感到无奈……
勤月翻翻身把脸扭向另一边。她知道母亲还没睡。压低声音说“妈。赶紧睡吧。”勤月妈说“勤月。你还没有睡呀……是不是心理有事呀”
“没有……”勤月又转过身子凑到母亲身边。屋里一片漆黑。仿佛与母亲的脸紧贴着。勤月轻声细语说“妈。咱们村的那些知识青年。也都去救火了。有十好几个呢……”“啊……”母亲并没有接女儿的话。随意答应了一声。停顿了一会。勤月问“妈。你在听我说话吗?”
“再听。你说吧”
“妈。这些知青今天上午才来。事有多怪。咋就碰上队里着火了。这事出的。也真算是怪怪的……”
“勤月。就为这事呀。睡吧。别瞎想了。”
“不是的。妈。我是说。这些知识青年还真有主意。火着的那麽大。火苗串的一房多高。他们让大伙把赶紧把旁边的玉米高粱麦秸。都挪到离火远的空地上。说先切断火源。又在还没挪开的玉米麦秸上浇了好多水。防止死灰复燃……”勤月还在回味着救火时的情景。母亲张凤巧也在猜测着女儿反常的举止。张凤巧。四十岁的女人。承受过前夫意外夭折带给她的巨大伤痛。如今。又不得不去面对现实。在一次触及她痛苦的神经。流失的岁月。使她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显然老了许多。卧病的丈夫已失去了往日强健的自身体魄。支撑这个家的顶梁柱在摇摇欲坠。她在担心和忧虑。不敢去想今后的情景。也抹不去半年来那伤感的一幕。
十八岁。是女儿花季的季节。如今。家里唯一的依靠就落在刚刚毕业的勤月肩上。她不忍心让女儿过早的承受生活的压力。尽可能的让女儿生活的舒适安愈。女人的自私偏爱。张凤巧开始偏重与勤月的侨装打扮。她相信。女儿突如其来的反常变化。一定是喜欢上了市里下来的知青。即使真的是这样。她愿意把女儿送出去。有个好的归宿……张凤巧想起了自己的十八岁。想起了勤月的生父。那是她最留恋的日子。母女俩就这样各揣着自己的心思。看着窗外遥远的夜空。期待着幸福的降临和苦日子的逆转……
张凤巧早晨起来。把夜里的尿盆倒掉。走到关了一晚上的鸡窝前。把鸡撒开。看看鸡窝里没有夜里下的蛋。这才转身在墙根处抱了一捆烧柴进了堂屋。放在灶前点火烧水做饭。润月还在熟睡。勤月还躺在被窝里迟迟不愿离开温暖舒适的被窝。妹妹润月嘴角上挂着口水还在甜甜入睡。她把被角给妹妹掖紧。这才起身穿好衣服下地。
冬至刚过。阳历年临近。清早。知青的宿舍陆续收到了家里及同学好友寄来得信件。所有的信封上的邮票大部早都被他人揭去了。扬忠礼拿着两封信和当天的报纸推门进来。随手将信件扔在靠门边的衣箱上。对还在洗漱的王继昌说“继昌。你和小锁的信……”
“知道了”
李小锁拿起寄来的信前后看了看。拉开门对已离开的扬忠礼喊到“扬忠礼。邮票哪去了。”
“要邮票干啥?看信就行了……哪那麽多事。”李小锁一边拆信一边自语着“这小子。又把邮票揭走了……”拆开信意外的从信封内掉出一张女孩照片。同屋的几个知青开始挣抢乱做一团。李小锁不停的喊者“别抢。别抢……”张文秋也参与其中。他把照片与几个知青传递端详着说“小锁。这就是你说的。你妈给你包办的玉莲吗?……还不错。还能说的过去”王继昌边看边摇头“不行。不行。也太土气了。小锁。可不能要。”张文秋把照片还给李小锁。说“小锁。你这个玉莲。你们见过面吗?
“见过。还是上高中时见的。这都两三年了。我妈总是驳不开面子。又不好开口说。怕伤了亲戚关系……咳。这叫啥事呀。”
“我说小锁。你最好亲自给她写封信。直接告诉她你的态度。就你这样。总挂着人家。又不理人家。又不回信。时间长了。容易给双方的父母产生误解。你在中间。事情由你而出。你就是罪人。”
“得。得。得。去她的吧。我哪有这份心思给她写信。我妈惹的事。还是她自己去处理吧。”王继昌半开玩笑而认真的说“文秋。你管他这事干吗?这小子好赖话听不进去。纯属一个杠头。递不进人话……说白了。小锁现在的注意力不是那个玉莲……是这个王小丽……”李小锁总算默许了王继昌给他的定论。充满自信的说“哎。你别说。王小丽可是咱们知青的一枝花。谁下手早。谁就能得到。我就不信你继昌不动心思。实际上我也想过。王小丽最看好的还是咱们的秀才。文秋。阎明凯你也就看看连撇都没有。”文秋接过话说
“是吗?小锁……要是这样。你早早退出吧。你还费这劲干吗。我就全权代表了。”
“你也太不瞧好我了。再不行。我也要拼一把。不会让你就这麽轻易得手吧。。”几个知青同时笑了起来。阎明凯坐在木制的长板凳上。趴在临时用衣箱架高可做饭桌用的箱子上。在给家里人写信。这几天各个生产队大都上午不出工。下午则选择性的安排一些人做点其它营生……
知青下来有一个多星期了。部分知青都抽到戏班排戏去了。张文秋。王小丽。王继昌选派到大队调查六队库房着火事件。最近几天几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证据去证实是人为故意纵火所制。其实。不仅仅是社员还是大队干部。对起火原因也在怀疑那怪异的火球。但迫与社会公众的负面影响。又无奈公社定性这是一起阶级敌人有预谋的破坏所施加的政治压力。大队也只能投其所好。迫使每一户甚至每一个人背靠背检举揭发起火前后的异常人和事。扩大了调查范围。导致乡里乡亲互不信任的人际关系。
村里的大喇叭在呼喊着“……知识青年张文秋。王小丽。王继昌。你赶快来大队…啊…就等你们了…快点。啊……”大喇叭里还在返返复复催促着。
知青宿舍。张文秋赶忙把还没吃完的半快玉米面贴饼子。用报纸胡乱包一下。穿上军绿色的面大衣。戴上部队替下的棉帽子。帽子上还残留着五星帽徽卡的痕迹。把包好吃剩下的玉米饼子揣在兜里。随口说了句“喂。你们吃吧。继昌我先走了。你也快点……”王继昌接过话“你不带快咸菜。着什麽急呀……”
“不了。小锁。我们中午回来……给我留饭……”
出了知青宿舍大门一直往西。就是何家屯的主路。王小丽早在门外等着张文秋。两人直奔大队部。张文秋感觉今天天气格外的好。风力不大。生产队送粪的马车经过知青宿舍。径直向村外的大田地里。马铃哗铃哗铃响着。车倌麻根跟着拉粪车走着。与进村的张文秋。王小丽打着招呼。“文秋。去大队呀?”
“啊。麻根叔。往地里送粪呀”
“啊……快去吧。早就吆喝上了。”
张文秋。王小丽还没到大队门口。就听到身后有人叫他。便停下脚步。回头看去。只有几步之隔的耿勤月紧走几步站在张文秋面前。笑着说“知青。张文秋。还认识我吗?”张文秋点点头。看看身边的王小丽。王小丽毫无表情。先离开进了大队部。张文秋看着面前梳理整齐的女孩又面带羞涩。很难让他想起一个星期前六队起火共同去扑救的那个女孩。那是烈火中的女孩。眼前确是窈窕淑女不由得想起古人传流下来的那句诗话“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张文秋细细端详着又有些不敢面对。她不像是乡下的农村女孩。她的肤色细嫩白净。一双杏眼默默含情。使得张文秋忘记自己要说什麽。停顿一会。张文秋这才问了一句“……你是要找我有事吗。?”
“没事就不能找你吗?如果不行。那我就不找了。”耿勤月笑了笑。看看周边没有他人。重复着她说过的话。
张文秋想了想说“我没说不行呀。你找我。想说什麽。?”耿勤月轻轻点点头。轻声细语的说“恩。那好。我想找你单独说点事。”
“啊。可以……你叫什麽?”
“耿勤月”
“那好。耿勤月。我现在有事。大队等我开会。抽时间我会找你的。你看这样行吗?”
“我知道。刚才大喇叭叫你。我听到才出来在这等你。”
“好。我顺便问你。你家是几队的?”
“六队”
“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会找你的。”
耿勤月感到她的心在通通乱跳。从未有过的那种兴奋再次让她叮嘱张文秋“一定要找我。我等你。记住。六队的。耿勤月……”
张文秋目送耿勤月远去。这才转身迈进了大队部的院门口……
大队部是一排平房。最东面的里外间用于大队办公室处理日常事物办公所在地。外间屋看似厨房。锅碗瓢勺生活用具齐全。这些生活用具是安排县里。公社下来干部吃住。又是临时开灶的地方。里间屋是一条土炕。窗户前的桌子上摆放着扩音机。长条板凳坐着四五个大队干部。王小丽早已坐在长条板凳旁边的方椅子上。支书刘殿伟与其他领导班子人员盘坐在土炕上闲扯着。张文秋推门进来。支书刘殿伟招呼着“文秋。上炕坐着。这热乎。”张文秋紧挨这支书效仿盘腿坐下。治保主任刘殿魁在一旁对张文秋说“这个后生。把腿伸开了。你们口上的后生都不会盘腿坐。俺们农村没有那麽多讲究。咋舒服咋来。”
支书刘殿伟问身边的张文秋。“你们来的知青。睡俺们农村的大炕习惯吗。”
“还行。头一两天不太习惯。早晨起来感觉鼻子嗓子都发干。现在可以多了”
“噢。每天晚上仅记住多喝水。时间长了。你就不想睡你们市里的木板床了……咱们农村人讲究的是实惠……”张文秋。王小丽。和大队干部闲谈着。王继昌披着大衣连扣子还没系好。也随后进了大队部。快十一点钟了。仍没有开会的意思。。闲谈中也没有提及到六队起火一事。张文秋感觉饿了。从兜里拿出那半块玉米饼子就着咸菜吃了起来。刘殿魁把自己用的大茶缸子水递给张文秋……
村干部还在东拉西扯着。临近中午。支书刘殿伟这才对几个村干部说“好了。时候不早了。下午没啥事。殿魁。你带上亮子。和咱们知青文秋。王小丽。王继昌去六队走走。都一个多礼拜了。着火的事。在问性问性……另外。找那几个下夜的人。不要在提起‘怪异火球’的事。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把嘴赌上。别他妈的一天瞎叨叨……文秋。你们知识青年肚里墨水多。这几天你们调查的事。你看着随便写写。也好给公社有个说法。再拖下去。也不叫个活计。啊。文秋。就这样吧。没啥事都回个吧……”
六队大牲畜的马槽前。麻根给辕马卸套。一直在饲养房常住的李世延老人把马栓在槽前。给牲口加料。生产队的屋里屋外聚集着队里男男女女的社员。不大的土炕上并排摆放着吃饭用的两个方桌。会计出纳和临时帮手围在桌边。桌上堆放着工分帐目及台帐算盘印泥等。队长紧靠在最里边的窗户前。巴匝巴匝抽着旱烟。屋子里的人有坐有站……会计叫着名单“刘金昶……”人们四下看看。对屋子外面的人喊“四叔。该你了。”刘金昶撩起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那脏夕夕的棉门帘进了屋。人们笑着“四叔。给钱还这麽慢。”
“哎。这俩子。管个屁用……”
会计翻看了一下帐本。把算盘上眼球大的算珠拨拉的很响说“四叔。今年四叔。四婶。和你家大小子总共是一千零五十个工。扣去你家五口人的口粮款一百二十六块。今年每个工分红是四毛六。四叔剩余的是三百五十七快……四叔。在这按个手印……”刘金昶按了手印。把手指头在嘴上舔了舔。数着手里有零有整的钱币。会计在叫下一个“郑佳……”
“在这……”
“你家全年总共三百二十个工。三个人的口粮款是八十二块八。剩余六十四块四。扣除上年欠生产队二十四块二毛四。实际开四十块一毛六”
“刘会计。我在砖场的做的活。工分都转过来了。咋少这麽多。不对吧?”
“你在砖场做的活。是转过来了。这是砖场拿钱买工分的……砖场补给你的工分还留在砖场。这个钱你去大队找张会计那去支你补助的工分钱。和咱们生产队没关系……”
“哦……”郑佳按了手印。会计叫下一个。
“麻根……”麻根早已站在炕沿边前。会计翻看了帐目。搏动着算盘说“麻根。你家全年的出工是八百四十个工。扣口粮款是一百二十六块分红。二百六十块四。不过。这个钱还不能支给你。夜里个。队长和我也合计过这事。还是春起的那事……”刘会计看看还在抽烟的队长说。“你说说吧。”“啊。”队长把烟锅子往窗台上磕了磕说“麻根。就这个事吧。我和刘会计还有出纳。前两天也找过大队。大队也找过公社。由公社出面与供销社核实年初三吨化肥这事。到现在仍没结果。供销社的王主任说。现在年底也在清查库存。让在等等。分红的钱。在没有找回少拉那一吨化肥之前。先不支给你。这也是村支书说定的。你别着急。这钱多咱也是你的……”
麻根脸胀的通红了“这都一年了。当初我就不该去做这活计。事出了。都他妈的躲的远远看热闹。”
“麻根。你说话不葬良心呀。谁看你热闹。别以为你是贫下中农就胡说八道。当时你套车走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二队急需化肥。三吨化肥暂时先借给二队一吨应急。当初告诉你三吨一块都拉回来。可你就偏偏拉回来两吨。你总强调说是二队去了三挂车。叫他们一便就拉回去。省得再捣腾。可二队只把自己家的三吨拉回来了。我才知道咱们少拉了一吨……”
“三哥。当时我就和你说过。拉化肥的车都是咱们村的。二队去了三挂车。走的时候我还问过你。你说。就叫他们一块拉回去。别捣腾了。哦。。出了事了。往我一人身上推。当队长的也不能这样干吧。……”
“我当队长怎麽了。化肥是生产队花钱买的。帐上的每一分钱都是六队贫下中农社员的钱。花了钱。见不着东西。这叫做的啥伙计。票据上明明写的三吨。你少拉了一吨。你不识字呀……亏你还认识两字。要不早让你干别的去了。”
“你当初的决定。叫他们二队的车一便就拉回去。他们不拉。匝地了。丢了化肥那是他二队的问题。”
“这和二队有啥关系。票据在咱们这。咱们花的钱……得。得。得。你去找支书吧。整个他娘的一个混蛋。四六不懂。刘会计。这事就这麽地了。不管他叫下一个……”
“郝万田……”刘会计不在理会麻根与队长还在不停的辩解。两个人又吵吵了一阵。队长接过话说“我说一下郝万田……咱们队有三个是大队定下的受管制的四类分子。按照公社的要求。对受管制的四类分子。我们党对这些人。还是以教育为主。要给他们有出路政策。上边咋定的咱就咋执行。我当队长的也只能安排社员做啥生活。其它都是支书说了算。所以。郝万田。郭中。还有崔富。你们三家往年扣的义务工分。今年就不在扣了。和咱贫下中农社员一样……另外。我在说一下赵启光。今年咱们村出了好几档事。大伙也都知道。村里也花了不少钱。赵启光到现在还在炕上躺着。人干不了活了。也的吃饭吧。所以呢。大队按每天八分给他记工。铁匠炉补助的工分就不在记了。过了年是咋的回事再说……好了。就这麽档子事……”
队长有些话。虽有些笨拙粗鲁。着实让一旁的勤月妈深为感动。今年的分红。赵启光家共分得一百六十七块六毛钱……她将努力的盘算着今后的支出。力所能及的照顾好自己的丈夫和关爱着的两个女儿。……
几天后。六队着火的事已平静了许多。人们不在谈及此事。更多关注的是今年的分红和各队的亏损和盈收。也许。生活在中国广大农村最低底线的农民阶层。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喜忧参半的时侯。也意味着每一户农民家庭生活今后一年的供给开销有了新的规划……
张凤巧的家是一处普通三间的土坯正房。中间屋摆放着十分简陋的家具。整个房屋没有顶棚。常年的烟熏火燎把木头棱和很不均匀的椽子熏烤的见不到原有的模样。蛛丝垂挂。破网粘连正对门口的北墙是两个陈旧的红漆躺柜。墙壁上是两个像框。里面的照片大大小小的排列着。玻璃表面的污垢遮挡了照片的清晰度。堂屋的两边是东西睡觉的寒舍。由于冬季寒冷。所以一家人都再东边的房屋居住。西间房是临时放谷米的粮食囤积处。院子里。堆放着杂乱不堪的烧柴和使用过的农具。南墙的西角是自家人用的漏天茅厕。鸡窝搭建在茅厕的旁边。院子的当中。栽种几年的杏树。早已成材。每年杏熟的时候。这棵不大的杏树也能为家添补点额外收入。屋檐的窗户上挂者干扁豆角和尖辣椒。窗户台上放着锄具。门框的边起是挑水的扁担。两支水桶倒扣在一起……张凤巧在院子里收拾着东西。老母鸡咯咯的叫着。张凤巧放下手中的活计。走到鸡窝前。把母鸡撵走。从临时鸡下蛋的草窝拿出两棵鸡蛋。大队的赤脚医生刘静云背着药箱从街上进来。“嫂子。又忙活啥呢?”
“哦。刘大夫呀。能忙啥呀。”张凤巧边说边把鸡窝前的鸡食盆子用脚扒拉在一旁。说“进屋吧“
“啊…嫂子。启光哥近日好点吗?“
“咋说呢。还那样……哎。慢慢养着贝。”
张凤巧把刘静云让进屋。十岁的润月在洗脸。半闭着眼睛。脸上抹的皂液歪着头叫着“伯伯”
“哎。润月。洗脸呢?”
“伯伯。进屋坐吧”两个人进了屋。涨凤巧对卧病的丈夫说“刘大夫来了。”赵启光微欠了下身子说“刘大夫坐吧”
“启光哥。咋说。最近感觉好点吗?这是我从口上给你捎来的中草药……你在吃吃看。也许说不定那味药里就有管用的。有病就不能着急。急也没用。”张凤巧接过话说“就是。刘大夫。你也好好劝劝你这个大哥。现在我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勤月还能说说他。”
“嫂子。我在口上的医院也打听了一下。向我启光哥这种情况。没太好的办法。只有靠养着。适当下地走动走动。可不能着急。”刘静云把一包包的药放在躺柜上。接着说“启光哥。口上的大夫说。就你这种情况。要想好的快点。咋也得一年半载的。”润月洗漱完进了屋。拿起放在柜上的中药包闻了稳“妈。这是什麽呀?”
“伯伯给你爸爸买的药。”润月把药包拿给卧病父亲的头前。轻声说“爸。吃了这药。就好了。”润月用手在父亲脸上轻轻摸了摸。效仿大人的习惯。把被子给父亲盖了盖。张凤巧刘静云看了很是辛酸。刘静云把药箱的扣带系好说“嫂子。我先走了。启光哥。好好养着。别着急上火的。噢。忘了说一下。这是六副药。总共是三快六。我给记帐了。明年年底扣吧。”
赵启光说“行。咋都行。凤巧。你送送刘大夫。”润月下地连忙到外间屋去开门。刘静云看着懂事的润月说“月。过几天你爸的病就好了。啊……”
“啊”润月点点头。眼睛有些湿润。她惦记着卧病的父亲。
刘静云问着润月说“月。姐姐呢?”
“姐姐她出去了。说是给我买学生用的文具。让我好好上学。”
“好……回屋照顾爸爸吧。伯伯走了。”
“伯伯常来。”张凤巧刘静云来到院子。刘静云问“嫂子。启光哥现在还尿血吗?”
“咳……说不准。有时看他尿里还有血丝。有时就没有。”
“噢。这样吧我抽时间去口上医院在问行问行。回头在给嫂子个回话……啊…嫂子。这样的病不要着急。夫妻那方面的事不能做……”张凤巧顿时感觉脸上发热。和少有的羞涩。低下头说“刘大夫。你再说啥呢……你走吧。”张凤巧转身回到屋里。她没敢进丈夫卧病的房里。一个人进了西间屋。独自一人坐在西间屋冰凉的土炕上。心在跳个不停。东屋传出小女儿润月和丈夫的笑声……
张凤巧自丈夫半年前的意外创伤至今。从来就没有想过个人的事。她专心的照顾着丈夫。照顾着两个女儿。如今。近四十的她。感觉自己已不在属于自己。她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两个女儿身上。她不由得站在女儿梳妆镜前。看着女儿化妆品上的‘面友’两字。脸上泛起由衷的笑意。曾几次背对女儿。偷偷在梳妆前。拔掉多了的白发。无意中从女儿勤月的脸上。发现了自己年轻时的美丽与女儿现在的相象之处。她笑了。笑的自然。笑开了尘封半年之久闭塞的心。冲动悠然而生。身子颤抖。呼吸急促。不由得瘫软在炕上。女人纤细的手。不由得去触摸她最明感的神经。呻吟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