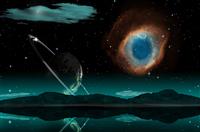
十五年前的一个冬夜,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于艾平大哥,和女高音歌唱家倪素华、电影导演祁晓野等几位朋友,挤在彼时他狭窄却充满书卷气的温馨的小屋里,谈文学、谈诗歌、谈电影、谈人生、谈理想……一直谈到凌晨,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那年北京的冬天很冷,艾平大哥把我们送下楼,一直送到远远的巷子口,站在昏暗的路灯下目送我们离开,高大挺拔的身影一如他送我的他的诗集《寂寞花儿开》那般地孤独,却又迸发出一种顽强的生命力。
后来,当艾平大哥把这套长篇小说《原谅,但不能忘记》(以下简称《原谅》)送给我的时候,我才真正地读懂了那个在寒夜的路灯下孤独而顽强的身影。
我在一种阅读冲动下痛快答应给艾平大哥写一个书评,但却迟迟无法动笔。因为阅读的过程实在是太艰难了,一次次地拿起,一次次地放下。并非文字艰涩,也非结构繁复,相反全书文字晓畅生动,结构清晰分明。每每阻断我的阅读的是,小说中痛彻心扉的经历,匪夷所思的残酷,以及深不见底的沉重。这些都让我本以为一路狂奔的阅读变得步履蹒跚。
读这部书需要巨大的勇气,这并不单指它煌煌四大卷的庞然体量,也不单指它纵达十多年、横跨数千里的时空维度,而是它给阅读者带来的直撞心门有如原子裂变的一轮又一轮震撼。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这应该是描写十年文革最直接、最全面、最真实的一部小说。
说它最直接,是因为很多小说都是以文革为背景,文革仅仅成为故事或人物需要时随时拿来陪衬的布景和道具,而在《原谅》中文革是它的全部,文革是前景,是所有人物活动的舞台,抽离了这个舞台,整个故事将无以立足。相反人物和故事,倒成了文革舞台的演员,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成为这个舞台的傀儡,有的扮演自己,更多的扮演别人,即使那些扮演自己的演的也是别人希望的自己。
说它最全面,是因为以往的文革题材作品,大多是片段式、小场景,反映的也是某地、某领域、某阶层的局部呈现,而《原谅》虽然通过一个少年之眼、一个普通家庭的幻灭反映文革,但书中涉猎社会层面之广、地域之大都超过其他,在作者笔下,一个疯狂的漩涡中的各色人等都被曝光在历史的显微镜下,并且第一次呈现了一个陌生化的“盲流群落”,这些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涵盖三教九流,他们虽然被主流社会所忽略,但他们对成长中的少年给予了最初的人性温暖。
说它最真实,是因为《原谅》虽然用了小说体裁,通篇大量文学性的描写,但字里行间充满着写实主义的氛围,甚至作者也不讳言它的自传性,书里的每一个字,乃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让你觉出它的真实,真实的像历史。但在我看来,这本小说真实的力量实在是超过了历史,比目前很多道貌盎然地陈列在历史书架上的历史书更接近历史真相。这无意中印证了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一句话:“历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说都是真的,除了名字”。
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不断闪回着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同样的两个古老而苦难的民族,经历了相似的两个野蛮的时代。当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曾说过:“在死亡到来之前,无人会被宽恕。”索尔仁尼琴在前苏联的集中营里承受过常人无法想象的折磨,他至死都不原谅那些无法抹去的暴行,尽管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少年于艾平在“特殊的监狱里”的遭遇,丝毫都不逊于“古拉格群岛”,但《原谅》中投射出的那些历尽磨难的人性光辉,却超越了憎恨、仇怨,作者选择了“原谅,但不能忘记”的终极立场,是他在那些令人痛苦的经历之后,悟出的更高的人生境界,人性在经过超越极限地摧残后,恶的更恶,善的更善。遗憾的是,前苏联尚能从那段罪恶的历史中走出来,他们给予了索尔仁尼琴和《古拉格群岛》以应有的尊重,而在我们的土地上,于艾平先生和他的《原谅》却远远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
小说从一个温馨的场景开始,少年于艾平参加中考,本来即将展开一段明媚的人生,不料一夜之间,一切秩序被打碎,身为糖厂副厂长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糖厂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母亲也成为反动家属,灾难并不止于成人,13岁的小学生也成为现行反革命,遭到了不亚于父母的对待,少年于艾平被关押、殴打、流放。刚烈的父亲不甘受辱,悬梁自尽而亡,却被污之以“自绝于人民”的对抗改造,母亲忍辱负重地咬牙抚养兄弟姐妹。天堂与地狱之间有时只差一步,一个本该快乐、阳光的少年时光,从此蒙上厚重的阴影。在那个“血统论”横行的年代,“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通行无碍,从品学兼优的学生一下成为“狗崽子”的少年艾平,几乎迅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但生活仍然有其自身的伟大,已经被逼入绝境的少年,在逐渐被边缘化的境遇中选择了逃离,在被迫的逃离中竟然意外找到了另一片天地,在少年逃离学校、逃离糖厂、逃离熟悉的一切之后,他逃到了大荒原、大雪野,找到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那里有江神庙、山东屯,有榆树崴子、地窨子,那里生存环境险恶,但那里却有不正常社会所缺乏的正常的人伦,抱团取暖成为那一群社会底层群落唯一的生存方式,他们远离政治纷扰,像老鼠一样地偷生,但他们却免于在政治漩涡中的恐惧,这是一种令人心酸的平和生活。极度的物质贫乏和居无定所的动荡,并没有摧垮他们,反而唤醒他们沉睡着的生命力。老头鱼、狗剩子、病叔、漂姐、妮儿、豆芽等等,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背景,层次杂乱,但相同的遭际让他们的命运轨迹相交,在相交的一刹那,他们便浑然一体,成为“不打不相识”的一群。这个自组的小社会,像武侠世界的“丐帮”,虽然地位卑微,但人格并不卑污,他们有自己的法度和规则,当妮儿被大下巴强奸之后,以老绝户为首的一批江湖好汉经过协商,处死了大下巴,他们本已是弱者,但他们对更弱的妇女、儿童仍然有他们的悲悯和保护,道义和公正并不缺席。
在这样的环境中,少年艾平成长了,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处事哲学。他身边不乏美好的人物,那个知识分子的病叔,虽然身体羸弱,但不舍昼夜地搜集、记录民谣民歌;那个被主流社会抛弃的妮儿,用自己的舞蹈让他们拥有着自己的娱乐。
但于艾平曾经拥有的这个难得的童话般的小社会,仍然没有抵御住主流社会的冲击,他们在“扫盲队”的狂轰滥炸下,被驱离、拘捕,四散而逃,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文明为名义的扫荡,最终扫荡的是最后一丝文明,和这些表面野蛮的人相比,谁更接近文明,似乎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判断。正如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运动,最终实施的是对文化的彻底泯灭。这种大悲剧,正值得今天的人反复思考。
《原谅》给当下陷入物欲至上的温柔陷阱中的人们,带来了太多需要重新审视的观念。
这部厚重的大书,不仅仅是于艾平一个人的心灵史和成长史,它是一个时代的挽歌,它告诉每一个人,忘记那段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如果今天的人们能够静下心来,翻开这本书,从每一页的烟尘里都一定会打捞出珍贵的历史珍珠。




